 zhouxu244
zhouxu244
你妹、自己百度不会、我都自己百度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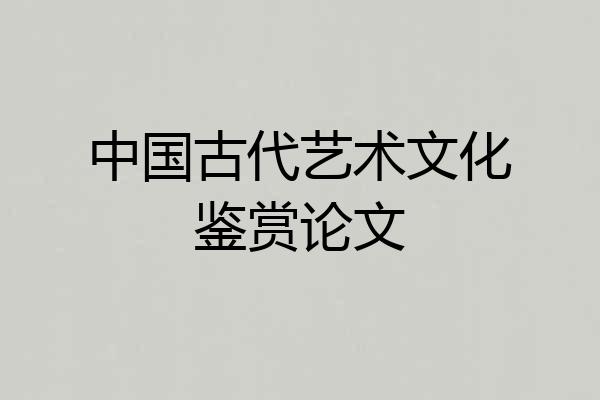
《洛神赋》三、作家“疯癫”的必然 弗洛伊德把作家创作心理与创作过程概括为“精神病的同道和艺术家的白日梦”。在文学理论中,也有“文学乃痛苦使然”的思想,这也就是厨川白村所说的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我国古代也有“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诗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认为,“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这些理论,都视文学为痛苦失意者的精神慰藉和补偿。 前人对曹植本文的创作动机颇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曹植求甄逸女不遂,后又见其玉镂金带枕,哀伤而作,初名《感甄赋》,由明帝改为《洛神赋》(《文选》李善注);有的认为作品实是曹植为了“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而作(胡克家《文选考异》、何焯《义门读书记》);也有人认为“感甄”说有之,不过所感者并非甄后,而是曹植黄初三年的被贬鄄城(朱乾《乐府正义》)。这些看法也许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感到在理解和欣赏一篇古典文学作品时,如果过于拘执史实,把作家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历史的直接反映,那也是不足取的。因此从作者当时的处境和作品的内容来看,与其将神女看做是甄后的化身,或者是作者的代言人,倒不如将她看做是作者在其他作品中一再抒写的那种无法实现的报国理想的艺术象征,这样也许更接近于作者的创作意图。当时,作者报国无门,被逐出京城,内心的苦闷是不难想象的。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是一种与现实对立的幻象,其功能之一是起着麻醉剂的作用。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实际上与精神病患者是一流人物。应该说,当时曹植的心情已经达到精神病般的“癫狂”。幻想洛神的容貌之美,想象人神的悲欢离合,想象群神对洛神的护驾……可以说,做起了白日梦。弗洛伊德在论述作家与白日梦时就说,“梦”就是一种(被压抑的)愿望经过伪装的满足,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它和梦一样都巧妙地伪装了那些被压抑的愿望。作家要把这种愿望表达出来,那是具有和常人不一样的本领。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不言而喻,艺术家不仅应该有强烈的感受力,而且还应该是容易冲动的人。否则,他可能感受颇多,但就是没有把主焦点感受传递给他人的要求。”⑥艺术家的“感受力”和“爱冲动”就决定了他和正常人的不同,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心理病态。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卢那察尔斯基认为:一方面,精神疾患实际上是阶级地位的变化、社会环境的恶化所造成的,一方面,它是对外界条件变化所产生的合理反应,在制造庸人的主流话语压迫之下,那顺应者便被视为正常,而那反抗者便成为“病态”。这个时期,作家就脱离了世俗生活,摆脱了各种现实关系的纠缠,而进入一个想象的、虚构的、自由创造的境界。这是一个幻想的王国,作家在这个主观幻想的世界中是一切的主宰,是国王,是上帝,是造物主,可以随心所欲地造天设地,呼风唤雨,创造万物或毁灭万物;这是一个虚拟的假定的世界,作家在这个非现实的境界中,可以移花接木,指鹿为马,无中生有,更改一切或重组一切;这是一个似醉非醉,似梦非梦,半醉半梦,忘我却又超我的迷人之境,身处此境的人,或狂热欣喜不能自持,或心醉神迷忘乎所以,或移情化物人我莫辨,或多愁善感恍如变了另一个人…… 曹植从小就才思敏捷,深受曹操的喜爱,在那样的皇宫里成长的聪明孩子,可以感受权力的魔力,可以体会受宠和失宠的天壤之别。本来相信自己要继承父位,权倾四野了,可命运和他开了天大的玩笑,皇位成就他人,喜欢的美女成了他人的妻子,好友身首异处,自己也被赶出了京城……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不忍又能如何!那就只有苦闷了,总的来讲,作者产生苦闷之情原因有二:一是“洛神”是他的精神寄托,但她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现实中难以找到,失落无限。二是以此赋托意,他不但与帝王之位无缘还屡受兄弟的逼害,无奈之余又感到悲哀和愤懑。所以,就自然成了“发生变态的心理反应”的人,在文学的天地里,忘我地想象,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可以把洛神描写得闭月羞花,沉鱼落燕;可以和这样的美女谈恋爱甚至做爱;可以在洛神离去后自己驾起小船逆水而上,在长江之上任意漂泊不知回返;可以不得不“归乎东路”,但仍“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我们作为凡人,不能耻笑艺术家的这些行为,因为“在文化和生活方面都失去平衡的时代,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一切正常的人都在为种种矛盾所苦恼,都在寻找对矛盾特别敏感并且能够特别外露、极富感染力地表现负面感受的代言人,——在这样的时代,历史正好以其高明的艺术家的双手,敲击着病理学的琴键”⑦。 曹植是一位奇特的作家,《 洛神赋 》也是一篇里程碑式的赋作,百读千品总还有新的感悟和发现。但总感觉探讨得还很不到位,期待方家高论赐教。
上个世纪初,在西欧流行一部卷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芳托马斯》。32卷由两个作家合作完成,每月创作一卷。合作延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路易•菲伊雷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芳托马斯》的主角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叫芳托马斯。他入室盗窃,诱奸妇女,抢劫银行,无恶不作。警察全力追捕,街上贴满缉拿文告。但是芳托马斯狡诈异常。警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有高超的易容术,从不露出真容;他身手敏捷,能飞檐走壁;他精通缩骨术,能从极小的缝隙中飞身而过。他经常与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化装成绅士出入于酒店、旅馆与赌场,时而与政要侃侃而谈,时而与贵妇逢场作戏。总之,这是一个半魔幻半真实的风流大盗。他有智取法律的力量,敢于向愚蠢的官僚机构挑战,具有超现实的魔力。 《受威胁的凶手》就是芳托马斯的崇拜者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关于马格利特的介绍网上可查,不在此赘述。接着返回原画上,整张画面,二名手持简单工具的侦探,一具赤裸女尸,一名穿着讲究不明身份的人,三名围观者。最初看到这幅画时,脑中便充满各种诡异的问号:谁杀了那名女子?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到底是谁?那两名侦探为何手持如此简单的抓捕工具?三名围观者到底看到了什么? 找到了上面的背景,心中稍微宽松,若马格利特真的是在画芳托马斯的话,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就应该是那位风流大盗了。刚刚做完案的他正在准备易容逃跑,地上的旅行箱,凳子上的大衣和帽子是他的作案工具。门口的两名侦探正在等待时机,或许是在等候支援的同伴,面对名声大作的芳托马斯不敢轻举妄动,面部表情极其凝重。三名围观者目睹一切后,惊愕、忧郁尽显脸上,一切一触即发。而画家更是将看画人的视角至于这一切发生的最近处,整个场面令人紧张不已。 可是画家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已经发明了留声机的年代,两名侦探还手持木棒、绳网,意图逮捕芳托马斯如此这般的江洋大盗,画家拿我们顽固。愚蠢的官僚机构开了一把涮。 老师也讲到过,整幅画人物的面孔全是马格利特,听到时很是迷惑。为何要将自己画成所有人?是技术,用以构成魔幻感么?以哲学绘画著名的画家应该不止有这点想法吧?我这样猜度着。受害者是我,施暴者是我,围观者是我,执法者也是我。画家这么画到底是为什么? 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已经在欧洲普遍流行,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正在蓬勃发展。随着照相机的发明,画家的绘画对象,表现手法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观念经受着暴风骤雨般的洗礼,画家本人也从一只烟斗开始,去探索相似和近似的概念,,把观念和形象分离开来,挑战了大众的常识,发人深省。用绘画把“是”与“不是”这个哲学问题表达出来。而以上各种主义发展到达达主义反传统,反艺术之后,不论是艺术,还是道德都需要一种颠覆,杜尚用他的作画颠覆了艺术形式,那马格利特这幅画就是对道德的一种颠覆。画家崇拜芳托马斯,崇拜他能玩弄政府机构于股掌,完全自由;在作画职业上,画家却扮演着那两名侦探式的人物,理性,专业;在现实生活中,画家扮演着别人生活的围观者,或许自己也是受害者。一个人身上有多种身份,不同以往,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暴者是必须谴责的,围观者是完全无辜的。道德不如以前一样代表着绝对的善恶,而是随着人性的胶合越来越暧昧不清。我们的自私,冷漠不再是无事者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与自己有关。这也正是体现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对观念的改变和诠释。改变和诠释建立在艺术家大量的思考上。马格利特受不了巴黎的艺术氛围回到了比利时,自己一个人思考,用画笔去诠释,虽然在美术史上不如其他一些大家那般早年得志,却也画出了自己的一副天地。他的画总以哲思出名,比例的夸大,主题的诡异,思想的深奥,挡住了大部分人的脚步,被印在钞票上的《天降》,我倒觉得远不如他《窗》系列那组画来的动人,画布遮挡住窗户,画上户外的景象,真实是什么?画家用这组画来拷问我们。与其说马格利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画家,我到是偏向于把他归为现实派的思想,魔幻的表达手法。他和达利不同,达利执迷于如何表达潜意识,但是马格利特却表达着现实,用魔幻拷问着现实。对于常规,大多数人选择默认,而马格利特却用自己的画笔拷问着这些大家默认的东西。以哲人的身份画画,这就是我想说的马格利特。【参考书目】: 《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 刘云卿 广西大学出版社 《现代主义绘画解读》 孙家祥 上海教育出版社 《剑桥艺术史-20世纪艺术》 罗斯玛丽•兰伯特(英) 译林出版社 《世界著名图像的秘密》 张延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 《奢华的冒险-现代艺术的消解与重建》 张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视觉艺术》 爱德华•路希•史密斯(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