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菜花666
油菜花666
五角场的精锐将升学考试大纲要求与考生全方位测评结果相对照,找出有知识盲区,制定科学的辅导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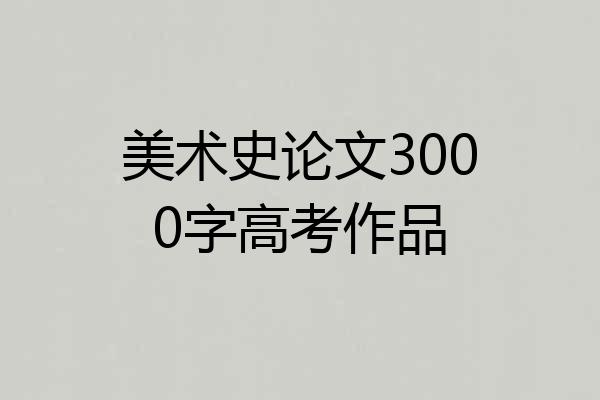
高考报考美术史论专业,文章写作首先要了解作品和作者,那学生对于艺术史也要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肯定要系统接触。否则考生很难掌握专业内容
作为五代董源唯一有名款的作品,《溪岸图》是徐悲鸿1938年在桂林阳朔购得,同年初秋张大千到桂林,硬是“挟吾董源巨帧”而去,1968年张大千以《溪岸图》与王己千交换,1997年5 月再由唐骝千(Oscar LTang)家族购藏捐献给大都会博物馆。同年八月,《纽约客》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引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著名中国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 Cahill)的看法,认为《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激起轩然大波。研讨会上,高居翰作了《对〈溪岸图〉十四点质疑》的发言,再次力主《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中国学者则进行反驳,认为至少是宋人之作。按常理,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讨会,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但不仅有近千人出席旁听,且在高氏讲完后,在场的美国人长时间鼓掌。中国专家陈述观点时,美国人却“听不懂”了。后学如我,对鉴定素无必得,更无缘亲睹《溪岸图》真面目,对此事本不敢置喙。但看了有关的报道,却觉如鲠在喉,必欲一吐。且不言西方“科学”的鉴定方法在鉴定中国书画时未必胜过中国传统的“望气”、“目鉴”法,单研讨会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已显出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欺凌之态。对此,连美国美术史家Croig Cluns也指出,这场研讨会, “甚至可以解读为隐含着令人不愉快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西方学者挑战中国学者。”由此,我也联想到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在美术史与美术批评领域,近百年来我们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美术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中,确实很大程度地存在着空疏玄虚之风,尤其在美术批评中,周易八卦、河图洛书、老庄思想、魏晋玄学,似高头大章,精彩绝伦,实隔靴搔痒,虚空缥缈,读者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作者自身也莫明真谛,徒弄玄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美术理论的引进,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矫正作用,这种引进自然是多多益善。但随着西方美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我们是否该冷静地反思建立在西方美术演变基础上的西方美术理论,能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简单地去套中国美术。以中国画而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画形成了自身完整的审美体系、价值标准、欣赏方式,六法精论、逸神妙能、传神写照、意境格调也好,计白当黑、五笔七墨、布局如弈、三远七观也好,都与西方绘画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画的写生不同于西画的对景写生,中国画的远近法不同于西画的焦点透视,更不是今人假设出来的“散点透视”,简单地把自身尚未真正理解、消化的西方绘画理论,不切实际地移用到中国画的评价上,无异是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之举。
西方经济、军事的相对强大,并不是意味着文化的必然精深,但在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许多人无所适从。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精神不作深入研究,对中国艺术的深层内涵缺乏体悟,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的堂奥却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真正搞懂、吃透西方文化,看了几本翻译得半通不通的西方论著,盲目地借用几个自己也莫明所以的外国术语,对中国传统艺术横加指责。于是,强调西方绘画“科学性”,认为“中国画不科学”的有之,高举“笔墨等于零”者有之,刻意求新求怪求野者亦有之。眩人耳目,引入歧途,服己尚难,服人更是妄想。
中西艺术的文化底蕴、审美方式各居一极,二者是各自独立的艺术体系,许多有睿智的、清醒的艺术家已意识到一味从西方寻找“真经”,是无法拯救传统艺术的,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内涵使得它具有无法想象的生命力和生发力,吸收借鉴他者的经验固然不可或缺,挖掘、发展自身的优良传统更是重中之重。我们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是否也该好好反省呢?我们不必固守祖宗之法一成不变,也不该把祖宗之法一概地抛在脑后吧。今日的美术史论家们,在准确地、系统地引进西方美术理论的同时,要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地、全面地钻研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使其重现生机,并且运用到当前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上来。如此,这一领域中的诸多弊端方有望改进。
美术批评需要交流和对话
李敬仕(绍兴文理学院美术系副教授、花鸟画家)
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的对象通常是美术作品和美术家,因此,它同美术家的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的。在现时代,欲望、金钱这些物质追求经由市场消费逻辑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题词时,一些画家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包装推销自己,对美术评论宠爱有加。而另一些美术家则对美术批评持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这其中有美术家本身的原因,如理论素质的低下和学术视野的狭隘,使他们对美术批评毫无兴趣。但也有对美术批评现状感到不满的原因。有位画家对我说:“那些写美术评论文章的人,读了几本理论书,就到处乱套。他们也许有丰富的哲学、美学、艺术史的知识,但并不懂画,他们哪里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块颜色,怎能看得出这块颜色好在那里?”这话虽有些偏激,却也不无道理。对于美术理论家来说,需要以宽容的学术胸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加强同美术家乃至广大读者的交流和对话。这里我冒昧对美术批评中某些现象谈一些浅陋的看法。
首先是不少文章对视觉形式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或分析不能令人信服。在艺术家心里,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却被转译成了他所理解、把握的艺术媒介形式,而其它因素都退而成为艺术创造的潜在背景因素。对这种艺术审美创造上的形式的“特殊性”不进行深入分析,就难以切入作品的本体。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绘画史上卓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大多出自大画家之手。如中国最早出现的理论专著《论画》和《画品》,作者是顾恺之和谢赫,北宋《林泉高致》的作者是郭熙,明代作《华山图序》的王履,倡导南北宗论的董其昌,清代作《苦瓜和尚画语录》的石涛,都是赫赫有名的画家。这些著作不仅被历代画家们奉为经典,就是在中国美学史上也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对各种视觉形式的感悟和理解,殊非易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即使是专业画家,对他所从事本专业以外的美术作品也难以作完全的解读。一个中国画家看油画,大多也只能停留在欣赏层面上,很难在形式层面上作出令油画家心悦诚服的深刻分析。美术批评家批评的范围涉及国、油、版、雕、年、连环、宣传、壁、民间美术、艺术设计甚至建筑、书法等等,我们不能苛求理论家对美术各门类的样式都进行实践,但评论家必须花大力气对其形式语言的特点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发言权。如果评不到点子上,对美术家来说无异是隔靴搔庠,无济于事。美术评论中常有这样的现象,评论家写文章大加赞扬的作品,画家却认为并不见得是好画。有些推介文章,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文字不多,却东拉西扯地写了不少有关文学史、美术史甚至哲学方面的知识,生硬地和他所要评论的对象联系起来,给人一种评不出什么也硬要说些什么的印象。还有对美术现象的一些评说,也难以使人认同。如有文章说:齐(白石)体的后人,“以吴作人为代表”;并把水墨人物画分为徐(悲鸿)和蒋(兆和)两派,说在明暗造型的手段上,徐氏以染为主,蒋氏以皴为主,把方增先归为徐派,把刘文西等一大批画家归为蒋氏门徒。这种说法未免武断。因为在中国画家眼中,蒋氏的人物画有以毛笔代替木碳笔画素描之嫌,作为中国画中特殊笔法的“皴”,和西洋画中的明暗完全是两回事,且在人物肖像画上运用皴染技法早已有之,怎么成为蒋氏的专利,谁用了皴法,就成了他的门徒呢?
其次是美术批评的话语方式,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很大变化,引进了大量西方文化思想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一些自命精英的前卫理论家依据这一表象,相信中国美术的进程也应实现同一模式的转型,而对本土民族文化和写实画风给予轻蔑的否定,对西方现代性文化不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加以观照,不作批判性的理解,而是沉浸在现代迷信之中急于建构现代乌托邦。一些理论家屈从西方话语中心,并以此为荣。他们以单一的线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把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强加处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的具有斑斓色彩的本土美术。按照耗散结构的理论,进化不是按单一轨线进行的。因此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中还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某些文章故弄玄虚,语言晦涩难懂。文章写给什么人读,应该有一个定位。读有些文章远比读黑格尔著作还难,画家看不懂,一般读者就更不懂了。如果只给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读的话,那就没有发表的必要。有的文章中大段深奥莫解的文字,在仔细琢磨之后,原来说的是很平常浅显的道理,学问不深,文章很深,只会令人厌弃。再有是某些评论家有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那里指手划脚,口气武断专横,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理,不能容忍别的声音,这当然令人反感。还有一些心浮气躁的理论家,在和某些画家作互利性的交换,其后果必然导致美术评论的庸俗化和学术人格的沦丧。凡此种种,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谷流(河南美术出版社编辑、艺术史学者)
真正的艺术评论家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关于艺术的评论话语都是源自牧羊人内心的亦或附庸的神话。牧羊人不但可以是神明的上帝,也照样可以是艺术评论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牧羊人就没有羊,没有羊也就没有牧羊人,没有牧羊人就没有这个世界和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也就更没有必要再有牧羊人和羊所必需的食物和水。既然有了牧羊人,就必须有应该属于他的羊、他的食物和他的水。为了能顺利地找到并得到食物和水,艺术评论家便毫无必要再顾及颜面而不好意思以一种有时连艺术家都拍手叫好的相当体面的圈层话语,如帝国主义般地肆意强奸和占有艺术品创造的原初意义,并美其名曰指点创作和引导时尚,直到把好端端的艺术家糟蹋到不会画画才肯去折腾点儿别的。惟惜乎斯世艺术家众矣,却教那牧羊人太也不好意思停业盘点。是为天职艺术评论家之一副活形也。
艺术品是真正艺术家真正天才的创造,是原初的价值性话语文本,但又有优劣之别,诚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和自我超越》所说:“斯德哥尔摩国家美术馆里令人惊叹的伦勃朗作品——仅仅为这些作品,我们就值得来这儿——和同一美术馆的一幅华托的珍品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然而,在任何时代里,像华托那样的艺术家,甚至尚根本无法与华托相提并论的绘画从业者,实实在在地多如牛毛,并缘此无限地孕育着所谓的艺术评论家的温床。
当今有这样一种时髦的观点:艺术界由艺术家——画廊——艺术评论家——画商共同构成。在市场喧嚣的艺术情境逻辑里,艺术评论家甚至毫无愧色地直接充当着艺术经纪人的角色,从而使匠气之作的价格往往被误认为有价值而存在。制造误导的评论话语似乎罩上了价值的光环而俨然更高于原初话语——真正的艺术品的价值。其实,该情境中真正的艺术品往往匮乏甚至缺席,评论话语往往毫无原创性——毫无历时性价值而仅仅拥有其共时性的实用意义而已。赵汀阳《谁去批评画面》界定了艺术评论的简单标准:描述性的是新闻报道;解释性的是辅助性评论;分析性的才是真正的学术性的艺术评论。信矣!是笃语也。
那么,真正的艺术评论家该由怎样的人来充当?他既不是极权主义者,也不是艺术市场炒作家,更不是那些并无广度和深度专业智识的艺术理论爱好者或自谦曰参与者;而应是那些真正对现时代具有深刻实践和洞察的文艺博学之士——诸如对某一艺术领域有针对性的专门独到研究的艺术史家、作家及相关研究学者。他们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喧嚣者大多都没有底牌!甚者根本就没有牌!打出来的竟还是“借用”人家的牌!甚矣!斯诚悲哉!
两河流域是指纵贯今日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区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它横跨亚非两洲,包括今天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发展摇篮之一。两河流域地区由于战乱、不重视墓葬以及水灾等因素造成了艺术品保存不佳,该地区以工艺美术品和雕刻居多,从艺术特点上看具有明确的东方因素,即写实与装饰风格相结合的特点。建筑最早使用黏土制砖建筑的地区之一,并且在建筑上采用碎陶片镶嵌防水的方法。著名的建筑代表是新巴比伦城,城内有“空中花园”。雕刻著名代表作有圆雕《萨尔贡青铜头像》,浮雕《纳拉姆辛纪功碑》、《垂死的母狮》等。绘画《军旗》是在一块乌黑的木板上,用贝壳、天青石、石灰石、肉红石等石片镶嵌的情节性画面。在古代两河流域绘画遗物十分短缺前提下,它成为研究当时绘画难得的珍品。第一节 苏美尔美术(前27—前25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美术活动和宗教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美尔的美术也不例外。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初,苏美尔人居住的地区出现了十多个城邦,这些城邦都供奉着各自的庇护神,在城邦的中心地带修筑气势宏伟的塔苗作为庇护神在人世间的居住。塔苗不但是宗教活动的中心,还是政治、经济活动的要地,塔苗周伟有宫廷、店铺和作坊,形成喧嚣繁华的街区。最早的苏美尔塔庙遗址位于乌鲁克城,大约建成于公元前3500年,比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的年代还要久远。它的平面呈方形,由体积巨大的平台和平台上的神殿两部分组成,平台高度在12米上下,外围有盘旋上升的阶梯坡道,神殿涂成明亮的白色,故也称为“白庙”。值得注意的是,神殿正门并不坡道的尽头,祭坛也隐匿于神殿内的一个角落里,说明建筑师没有强调严格对称的格局。苏美尔复兴时期修建的乌尔城塔苗,规模要更大一些,它原先有三层平台,现在只剩下一层。它的正面突出了三组阶梯坡道,显得气势非苏美尔人的人物雕像为宗教祭仪用品,它们的形体塑造得近似于圆筒形或圆锥形,比较稚拙;双手紧握着,置于胸前,眼睛大得出奇,正视前方,神情姿态之中流露出虔诚和谦恭,大概在表示对神的无限敬畏与崇拜。泰尔阿斯马尔的阿勃神庙中的《祭祀者群像》,典型地反映出苏美尔人物雕像的上述特征,据说群像中体型最大的两人代表着国王和王后。苏美尔人在装饰工艺上成就斐然,留下了许多风格优美、制作精致的雕刻品。在乌尔城发现的一个牛头竖琴非常精美,琴箱上的扭头用金片和天青石等材料制成,形象生动写实,音箱的端面上还装饰着镶嵌浮雕,浮雕由上而下共分成四个画面,叙述了苏美尔传统神话中的故事,画面构图简洁,中间拟人化的动物姿态生动,顶端拥抱着双牛的人物及底层的蟹形人保持着一种肩部正面、双脚侧面的模式。第二节 阿卡德王国美术(前24—23世纪)约在公元前24世纪,阿卡德人征服了苏美尔诸城邦,在两河流域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国王萨尔贡和他的孙子纳拉姆幸都雄心勃勃,热衷于攻城掠土,扩展疆域。阿卡德美术也以炫耀征服者的武力为目标。在尼尼微发现的一尊阿卡德国王青铜头像表现了君主沉着镇定的风范,他的眼眶大而深邃,具有显著的苏美尔特征。纳拉姆•幸的记功碑则是为了纪念这位国王对山区少数民族远征的胜利。整个浮雕画面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场景,明确的传达了征战胜利的含意。纳拉姆幸王占据着上层空间,他的体型最大,身下的士兵列队沿着山坡向上行进,敌族士兵局促于石碑的边缘,他们中间,有的正在被处死,有的则乞求饶恕。阿卡德王国以军事征服发迹,最后也覆亡于外族的入侵浪潮中。公元前2200年前后,古丁人从东北山区侵入两河流域,征服了阿卡德王国。苏美尔和阿卡德王国美术比较:这个时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起主要作用,也对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包括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美术。 建筑:此时期的建筑有独特的成就。以神庙为中心。 两河流域南部原是一片河沙冲积地,没有可供建筑使用的石料。苏美尔人用粘土制成砖坯,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为了使建筑具有防水性能,他们在墙面镶嵌陶片装饰,类似现在的马赛克。 苏美尔人最重要的建筑为塔庙。是建在几个由土垒起来的大台基上,这种类似于梯形金字塔的建筑被称为“吉库拉塔”。乌鲁克神庙是塔庙的最典型的代表。 乌鲁克城废墟上的这座塔是残留的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塔庙(层进式神庙)之一。据考证,塔庙建于公元前21世纪,它是乌尔那姆(Nammu)国王为了表示对生育女神的尊敬而建的。 雕刻:这一时期的雕刻相当发达。 苏美尔人的圆雕像很可能是用于宗教目的。雕像身体呈圆拄形,双手捧于胸前,姿势虔诚,面部表情平静划一,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纯真、朴实、专注的表情。 阿卡德人的雕刻具有更强的写实性。在尼尼微出土的《萨尔贡一世头像》刻画写实。神志庄严威严,个性坚毅,显示出精湛的工艺水平。《纳拉姆辛浮雕石板》以其写实的手法刻画了纳拉姆辛王率军政府山地的历史场面。对角线的构图使浮雕具有动感和空间感,简单的风景刻画表现了特定的环境。 绘画:现存的苏美尔绘画代表作为乌尔城出土的军旗,即在刷有沥青的木版上用贝壳、闪绿石、粉红色石灰石镶嵌成的战争和庆祝胜利的场面。画面共分三层,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展开,人物、动物、器物的安排有条不紊。人物形象以侧面、正身、侧足为主,倾向于平面的描绘。色彩对于鲜明,四周和各层之间用几何形装饰,很象一幅挂毯,具有浓厚的装饰性。 工艺美术:苏美尔人是古代最杰出的工艺美术师,他们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如黄金器物、武器、金头盔、匕首、乐器等。代表物:《公山羊与圣树》、《牛头竖琴》 苏美尔人的牛头竖琴是最古老的精美乐器。琴架顶部以牛头作为装饰,用天青石和金箔制成,牛的神志表现得十分生动,顾起的牛鼻似在翕动。琴身由黄杨木制成,正面在沥青上用贝壳镶嵌着人和动物,表现了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与双头公牛以及一些神化的动物在进行人类活动的情景,具有浓厚的奇异色彩。第三节 苏美尔文化复兴(前23—前21世纪)古提人统治期间,苏美尔城邦拉伽什仍保持着独立,它使苏美尔文化得到了复兴,历史上把这段时间称为“新苏美尔时期”。格拉什城邦的统治者古地亚有许多雕像传世,从这些雕像可以看出,传统苏美尔工艺精湛的装饰趣味与阿卡德较为粗犷的风格融合在一起。雕像所用的材料是坚硬的花岗岩,表面经过了细心的打磨,十分光洁。古地亚身着单薄的长衫,袒露出肌肉发达的右臂,薄衫的褶纹显得很服帖;他双手我在胸前,眼睛注视着前方,无论是坐像还是立像都保持着同样的神态。第四节 巴比伦王国美术(前19—前12世纪)古巴比伦时期遗留下来的雕塑和绘画作品稀少,著名的有《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它是一块闪绿岩石柱,上面镌刻着的汉谟拉比发典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石碑顶端有浅浮雕,汉谟拉比国王站立在太阳神沙玛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两者交流、呼应的神情体现着君权神授的信仰。汉谟拉比法典: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竭力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社会的情况。法典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共有282条,内容包括诉讼程序、保护私产、租佃、债务、高利贷和婚姻家庭等。它刻在一根高25米,上周长65米,底部周长90米的黑色玄武岩柱上,共3500行,是汉谟拉比为了向神明显示自己的功绩而纂集的。 为后人研究古巴比伦社会经济关系和西亚法律史提供了珍贵材料。第五节 亚述帝国美术(前9—前7世纪)古亚述人居住在底格里斯河上游,以游牧为主,后来凭借勇猛善战,组织良好的军队征服了两河流域以及周围的大片地区。亚述帝国盛期,疆域从西奈半岛延伸至亚美尼高原。古亚述的历史充满了征服战争的血腥和残暴,记录了军事冒险家、暴君的贪婪和欲壑能填的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