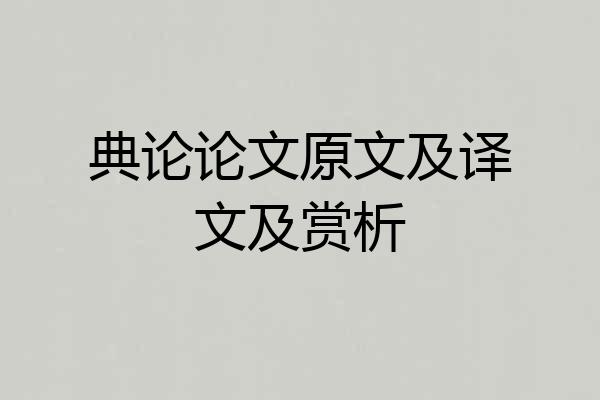nmryo
nmryo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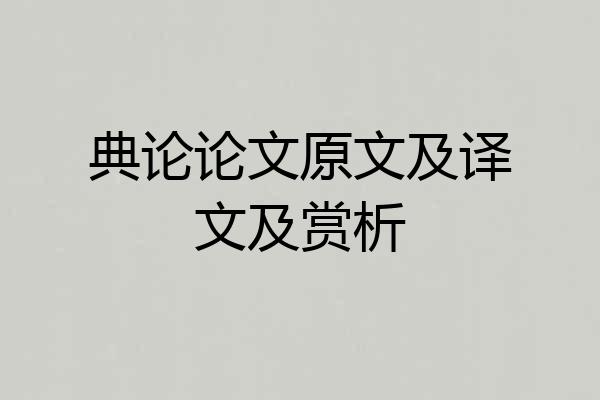
内容《典论·论文》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涉及到文学的价值、作家评论、作家的气质、作品的风格、文体的区别等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为此后的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开了先河。①对文学价值的重视。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②对建安七子作了评价,指出各人的长处和短处。③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它所说的“气”,大体指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气质不同,导致作品的风格就不同。④初步探讨了各种文体的特点:“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善实,诗赋欲丽。”
文章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那是“不自见之患”,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第二,评论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第三,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曹丕的这一观点,表明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第四,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关于《典论·论文》作者曹丕的生平曹丕,字子桓,出于东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卒于魏文帝黄初七年(226)。沛国谯(今年徽亳县)人,曹操次子。建安二十一年(216)操称魏王,二十五年操死,丕袭位为魏王。后废汉献帝自立,称魏文帝,在位七年。《典论·论文》是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论》中的一篇。《典论》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五卷二十篇。所谓“典”,有“常”或“法”的意思。所谓《典论》,主要是指讨论各种事物的法则,在当时被视为规范文人言行的法典。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明帝太和四年,曾将这一名著刊该于洛阳太学的石碑上,凡六碑,供人阅读。据严可均《全三国文》考证:“唐时石本亡,宋时写本亦亡。”只有《自叙》见载于裴松子注,《论文》见收于南梁萧统的《文选》中,因而保留完好无缺至今。又据《艺文类聚》卷十六《赞述太子表》,知成书尚在丕为太子时。另观《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可知成书当已在汉献帝建安末期。关于《典论·论文》的文学批评论首先,曹丕分析自己时代“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一是创作主体在认识论上的根源,表现为既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闇于自见”。二是创作客体在掌握写作技巧上有差异,“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各有所长也就必有所短。解决的办法就是“审己以度人”。即从自我出发,正确地审视别人。这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在文艺领域的具体应用。其次,曹丕认为阻碍掌握文学批语正确标准的,还有两点:一是“贵远贱近”;二是“向声背实”。这种“尊古卑今”的思想向来有之。如西汉时桓谭就曾指出:“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全后汉文》卷十五引桓谭《新论·闵友篇》)曹丕继承其论点而加以发挥,这就有助于打破当时文学批评那种徒慕虚名,迷信权威的思想模式,进而为正确掌握批评标准,推动诗文创作的发展,促进各类风格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独创性的创作风格总是要通过不同文章体裁的熔铸,而呈现在具体作品之中。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艺作品从非文艺作品中界限出来了。它已远远超越于其划分文体论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美学意义。它开始突破儒家“诗言志”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纯文艺观的萌芽。这也意味着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的成果,在曹丕心灵中的破土而出。正如鲁迅所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典论·论文》论文学的价值论与社会作用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束缚,少有独立地位。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曹植:《与杨德祖书》)然而,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认为文章有两大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国家;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自身。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这样从事诗赋创作,亦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亦可以“声名自传于后”,亦可以“不朽”。可见,这个“不朽”说,固然是从《左传》“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题中引申而来的传统说法,但在这里,已经被曹丕赋予“不朽”这一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涵意和历史意义。曹丕把诗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正如李泽厚所说:“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的。文章不朽当然也就是人的不朽。”这反映了曹丕同时代人,由于“文学的自觉”所带来的人的新觉醒。人们已不满足于生前的建功立业,而是思索和追求死后怎样才能“不朽”。于是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人们终于找到了、明确了诗赋确实是这样一种可以“不必寓教训”,而却可寄寓自己思想感情、欢欣、苦恼和追求的艺术载体。这样,尽管“日月易逝”,人生易老,生命无常,“志士大痛”,感性个体的血肉之躯难免要消逝,然而理性个体的精神信念,却可以包孕于“不朽”的诗赋的深层意蕴之中,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无限留恋、执着追求的蕴藉之情和愤发之意。可见,“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两者之间,确乎体现了文学的功利目的和审美的的历史统一。《典论·论文》确乎是建安时代的文学精神的宣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