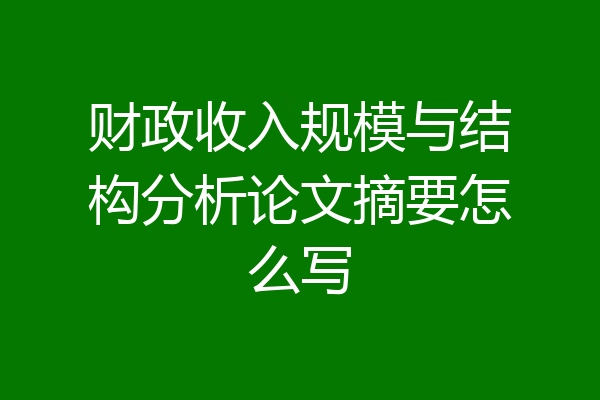不chi葡萄
不chi葡萄
一段60年的时光,是一段人民经历了贫穷短缺、温饱不足,最终进入小康生活的岁月…… 经历无数风雨,熬过多少阵痛,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迈向伟大的复兴。 综合国力由弱到强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教授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60年弹指一挥间。行驶在‘快车道’上的中国经济,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共和国成立之初相比,我们现在一天创造的财富相当于那时一年的总量;现在的国家财政收入是那时的1000倍。如此辉煌成就,令国人自豪,令世界瞩目。” 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个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以及连年战乱中走出的国家,用一穷二白、国力空虚来形容毫不为过。经过60年的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连上台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综合国力由弱到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从纵向比——1952年,5亿多人口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济总量迅猛扩张,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1%,比1952年增加了77倍。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今,中国人民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 从横向比——1952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到1978年也只占到8%;而2008年为4%,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二十九位跃升到第三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8%提高到9%。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2008年GDP折合成美元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日本的6%。人均GDP由1952年的119元人民币上升到1978年的381元后,迅速提高到2008年的22698元,扣除价格因素,2008年比1952年增长4倍,年均增长5%,其中1979—2008年年均增长6%。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329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跃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国力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更体现在国家的财力上。1950年,我国财政收入只有区区62亿元,到2008年突破6万亿元大关,近60年增长了约1000倍!从62亿元增长到1000亿元,用了整整28年的时间;从1000亿元增长到1万亿元,则用了21年的时间;而从1万亿元到突破6万亿元,却只用了9年的时间。令人振奋的数字,印证了我国经济逐步发展壮大、不断迈上新台阶的历史进程。 ● 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水果等产量居世界第一;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发电量居第二 商品由奇缺到充裕 经济结构由低到高 家住华盛顿的美国人琳达·斯特福德一家的生活几乎离不开中国:早晨叫醒的闹钟、盥洗室里的牙刷毛巾、上班的套装和皮鞋、办公室的空调和咖啡壶,以及女儿最爱的芭比娃娃,全都是“中国制造”。“就算不走出美国,身边也到处都是中国!”她感慨万千。 年长些的人,对早年物质匮乏的状况都有深刻的印象。而今,中国经济已经走出短缺,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供给能力名列世界前茅。 能不能让人民都吃饱饭,是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如今,农产品供给不仅解决了占世界1/5人口的吃饭问题,还为加快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持。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52871万吨,与1949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7倍,人均产量增长91%;棉花产量749万吨,增长9倍,人均产量增长9倍;油料产量2953万吨,增长5倍,人均产量增长7倍。 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大国,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短缺问题,而且还使我国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大国。2008年与1949年相比,纱产量由7万吨增加到2149万吨,增长7倍;布由9亿米增加到710亿米,增长6倍;原煤由32亿吨增加到93亿吨,增长3倍。电视机、电冰箱、照相机、洗衣机、计算机、空调器等一大批新兴电子产品产量也从无到有,在改革开放以后呈迅猛扩张之势。 工农业产品产量位次大幅前移,一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解放初期,我国钢产量仅居世界第二十六位,原油仅居第二十七位,发电量仅居第二十五位。经过60年的发展,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位;发电量居第二位;原油产量居第五位。 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中国不断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方面推出重大调整,力争开创新局面。经过60年的大规模建设,中国的产业结构极大改善,比例也日趋合理。到2008年,第一产业由1952年的51%下降为3%,第二产业由8%上升为6%,第三产业则由2%大幅上升至1%。工业结构实现了从门类简单到齐全,从以轻工业为主到轻、重工业共同发展,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向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共同发展的转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个行业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全面实施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继东部率先崛起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战略相继实施,区域结构在不断调整中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 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了9%和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分别属于富裕型和小康型消费结构 走出贫穷解决温饱 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四川双流县永安镇白果村5组村民苏炳中住过三个“家”。第一个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父母挤在一起的两间茅草屋。90年代初,苏炳中一家人住进了第二个家——不漏雨的瓦房里。现在别墅式的楼房是苏炳中的第三个家,洗衣机、液晶电视等现代家电一应俱全。 一切生产的目的,一切财富的创造,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经过了从脱离贫困,解决温饱,到迈向小康的曲折历程,人民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消费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 从收入状况看,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逐步加快,财产性收入进入寻常百姓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不足100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1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5倍,年均增长2%,其中1979—2008年年均增长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4元提高到2008年的4761元,1979—2008年年均实际增长1%。收入的增加使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8万亿元,比1952年底的6亿元增加5万倍,人均从6元增加到16407元。 从保障情况看,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在顺利地向前推进。到2008年末,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1891万人,比1989年增加16181万人;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大幅增加。272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参合率达5%。2008年有2335万城市居民、4306万农村居民得到了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收入的增加,让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保障的逐步建立,让百姓对未来有了越来越多的安全感。吃、穿、用、住的消费水平,更是与6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老人们会记得,百姓心中的高档消费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百元级“老四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80年代是千元级的“新六件”——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电冰箱、电风扇、照相机;到90年代后就是万元级、十万元级、百万元级的电脑、汽车、商品房。 新中国成立之初,城镇居民用于吃和穿的开支占到全部生活费支出的80%,农村居民更高达90%以上。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了9%和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我国城镇居民已经属于富裕型消费结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也达到小康水平。 ● 2008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4万户,实有个体工商户46万户,外资企业29万户 告别单一公有经济 初建市场经济体制 辽宁奥克集团董事长朱建民在1991年凭借自己的科研成果创办校办工厂,2000年创建了股份制企业,公司以年均55%的速度增长,2008年也逆势增长50%,销售额达到11个亿。朱建民说:“有人问国家给了我们民营经济什么?我说给了政策,给了环境。” 财富的创造来自生产力,生产力的活力来自体制。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最大的成就是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 60年前,社会主义新中国向前苏联学习,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之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所占比重约为9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作出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经过30多年的艰辛努力,中国已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单一公有制经济活力不足的弊端得到根本改变。在所有制结构改革方面,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2008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4万户,从业人员75万人;实有个体工商户46万户,从业人员68万人;外资企业29万户。同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控制力、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多种层次、比较完备的体系格局已经形成。要素市场发展加快,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也趋向成熟。在经济调控手段上,初步建立起国家规划计划、财政、货币、投资等政策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 60年的中国是一个成熟的中国,它在探索中走过弯路,在成长中经受痛苦;60年的中国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仍在强劲发展,融入经济全球化才刚刚启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道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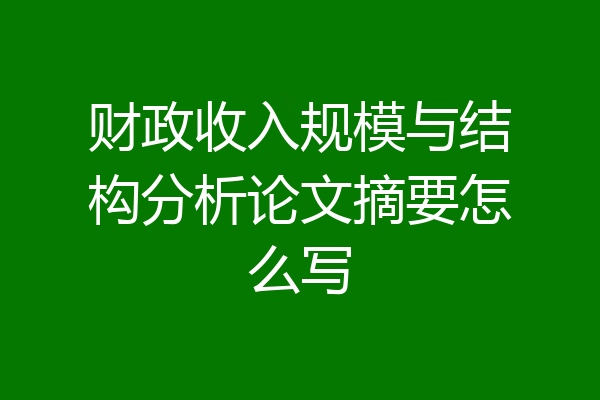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内容摘要]本文对于财政平衡及赤字,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角度,自定义性的分析开始,作了分层次的通盘考察,涉及到赤字的口径、比重、弥补方式、财政收支安排原则等等,并展开到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关系的勾画,以及财政赤字经济影响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财政赤字本身其实无所谓好坏,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一种财政政策工具,利用得当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一)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的概念 财政平衡是指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在总量上相等。如大体相等,可称为基本平衡。财政赤字是指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会计上将其用红字表示,所以称为财政赤字。财政平衡和财政赤字通常按财政年度计算,我国的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相同。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收支相等,也就是财政平衡;二是收大于支,即存在财政结余;三是支大于收,发生赤字。从我国和其他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在编制预算时,三种情况都可能出现,但预算执行结果收支完全相等、分毫不差的情况几乎没有,不是收大于支,就是支大于收。因此,只要收支相差不多,就可以看作财政大体平衡。 (二)赤字与赤字预算 财政赤字是一种统称,出现财政赤字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编制预算时就是支出大于收入,留有一块缺口,这是事先有计划地安排的赤字,这种预算称为赤字预算;另一种是预算安排中并没有赤字或者赤字数额很小,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收入减少或支出扩大,结果出现赤字或增加了赤字的数额,这种执行中出现的赤字也称决算赤字。 预算是平衡的,决算出了赤字,一般来说只是个别年份因天灾或工作失误等而造成的。而赤字预算则一般是和赤字政策相联系的,因为有某种需要,政府事先有计划地安排了赤字的使用方向,以达到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等目标。 (三)长期平衡与当年平衡 一般讲财政平衡,多指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近几十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长期平衡的观点,他们认为财政的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要与经济周期相适应,因此,追求财政平衡也不能只着眼于当年,而应着眼于长期的平衡,在一段时期内,有些年份出现赤字,而另一些年份有结余,从整个时期来看,只要总量大体平衡,就可以认为是财政平衡。 (四)财政赤字的不同口径 如何计算财政赤字的数额,不同国家使用的口径有所不同,最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口径: 第一种:赤字(结余):(经常收入+债务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债务支出) 这一公式又可表示为: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债务收入-债务支出) 这里首先明确一下公式中的概念:经常收入是指政府通过税收等法定渠道所取得的财政收入;经常支出是发挥政府基本职能所安排的支出;投资支出是与固定资产形成直接有关的支出;债务收入包括国家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收入、向国外或银行的借款收入;债务支出是指还本付息的支出。显然这一公式所表示的赤字就是我国通常所说的“硬赤字”,即国家通过举债手段仍未能弥补上的入不敷出硬缺口。 第二种: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 按照这一口径计算,如果出现了财政赤字,说明财政在其正常收入的数量规模之外,多支出了一部分资金,这部分资金通常是通过政府举债来弥补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软赤字”。 这两种口径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把年度债务收支计入正常财政收支的范围。各国对债务收支的处理方法是不相同的,日本把国债收入列入国家岁入之中,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多不把公债收入作为正常的财政收入。1993年之前,我国是采用第一种口径计算财政赤字的。1993年以后,已经改为采用第二种口径了(但在付息支出的处理上仍与西方通行口径有差别)。 (五)中央、地方、全国财政赤字及赤字占GDP的比重 多数国家的预算是分级编制的,中央政府预算中的赤字,称为中央赤字;各地方汇总的地方预算中的赤字叫做地方赤字;全国财政赤字就是将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汇总后,将两部分赤字(结余)相加后的全国总赤字。 一般而言,各国中央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很多,而地方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很少。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其借债能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旦出现赤字要通过以后年度压缩支出或增加税收来弥补。像美国,近十余年来联邦政府几乎年年是赤字,而州和地方政府则基本是略有结余的。按照我国《预算法》的规定,地方政府在编制预算时是不能出现赤字的,在实践中地方出现赤字的情况也比较少。 衡量一个国家财政赤字的多少、财政状况的好坏,进行财政赤字的年度间或国际间比较时,通常采用赤字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 赤字额占GDP的比重,即是将赤字数额与GDP进行对比,它反映财政收支入不敷出的程度和财政稳固状态的区间。一般认为这一指标的警戒线是3%一5%。 (六)安排财政收支的原则 在编制财政预算,安排财政收支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原则。一种是“量入为出”,就是根据收入能力来安排支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另一种是“量出制入”,就是根据支出需要来组织收入,“要办多少事,去筹多少钱”。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量入为出”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原则。但在实践中,有时必要的支出无法压缩到收入能力之内,仍然会出现财政赤字,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绝大多数年份出现赤字,就是这种无奈的结果。 因此,对“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的理解不能绝对化。“量出为入”并不是要满足所有的支出需要,关键是要合理地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安排支出时从当时当地的经济水平和人民负担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入”应该是按照政府履行职能需要积极组织的收入。从逻辑上说,政府理财在收支规模方面第一个层次的原则应是在明确政府合理职能范围和必要支出任务的前提下设计筹措财力的通盘框架,即“量出制入”;而后,应在财政常规运转、安排落实具体项目的层次上量力而行,以收定支,即“量入为出”。这样,量出制入和量入为出是在先后两个层次上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原则,积极组织收入和合理安排支出实际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偏废。 财政赤字的弥补 (一)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方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实行的经济制度各异,形成财政赤字的原因和赤字计算口径不一样,因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也有差别。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第一,用往年财政结余弥补;第二,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第三,发行公债,以债务收支弥补赤字。 往年财政结余弥补赤字 “所谓财政结余,并不是结余钞票,而是结余相应的物资”。①运用上年结余弥补当年赤字,只要是真实的结余,便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来源。利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不会影响银行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量,也不会引起债务负担。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状况看,从1979年至今实际上只有1985年略有结余。因此利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在实践中无法实现。 ① 《陈云文稿选编(1952-196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财政向银行透支是指财政从银行取得资金用以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法;财政向银行借款则可看做是有偿透支,即付息借款。在我国,两种方法的效应实质上差别并不太大。这种弥补方法具有三种运作过程和后果: (1)如果银行是用压缩原有贷款办法或用银行存差向财政垫支,这种垫支都是有物质作基础的,货币发行可以保持在经济性发行范围内,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总供求平衡不会产生冲击。 (2)如果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部分超过了银行承受能力,这时超出的部分将引致银行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而这部分“财政发行”是没有物质保证的,这将引起需求总量膨胀的不良后果。 (3)如果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银行完全没有承受能力,这时,完全靠毫无物质基础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来弥补。这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非经济增长,使社会购买力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90年代初,考虑到银行业务发展情况和体制改革深化等因素,我国已明确规定不得再采用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发行公债弥补赤字 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是现代各国的普遍作法。尽管各国财政赤字形成原因和发债自的是不尽相同的,但各国发行国债的绝大部分实际上都是用于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尤其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发行内债弥补赤字。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多,资源贫乏,生产力低下,仅靠国内筹集弥补赤字的能力有限,还向国外发债弥补赤字。用公债弥补财政赤字,实质上是将不属于国家支配的社会资金在一定时期内转为国家使用,是社会资金使用权在一定时期内的转移和使用结构的调整。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只要合理掌握,一般不会影响经济正常发展。这主要是因为: (1)发行公债只是将部分社会资金的使用权暂时转移,使分散的购买力在一定期限内集中到政府手中,不会改变流通中的货币与可供物资的对应关系,因此,适度的国债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2)公债的认购通常实行自愿的原则,通过发行公债获取的资金基本上是社会资金运动中游离出来的部分,即社会暂歇的资金,将这部分资金暂时集中使用,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不能把公债视为可以无限制使用的弥补财政赤字手段。当财政赤字长期、连续、大量发生,债务规模超出合理区间,形成债台高筑局面时,就可能引出危机性的后果。而且,社会闲置资金是有限的,国家集中过多往往会侵蚀经济主体的必要资金,从而降低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力与效率。 (二)我国财政赤字弥补的概况 1993年以前,由于我国的赤字是财政的经常性收入与债务收入加在一起之后,仍然入不敷出的硬缺口(硬赤字),当这种赤字发生时,因国债收入已经打入预算收入,弥补硬赤字只有两条途径。一是运用过去年度的财政结余,从我国实际情况考察,这种方式余地极小,因为1979年以后连续出现赤字,已经没有结余可利用。另一条途径是向银行透支或借款,这种弥补方式容易引起“赤字货币化”的通货膨胀。例如1979~1980年发生较高额的赤字,按硬赤字口径计算,1979年为67亿元,1980年为05亿元。1980年财政向银行透支额的年末余额为1 2亿元,引起了当年和下一年度的货币发行量较大幅度的增加和零售物价指数的上涨,1979~1980年零售物价指数共上涨8%。1994年,国家规定财政不再向银行借款用以弥补赤字,财政赤字完全依靠国债弥补,至此,我国财政“硬赤字”计算口径不再存在,结束了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的方式。1994年以后的财政赤字全部以发行国债弥补。 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得以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它是一种复杂的动态过程,包括国民经济中的物资可供量(有效供给)与社会购买力(有效需求)数量相当、结构适应、流通顺畅。社会总供求的平衡是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 社会经济运行动态过程中,影响平衡的因素来自各个方面且千变万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平衡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错综复杂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矛盾,使之不断达到相对的平衡。 一般来说,企业和居民只能在自己的收入范围内安排支出,即使发生借款也只是收入支配权的暂时转移。能够创造购买力、影响需求量的只有两个手段,就是财政和金融。财政和信贷的收支都是货币收支,是整个社会货币流通和资金收支与分配的两道“闸门”。 在我国,一方面银行代理财政金库,财政的存款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银行向财政缴纳利润或税收,并且购入财政发行的债券。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是由财政和银行共同提供的。不论是财政出现赤字,还是信贷出现了不平衡,都会影响到社会总供给的变化。所以要保持总供求的平衡,宏观层次上的关键就在于管好这两道“闸门”。当我国取消了财政向银行透支的渠道以后,实际上财政赤字已经不能直接引发总需求的扩张了。但这时财政赤字仍然可以通过各种间接的渠道,引起银行过多发行货币和需求膨胀。 应该看到,50年代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方针,是与我国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1949年建国后,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加快工业建设的进程,国家只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统一调度使用,为此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从生产、流通到分配、消费,都是通过政府的计划直接进行控制和调节的。国民收入除了劳动者的必要消费部分外,绝大部分由财政集中起来统一分配,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需要。这种体制决定了财政对国民经济总量平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只要财政收支能保持平衡,整个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也就有了基础条件;而如果财政不平衡,就会很快引起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所以,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二十年来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经济与旧的计划经济相比,在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政府计划与调控经济的方式发生变化,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已经很小,市场机制正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中发挥着作用。 (2)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经济运行中自主经营,展开竞争。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成份在产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国有企业正在实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结构为目标的战略性改组。 (3)通过对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个人收入大幅度增长,城乡居民的个人消费和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大提高,已经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4)随着银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巳形成了中央银行调控下较完整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信贷资金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货币政策成为调控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状况的有力杠杆。 (5)国际收支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显着上升,随着对外开放,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NP的比例巳由1978年的不足10%,上升到接近40%,1979~1997年间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近35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收支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形势对国民经济及总供求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6)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周期波动“自然节律”因素,在我国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正因为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这些重大的变化,财政虽然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仍然处于重要地位,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决定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两者应该、也必须互相配合,来调节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尽量避免或减少其对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损害。因而,在这一总目标下,我们就不能孤立地追求财政的平衡,而是要特别注重财政与金融的协调平衡以及社会总资金运行与社会供求总量与结构的综合平衡。为了这个目标,有时还需要财政或银行在不同年度采取紧缩或扩张的政策,这与财政平衡方针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经济的市场化以及经济情况的复杂化,决定了今天综合平衡的调控手段要由过去的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调控对象也要由过去对实物形态的指令性安排为主转变为以价值形态的杠杆调节为主。但是,这些并不能否定综合平衡思想的内核。 回顾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国民经济的供求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出现较大波动的时候,人们就肯定和重视综合平衡的理论,并据以进行经济调整;当经济调整恢复了平衡,国民经济顺利运行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就往往出现否定和抛弃综合平衡理论的倾向;当因此而使平衡关系遭到破坏,便又开始一轮新的循环。这种历史现象,一方面说明社会总供求平衡与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说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容易导致国民经济出现反复,甚至付出高昴的“学费”。 在我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经济周期”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减少它带来的损失,即实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是我们必须着力探讨的重大课题,并且要跳出计划经济下固守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的框子,把眼界进一步扩展到跨年度、跨经济周期的相机调控及动态中与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全方位协调配合。西方各国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实施反周期调节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成功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和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实践,是在新时期通过宏观调控寻求总供求平衡的典型事例。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这几年总体上是不断增加的,虽然国家出台的文件总是在强调高科技,环保,新能源,服务业等的重要性,但实际在上述亟待发展的行业投资还是不足。我国在传统重工业方面的投资还是逐年增加,在钢铁,传统能源方面我国已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中国经济体制还是落后于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