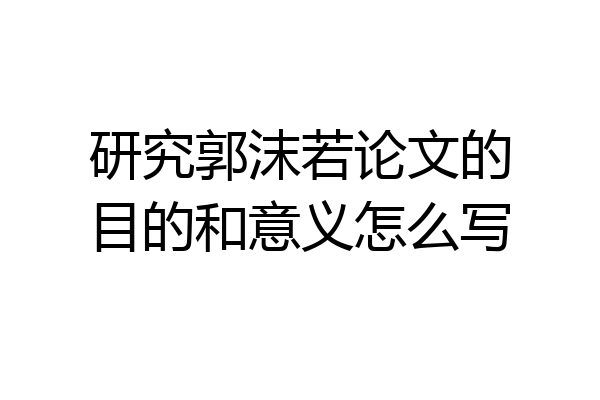←烟花易冷
←烟花易冷
《屈原》写于1 9 4 2 年1 月,时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半壁河山沦于敌手, 蒋介石集团又消极抗日,掀起反共高潮,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人,“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于是,针对政治现实,郭沫若创作了《屈原》,用以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抒发人民的愤慨。作者曾说:“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剧中,郭沫若借屈原的悲剧,展示了光明与黑暗,正义和邪恶,爱国和卖国的尖锐、激烈的斗争,起到了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作用。全剧分为“橘颂”“受诬”“招魂”“被囚”“雷电颂”五幕。课文节选的第五幕的第二场,是全剧的高潮部分。 《屈原》在当年国民党统治的中心——重庆上演,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尤其是“雷电颂”一幕中的独白,激起过许多爱国者的共鸣。每次演出都被观众爆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所淹没。这个剧最后终于被国民党当局禁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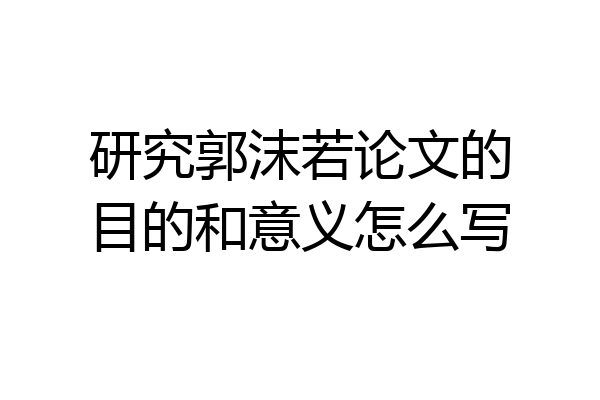
《屈原》写于1942年1月,这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最为黑暗的时候。半壁河山沦于敌手,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并且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大肆屠杀爱国抗战的军民,掀起反共高潮。郭沫若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义愤填膺,创作了《屈原》,以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说:“全中国进步人民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时的时代。”(《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于是,郭沫若借历史上的屈原的悲剧,展示了现实世界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爱国与卖国的尖锐、激烈的斗争,起到了“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作用。全剧分为“橘颂”“受诬”“招魂”“被囚”“雷电颂”五幕。作者对伟大诗人屈原的“独立不移”“坚贞不屈”“光明磊落”的崇高品质的塑造,撼动了进步人民的灵魂。课文节选的是第五幕的第二场,是全剧的高潮部分。尤其是“雷电颂”一幕中的独白,激起过多少爱国人士的共鸣。这段著名的长篇抒情独白用风雷电与黑暗的撞击,表达了屈原与旧世界决绝的心声,充满了对光明的讴歌和向往。屈原和雷电同化了,而郭沫若又和屈原同化了。人们可以在这个历史形象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周恩来同志称赞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能写出来,这是郭沫若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屈原》的创作在当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大大鼓舞了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斗争意志,有力抨击了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暴政。《屈原》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中心——重庆上演,轰动了整个山城,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每次演出都被观众爆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所淹没,这个剧作最后终于被国民党当局禁演。
——郭沫若的小说创作因其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富有开创性的现代创作手法,而具有现代性特征。本文旨在通过其小说内容的竭望现代争取现代而又反现代的意识和小说创作中采用的心理分析和意识流手法揭示其现代性特征。——郭沫若是以诗人著称的,但他写小说也很早在创造社成立以前,他已经在《学灯》上发表过《鼠灾》,在《新中国》上发表过《牧羊裒话》。后他还发表了十多篇短篇。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郭沫若的小说创作重视不够,评价不高因为“他不会节制”,“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认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沈从文的看法很代表了当时一些人的意见。而笔者手里现有的两套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前本书在第八章《郭沫若里赞同郑伯奇的观点,"寄托小说是更成功的"后本书在第五章《郭殊若》里,则只字不提郭沫若的小说,只强调他的诗人和剧作家身份。——在中围现代小说的现化进程当中,郭洙若的小说创作囡其富有开拓精神的现性而具有创新意义。小说的现代性内容20世纪初,中罔现代文学在四的文化思想的启蒙下,追随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而走现代。”由于现代化过程在中国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现代性裂痕显为双重性的。不仅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亦是中之冲突"在郭沫若的小说创作中,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的冲突集中体现在其小说内容中对渴望现代,争取现代而又反抗现代的艰难表达。从1919年发表《牧羊衷话》到《地下的笑声》,郭沫若共创作短篇小说10篇。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吝丰寓然而他们不同方面,不同角度表达着一个共同的信念——通过反帝反封建内容表达苛对中国现代性的渴望,如《牧羊哀话》《月蚀》《行路难》《万引》等,通过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现实生活中的艰难挣扎表现卉对现的争取而又反抗的矛盾。如《叶罗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春别》《漂流三部曲》,《三诗人之死》等,现代性为西方社会带来经济高度发达和物质生产的不足,而隔的现性则昭示着一科一国强的社会理想。11年郭沫若为了现的渴望而到了日本留学,科学知识使郭沫若大量地接触到现代文明,而作为语言教材的外国文学名作又熏陶了他的现代人生观和人道主义精神。——《牧羊哀话》写作于巴黎和会期间,假借朝鲜为小说背景,以一对青年尹子英和阂佩荑的爱情悲剧表现了强烈的排日反帝舶时代精神作为弱国子民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在郭沫若舶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深刻在《行路难》中郭洙若借小说主人公爱牟的口,直接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是说这'支那人'三个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示尽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但是在国外受到的屈辱远远不及在自己的国土上受到的凌辱在《月蚀》中,作家直接发出这样的悲愤之声:"没有法子,走到黄浦滩公园去罢,穿件洋服去假充东洋人去吧可怜的亡国奴!可怜我们连亡国奴都还够不上,印度人都可以进出自由,只有我们华人是狗……"在这月蚀之夜,曾经吟诵过"我是一条天狗"的诗人,只能悲叹"我们地球上的拘类真多,铜鼓的震动,花炮的威胁,又何能济事呢?"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后人,作为曾竖有过发明火药的骄傲今天却在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下摧眉折腰的今人,面对今天因为文明的进程的落后而只能挨打的现实只有倍加感到行路难要改变中国只有挨打,中国人只有受欺负的历史困境,郭沫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突破。——1923年郭沫若创作了《漆园吏游梁》,《函谷关》两篇历史小说1936年出版了历史小说集《豕蹄》,包括《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司马迁发愤》和《贾长沙痛哭》等在历史小说中郭珠若把古代的圣人帝王凡俗化,把知识分子人格化正如他所拟的标题一样,圣人也逃不过食,色这些正常欲望,帝王也难逃死亡的宿命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司马迁和贾谊的肉体虽然遭到了摧残损伤,但他们的精神却是永恒的郭沫若借司马迁64之口,更是直截了当地对封建权势进行着声讨控诉:妈的,旬着书籍放火向着牛羊叩*,向着读书人头上洒尿,向着有钱的寡妇捧玉带,这便是权势啦!哼哼我笑杀它我不愿意天下的人都是不学无术,但我愿意天下的人都有钱假使我是有钱,我的朋友中有一两个人是朱家郭解,少卿,我同你讲,我那里会至于受官刑,我那里稀罕得他这个臭中书夸文学家假如是有鸟氏傈巴寡妇邵样的豪富权势会自行割掉卵袋子来奉侍文学,那里会让文学被剖掉卵袋子去基侍权势?当时中国和现在虽然隔了两千多年但情形却相差不远,郭珠若借古喻今,高扬着反封建能精神旗帜,现实针对性很强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是郭沫若表达其对现代渴望的最佳途径。作为一个绝对自由个人对爱情,理想的热烈追求,则真实地再现了郭沫老对现代的争取。现代一个最主要的内涵就是强调一个真实完整雕自我的存在。而在"五四"期间,文学往往适过爱情,婚恋题材来表现个性的追求,人的独立注重两性问题,表现对理想爱情戢渴求,是当时创造社成员创作的一个共同特征,郭沫若也不例外,《牧羊哀话》,《残春》,《落叶》,《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塞》等抒情小说,都体现了郭洙若对于理想鬟情的追求正如黄侯兴指出,郭沫若“认为,对待两性的情爱,也应该具有这种率真的态度——它敢于冒犯世俗,不顾社会舆论,要自由地表现自我的狂放的感情,要无所顾忌地披露内心的真挚爱情,表现赤裸裸的自我的真实的意识”。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五四文学的研究兴趣将越来越转向文学自身。郭沫若《女神》留给后世的启示性意义,也许将主要在新诗形式方面。新诗在韵律节奏探索上的一系列尝试和突破表明,新诗中“自由派”与“格律派”之争并非文学史描述中的那种两军对垒,而与诗人创作个性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郭沫若《女神》 新诗形式探索 诗人创作个性 一 随着20世纪进入尾声,本世纪初诞生的五四新诗,将留下一些遗产给新的世纪。这笔遗产现在我们还不能打理清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时间越长,选择就将越偏重于文学本身。 作为五四新诗的重要成果之一,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早期诗歌创作,一直被普遍视为现代新诗史的真正开篇。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反复谈论《女神》中充满理想光耀的自我抒情形象、大胆叛逆精神以及渗透在内容和形式中的彻底解放感,为的是——也习惯于从中寻找它与五四时代之间的种种精神联系以及启示意义。但是,当人们谈论了大半个世纪以后,可能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超出1922年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的见解。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就断定了,《女神》之“新”,“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即《女神》的独特性正在于它惊心动魄的精神风格使新诗无愧于那个伟大时代。接着,闻一多准确分析了诗中那个狂放不羁的自我与五四一代青年的内在精神联系,“现在的中国青年——‘五四’后之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象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钟也羁留不得了。他们厌这世界,也厌他们自己。于是急躁者归于自杀,忍耐者力图革新。”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音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因此,闻一多指出,《女神》中那个炫新耀奇的自我并“不是这位诗人独有的,乃是有生之伦,尤其是青年们所同有的”〔①〕。 而现在,20世纪的串串雷声渐渐远去了,又是世纪之交,生活还要继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问题必然要提出来,这就是:郭沫若的早期诗歌创作,除了显而易见的时代精神特点或象征意义外,还有没有更为长远的启示性意义呢?如果没有,它早晚将尘封在一页历史中;如果有,它又在什么地方呢? 显然,这一启示性意义应当到形式方面去寻找。郭沫若在新诗形式解放方面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朱自清曾明确指出,五四新诗革命与近代“诗界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新诗从诗体解放下手”〔②〕。而导致诗体空前大解放的第一人,正是郭沫若。经过以胡适为代表的早期白话诗人步履蹒跚的短暂尝试,郭沫若的《女神》以高度自由、狂放不羁的诗行,一举结束了早期新诗在形式上文白参半的稚拙状态,使新诗体真正获得了自由的生命。《女神》这一重要贡献不仅在新诗史上具有开篇意义,也必然作为一份历史遗产面对未来新诗形式的发展产生相应的启示作用。 不过,研究者们虽然很早就注意到郭沫若对新诗形式解放所做的突出贡献,但似乎更多地是将这种贡献纳入史的描述中。最早从30年代起,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便将对新诗形式方面的不同见解和尝试粗略地划分成两派,一派是主张自由体新诗的,另一派是主张格律体新诗的。这样概括也许是为了便于描述20年代有关新诗形式方面论争的基本状况,但从这以后,文学史学家们的研究思路便不假思索地循着朱自清的观点走,似乎再没有人想到越雷池一步。于是,根据一般新诗历史的描述,我们得知的是,自由诗派和格律诗派从20年代即已形成,并各有各的旗手,自由诗派的当然旗手是郭沫若,而稍晚些的新月派诸诗人则是格律诗派的典型代表。这两个诗派又反复论争,各持一端,脉络清晰,在每个时代差不多都可以找出它们的代表者。它们的实际影响也依时代的不同而互有消涨,并且还将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文学史家从中获得了高层建瓴地把握文学现象的线索和激情,但问题是诗人们凭什么要一代代地这样对峙下去呢?诗人们在理论上也许确实主张过什么,甚至还大声呼吁过,但这对他们自己的创作来说并不是金科玉律,对别人就更不是。这些主张也许是个人的体会、感悟,也许寄托了某种理想,也许与诗人特定的社会、政治立场和态度有关。但无论怎样,当诗人们提笔创作时,这些背景因素就统统隐退了,唯一使他们激动的只能是尽可能完美表达的冲动和愿望。实际上,越是好的作品似乎越是自由自在,很少自我限制,划地为牢。郭沫若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天上的市街》是一个例子 可曾记得爱 团队为您解答。如满意请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