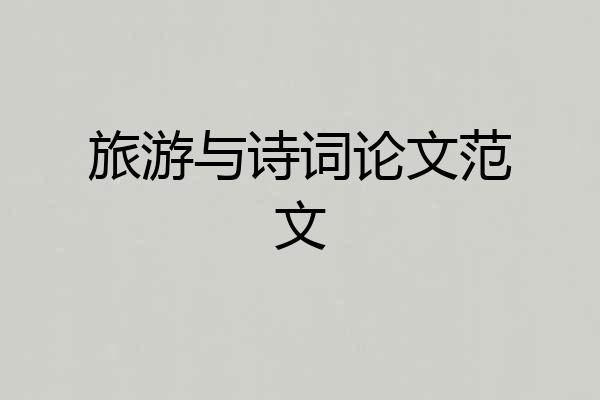一个小橙子
一个小橙子
旅游胡秉言听别人讲外面很多好风光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和向往于是从自己活腻了的地方跑到人家活腻了的地方满怀喜悦的心情去回来满身疲惫空空行囊花掉自己辛苦挣来的钱把那里的人们来帮旅游是旅游者的梦想想看看自己想看的地方看了景点总是有些失望和自己的家乡也没有大的两样旅游来去是那么多匆忙购物花钱是那么的大方满怀喜悦任性近乎疯狂到头来就会大失所望 后悔抓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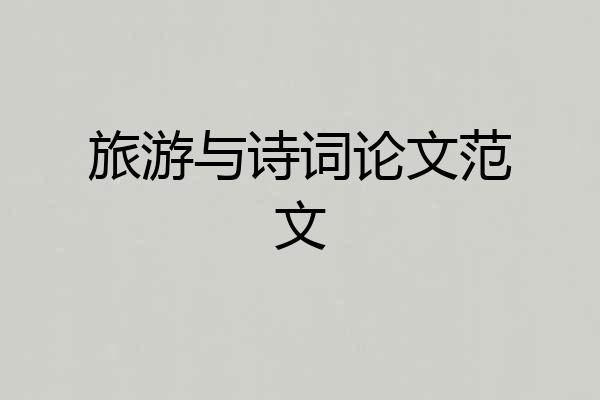
旅游与文学这些天,周围的朋友们许多都要相约出游,去省内和省外的皆有。我一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免显得俗气,在我心中,出门几天而耗个千把元,还远不如呆在家里用它来吃香的、喝辣的。况且随团出游,终日倦怠之下还要慌忙着去赶时间,这就更累了。也有朋友说,你写东西总要四处走走的,这对你有好处。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尤其以唐诗宋词看来更是如此。我们所读过背过的诗词里,那些数不清的咏唱物景的传世之作,若不是旅游,它们从何而来?一位青衣着体的书生,他若是情绪不佳,便大可以看到流水也叹,看到一山一石也叹,看到花木也叹,弄得怨气四溢。反过来要是高兴了,依旧是唱喝新绿,唱喝早春,唱喝一土一尘,顿成了一个可怕的乐天者。这样几千年下来,自然界在中国人眼中早就不是个客观之物了,而成了一个与人混同的情绪体。正是因为从前中国人过分滥用了自己的主观情感,这才致使我们在想问题做事情上都习惯性地去用这个情绪体来回避、龟缩。由于这件事一开始是个文学问题,理所应当的它在文学上也有了反应。简单说的话就是,中国文学自古以来“有文而无质”的毛病,除了文言文体的影响,受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染也是颇重的。胡适在他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提到了他的一首《沁园春》,我想多少也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牢骚:“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腐臭,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我们确不该对自然太过煽情,这可大大避免掉在写文章时无病呻吟、言之无物的空洞。因此我对旅游并无特别的诗意,我想也没这个必要。难道非得躲进山圈水路之中才能写出见仁见智的好文章?讲到旅游与文学,现今的人都不得不谈谈余秋雨。我认为余在这一问题上的确有着有量无质的进步,他所说的有关“到达第一现场”的重要性不无道理,但就最终成形的他的文章看来,实在也未尽脱无病呻吟、言之无物的惯病。文章中的泛泛情绪,甚至是伪情绪太多了。我不是个极物之人,对出游也还是有想往的。但人不要太多太熟,熟人是城市的产物,除非是去城市游玩,否则是与自然之风相悖的。我们去到自然之中,为的就是和世间的情与法来个暂别。太多的骚感不必要,而自然以外的不自然也全是多余的。这个暑假还没有出过远门,或许八月中旬会有一次的,我现在写下对旅游的态度,所谓“岂徒责人,亦以自誓耳”!
介绍了奇山秀水,化育人文。华夏大地的璀璨明珠--江西,山奇水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滋生诗词文赋的沃土。
古典园林的意境和古代诗词绘画的关系 我国素有“书画同源”之说,作为蕴含“有真为假、作假成真”的造园之理意即画理贵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语汝城温泉旅游区植物配置的[04-12] 营造具有良好空间品质人性[04-12] 分析与研究
认数狮子的旅游文化价值,狮子的旅游文化可以体现当地一个地方的文化素养,所以说非常的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