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dejourney
jadejourney
真的好难,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不好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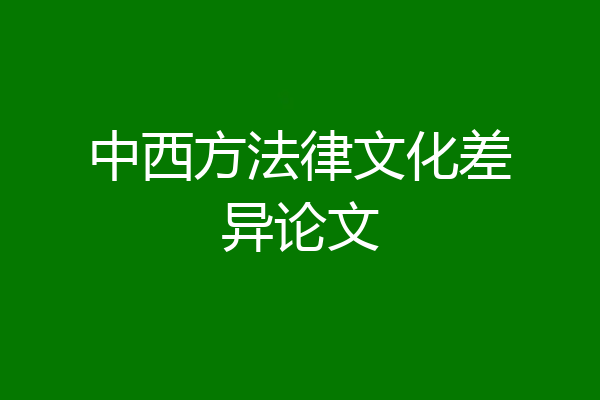
法的公平与正义征汉年【摘要】法律应当是追求更能体现公平、正义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均衡。法律把追求正义和公平作为其终极价值。人们的权利和正义的客观性,法律是其追求正义的保障。如果脱离利益基础,去追求那些文字或理论中的正义和公平,或者追求所谓理性,都显得底气不足 。利益均衡的出发点应当是有效付出和可能收获的均衡。【关键词】公平,正义,权利,义务,均衡【全文】 法的公平与正义 征汉年 法律把追求正义和公平作为其终极价值。法律如果仅仅是正义的,那是单一的和狭义的。正义的追求是以公平为基础上的正义。公平的依据是与时俱进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的均衡,这种均衡首先体现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上,并随经济而发展,这种均衡更为主要的是体现人权的保障和实现的最大化,克服对弱势群体的忽视,也不能对创造性人群的限制,否则这种正义和公平将会限制社会的发展,更不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法律就其实质而言是对自然认识规则及其规律的掌握。如果法律不能体现 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价值趋向,则这种法律就不能称之为良法。当然,我们不应该忽视对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的调和,然而这对矛盾的调和必须站在绝大多数人利益均衡的立场上,否则,这种存在是必然是一种恶 法,也必然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因而社会的立法者要有其独特的预见性和立法的超前性,更不能从补救性作为出发点,补救性的法律作为社会对人们权利保护手段往往是有限的。 自然学派倡导人们的权利和正义的客观性,法律是其追求正义的保障。分析实证主义学派则是把法律作为工具性和纯学科性。它们各自都有其值得光大的内涵。如果把法律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则自然学者提供了法律所追求的目标,同时,提供法律创建的更为充足的理由,那就是天赋人权,人生来就是平等,法律将这种平等制度化。而分析实证主义更注重法律学科中结构的研究,所追求是法律的严谨性,从另一方面去体现公平和正义。两者都把对法律公平和正义作为其终目标来追求,只是他们的出发点和方法不同而已。 作为学派之间的争鸣,能使一个学科或科学更为合理、更明了。如果没有争鸣,肯定没有实质性的飞跃,更不可能有理论的完善。争鸣使人们能有机会面对自身理论的不足和错误,不断修正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贴近实际。就像自然学派与实证学派的争议,导致法律所追求的正义和公平的本质没有变,而使其变得更为全面。自然学派在理性的高度,用理性去解释法及其本质;实证学派把法作为学科建制来要求,去讨论法律的内在规律。当然他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和实际效果不同。然而他们的争鸣,使理论得到发展和提高。无论是站在权利论上,还是站在义务论上,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权利与义务是法律上的对偶概念,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只是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往往权利享受与义务承担上的不对等,甚至可能出现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的现象,同时,必然出现光承担义务,仅仅享受少量现象。因此,法律应当是追求更能体现公平、正义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均衡。 记得有一本叫做《为权利而斗争》的法理著作,光就书的名字就很有诱惑力。初读那本书才知道,在这个与自然有着同样”权利与义务守恒定律”中,我们不仅仅是义务的履行者,而也是权利的享有者,法律是保护这种守恒的调节器。有些权利受到限制和剥夺,还需要通过斗争才能捍卫,这个问题又回到政治学的范畴,故而法律这个玩意是无论如何无法超越人们的理性的追求的,而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并且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当然,影响均衡的因素是多方面,其本身就是各方面力量所体现价值之间的均衡。因而,不同人群对正义和公平有不同追求,而这种追求指导人们的行为。人类在追求自然完美与自身的完善时,法应当是,而且也只有是人类终极的价值。只是在完善自身的过程中,存在人与人的差异,更现实的是谁能使自己得到发展,而发展需要有公平 、公正和均等的机会。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时,这种机会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具有稀缺性。故此,对某一个体而言,不可能拥有同等的机会,但人们都应该有拥有这个机会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也许就是人们所讲的那种权利,只当这种权利得到实现,才会成为利益。 这种利益,也许就是法律所追求最根本的基础。如果脱离利益基础,去追求那些文字或理论中的正义和公平,或者追求所谓理性,都显得底气不足 。利益均衡的出发点应当是有效付出和可能收获的均衡。而对这种均衡,法律所给予保护当事人的自由意合。这种自由意合不是无限制的意合,而是以法律为界限的意合。从这个层面讲,法律所体现的是一种方圆,追求人们在方圆法则中利益的均衡。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利益是综合的,是以物质利益为载体和人们的心理满足程度的结合;而心理的满足可以说是无法脱离人的成长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念。因此讲法律所追求的这种正义和公平是有其时代性和现实性,同时,必然存在其局限性,这是人们对公平和正义理解偏差所造成的。 当人们知道他人的权力是来自本身权利的让渡,他人的权利的实现依赖于自己义务的履行时,那社会就会认识到角色的平等问题。因此,法律所追求的公正和平等,其本质首先是人人都应当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本质上是平等的,贵贱只是社会环境给予的不符合人性本质的评价,是后天变革中形成的,而这种其中是社会环境及观念所产生的惯性,正是这种惯性使得社会发展变得缓慢而稳妥。缓慢的节奏使权利的享受者感觉到一种满足,在制定法律时,必然要保护这种惯性,使惯性法定化。然而,惯性有着本身的惰性,有时会阻碍社会发展的车轮,影响人们权利的均衡。法所追求的正义和公平,必然导致法以及社会的变革,力求使权利与义务在价值体系上的均衡。
西方法律文化是指在古希腊古罗马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北美及受其影响的地区的法律文化。就其中西方法律文化而言,二者在人治与法治、义务与权利、对法律的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将从以下几点来阐述造成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的原因一、中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而存在的,因而法律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和适应物,是随经济的需要产生并发展的。(一)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以家庭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由此决定了人们的活动主要囿于家族、地域、亲缘的有限空间内,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成为人们之间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调节封建家庭和婚姻关系的最高准则,也就是最重要的伦理规范即父为子纲,妻为夫纲。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国家正式以宗法血缘家庭为基础形成的宗法制国家。国事家的放大和直接延伸,是血缘关系的政治化,君为臣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最高准则。这是调节家庭和婚姻关系的最高准则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延伸。在调节社会关系上,不论是家庭之间还是国家调整上,他们会更亲近于伦理社会规范而对法律没有亲近感。人没有任何独立和自由,社会所需要的只是服从和听命。这种伦理依附性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人治的根源。同时,这种依附关系,这种服从和听命也包含着其实强调的就是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人没有独立性也就谈不上权利。(二)西方有悠久的商品经济历史,商品经济是与分工和交换相联系的分工就意味着利益的分化和不同经济利益主体的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满足各自需要必须与其他经济主体经济主体进行交换,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可能出现利益冲突,因而为了使交换顺利进行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法律规则来强制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以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从另一方面来看,商品经济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束缚人具有了独立性。每个人都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并不容许他人的干涉。在市场经济中没人人都想发挥个人的主体作用以满足个人利益。这就需要通过法律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各种需求,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保障利益交换的进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更倾向需通过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利。二、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一)从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来看始终的是一种宏大的整体观中国传统哲学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强调整体观。“天下万物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有和无都是在强调整体,老子认为宇宙就是一个整体,即道。整体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种整体观就要求人们在观察事物时通过直觉、感性去认识把握整体,而无法通过逻辑把握。因而基于这种思维方式,中国需要的不是有棱有角的法律,而是具有整体概括性、感性的习俗、习惯、道德等。他们更多的关注个人的内心,关注人的内心感受,个人的内心情感体验,通过把握自然界而最终更好的把握自我。把自然界的变化看做是个人行为的向导,这种最朴素的对自然的利用所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一种敬畏,没能把人同自然中分化出来,人没有脱离对自然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反映到社会上,也就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因而中国的哲学中所映射出的也是一种人对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中国人治的哲学温床。(二)西方的哲学是一种构成论,是一种强调单元个体的思维方式西方人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体,其他一切都是客体,人的欲望是可以从宇宙万物中找到的,自然界存在的目的就是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在他们的思维下,主体与客体是对立的,这样就把主体从客体中完全解放了出来,重视个人的自由和权力。人人都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并不受外界干涉,但这必然会引发冲突,这就需要通过制定一些规则来调整明确利益,道德伦理的模糊性使他失去了调节的可能性,所依靠的只能是强制性的法律。三、中西方的地缘环境不同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中国四周被海洋、高原、草原、沙漠和森林所包围,且中国自古以来一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著称,这就会形成与外来社会相互隔绝的近乎封闭状态。他们习惯于安居,固守家园不善于活动,这就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态势,是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另一方面这种强大的传统力量又会禁锢国人的思想,是他们不易接受外来文化,很难被外来文化所改变,任何到中国的文化都被深深地刻上了中国印,失去了它原有的活力。这也使中国失去了与外来法律文化交流的契机,中国也就失去了法治的机会。在西方,特别是西方法的发源地古希腊古罗马,他们都位于半岛之上,海上交通较之中国便利。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发展简史》中将中国归为乐山好静的大陆国,将西方归为乐水好动的海洋国家。他说:“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因而环水的环境塑造了西方人好动的品格。他们善于经商,这是西方商品经济的雏形,也是西方法治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