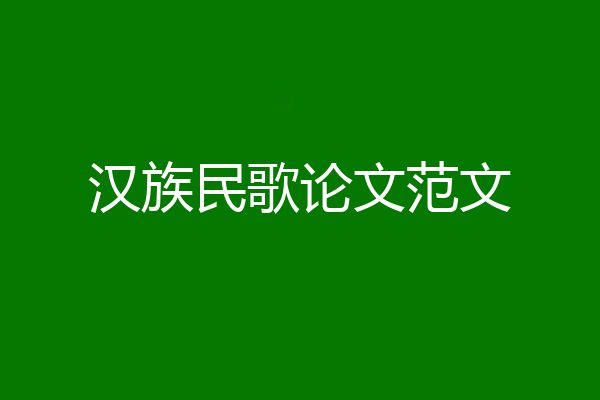派大批大批
派大批大批
民歌是世界各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经典,反映着人类的一切生活实践流传至今,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和艺术珍品。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民歌,并以多样化的体裁、歌唱形式和内容,反映本民族地区特有的历史、民俗、性格、情趣和文化传统。不同的地区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特色,从而成为该地区音乐特征的标志。我国地域广阔,南北东西在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也形成民歌在风格上的多姿多彩。下面我来简略地介绍一下我国南方,西北,中原民歌的风格特征和形成各种风格特征的原因。南方民歌的风格特点:南方民歌的歌词都比较含蓄,善用比、兴,其旋律多表现得婉转、细腻、抒情。旋律进行以级进为主,结构短小精悍。歌曲前多有引子。南方地区河流交错,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自然景观秀丽,对里的人们聪颖细致,音乐风格委婉秀丽;西北地区高原纵横,山石峥嵘,蓝天下一望无垠的黄色土地,气候寒冷,人们为了生存必须与大自然做斗争,所以民歌的音调高亢,嘹亮,质朴中带着严峻和深沉。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地理条件、风俗习惯、生活、生产方式多种多样。语言虽同属汉语,但各地方言不同。东、西、南、北差异很大,民歌的风格特点也呈现出多种特征。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自古以来属于半农半牧文化范畴。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文化交流较早,由于长期的多民族交化交融,产生了八个民族并有的歌种——“花儿”。该区民歌可分“家曲”,“野曲”两大类,“家曲”包括各种酒曲、宴席曲、小词、秧歌等;“野曲”包括“花儿”在内的各种山歌、牧歌等。野曲只能在室外唱。“花儿”为代表性歌种,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扩、淳朴。不论哪个民族都使用汉语演唱,而各民族有自己的衬词,中外闻名的曲目有《上去高山望平川》。地域:包括甘肃、青海、宁夏的黄河上游地区,有汉、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藏、裕固等民族聚居的区域。自古以来属于半农半牧文化范畴。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文化交流较早,由于长期的多民族交化交融,产生了八个民族并有的歌种——“花儿”。该区民歌可分“家曲”,“野曲”两大类,“家曲”包括各种酒曲、宴席曲、小词、秧歌等;“野曲”包括“花儿”在内的各种山歌、牧歌等。野曲只能在室外唱。“花儿”为代表性歌种之一,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扩、淳朴。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 以维吾尔、哈萨克民歌为代表,它受过来自中亚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阿拉伯音乐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歌舞艺术以“十二木卡姆”闻名于世。民歌有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四大类。维吾尔民歌在音调方面包括了中国音乐、阿拉伯、欧洲三种音乐体系,它是中国民歌音调多元化来源最突出的一种。有不少民歌是与舞蹈相结合的,具有活泼、风趣、快乐的格调。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包括山歌(牧歌)、劳动歌、爱情歌、凤俗歌、颂经调五大类。民歌演唱活动大都与佛教节日有关,民歌中不少是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如“囊玛”、“堆谢”、“果谢”、“锅庄”等歌舞品种。音乐属于中国音乐体系,民歌一般特点为热情、开朗、诚挚、动人,极富高原特色,节奏律动性强。民歌:多为群众在口头相传中不断加工提高的集体创作。常见民歌体裁: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儿歌、风俗歌。民歌特点:音乐语言简明洗练,音乐形象鲜明生动,表现手法丰富多彩。(1)是劳动人民自发的口头创作,(2)其歌词、旋律具有变异性,(3)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和民族风格。民歌的不同特点:1、 民歌地方风格的形成与地理环境有关:2、 民歌地方风格的形成与方言有关;民歌的旋律总是和不同的语言、语音、语调相一致。3、 民歌地方风格的形成还与该民族的人文环境、生活方式、经济形态、生活方式都因素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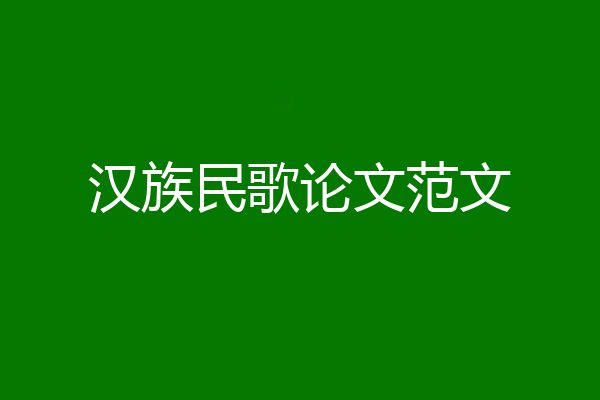
第一:写中国民歌的分类。50---100字度。第二:写 中国民歌与流行歌曲(或者通俗歌曲)的比较。(在你看来,它们的的相同之处或不同之处)。100---200字度。第三:选一到两首(著名或比较广泛流传的)民歌来分析与评价。200---300字度一首。第四:写你对中国民歌的感想。可以用一首来做例子,从歌曲的曲调、节奏、风格、出自那里、怎样流传的?例如:从生活中、一个故事。。。200---300字度。在网上找,应该可以找到一些你需要的吧。。。。。
民歌的分类有多种方法,其中关于民歌音乐的分类有体裁分类和"色彩区"分类两种方法。 民歌的体裁分类是一种运用的时间比较长,从分类的结果看比较成熟,但又还存在一些继续在讨论的问题的分类方法。它是一种从民歌的艺术样式进行分类的方法,具体来说,在分类中更多地考虑的是歌唱形式、音乐的节奏和结构等"外部"形态的特征。 20世纪60年代,《民族音乐概论》一书将我国民歌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长歌(风俗性的和史诗性的)及多声部歌曲4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1983年7月第3次印刷,18-19页)。80年代,音乐学者们考虑到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歌了解的还不够深入和全面,还不宜将少数民族民歌和汉族民歌作统一的分类。因此,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民歌的分类角度比较多样,而汉族民歌仍主要沿用体裁分类方法。另外,以往的体裁分类方法在各类的标准上也不够统一,各类别之间有所交*,例如汉族的劳动号子中也有多声部歌曲;劳动号子、山歌、小调是按照艺术样式分类,而长歌是按照音乐结构的篇幅分类。 20世纪80年代中,随着民间歌曲调查工作的广泛与深入,汉族民歌的体裁划分又经历了一个百家争鸣的阶段。例如:江明惇的《汉族民歌概论》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2月)中,使用了三分法(劳动号子、山歌、小调);李映明的论文《民歌分类管见》(《中国音乐》1982年第3期)中,采用七分法(号子、山歌、田歌、小调、灯歌、儿歌、风俗歌);而由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0至1985年出版的四卷本《中国民歌》中,关于汉族民歌的体裁划分,就有四川的四分法(劳动歌曲、歌舞歌曲、小曲和风俗歌曲),陕西的五分法(山歌、小调、民间歌舞曲、劳动号子、其他),山东的五分法(劳动号子、秧歌和花鼓、大型民歌套曲、生活小调、儿歌),广西的六分法(山歌、劳动歌、小调、儿歌、舞歌、风俗歌),浙江的六分法(号子、山歌、田歌、小调、灯歌、渔歌)等多种体裁分类方法。 体裁分类结果产生分歧的原因,是由于分类依据的不统一。从上述的不同分类结果中可以看出,这些分类法的依据既有民歌的使用场合(例如民间歌舞曲和小调的分法、渔歌和田歌的分法),也有民歌的篇幅(例如大型民歌套曲),还有民歌的社会功能(例如风俗歌曲)等。 本课采用汉族民歌体裁的三分法,即劳动号子、山歌和小调。分类依据主要是民间歌曲的音乐艺术形式,其中包括民间歌曲的歌唱形式、节奏形式和乐段的曲式结构。采用这样的体裁划分标准的理由是: 第一, 民歌的体裁划分应充分考虑其音乐类型。 第二,在不同的场合,可以使用相同的音乐体裁;在相同的场合,可以使用不同的民歌体裁。场合不等同于音乐类型,场合与音乐类型的使用也不能统一。同样,社会功能与民歌体裁的音乐类型也不能统一。例如,在舞歌中、日常生活中和风俗仪式中,都可以使用小调类型的民歌;山歌既可以在山里唱,在秧田里唱,在平地上行走时唱,在民间歌唱节日中唱,还可以在茶馆里唱。山歌在山里唱,既可以是劳动人民个体消愁解闷的自娱性手段,也可能是出于交际和寻找心上人的需要。山歌在秧田里唱,是为了提高劳动的效率,减轻漫长劳动过程中的单调和乏味;而在茶馆里唱,则成为娱人的表演,成为换取报酬的商业行为。民歌有三个特点: 第一,和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 民歌的作者是人民群众.是他们在长期的劳动、生活实践中,为了表现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意志、愿望而创作的。在过去,劳动人民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利,不识字、更不懂谱,但他们却用口口相传的方式编唱着自己的歌曲,以满足生活的需要。如《长工苦》《揽工人儿难》倾吐了遭受欺诈压迫的长工的悲苦情怀;《绣荷包》抒发了少女对情人的思恋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打夯号子》、《川江船夫号子》等,表现了劳动者在与自然作斗争时的豪迈气概;《花蛤蟆》、《冬丝娘》等,唱出了儿童们游戏时天真无邪的性格。但“有假诗人,无假山歌”(明,冯梦龙)。民歌所表现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是最真实、最深切的。 第二,民歌是经过广泛的群众性的即兴编作、口头传唱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无数人智慧的结晶 民歌的创作过程和演唱过程、流传过程是合而为一的.在传唱的过程中即兴创作,在编创的过程中演唱、流传,当然,传统民歌的创作和发展过程是缓慢的、自发的。 第三.音乐形式具有简明朴实、平易近人、生动灵活的特点。 民歌的音乐形式短小精干, 大多以乐段为基本结构单位,单乐段反复而构成分节歌的结构形式在民歌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民歌的音乐材料和表现手法都很经济、洗炼。民歌的音调大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它与方言语音结合紧密,音乐表现很生活化,形式灵活、生动,没有固定的格律.善于变化.对各种不同的内容、唱词、演唱场合与条件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中国民歌的形成 我国的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厚的艺术遗产,远在原始社会,他就在热人民的集体劳动中产生了。只因没有文字与乐谱,当时的民歌无法完整的资料可考。《诗经》中的《国风》,收录了我国北方一百六十篇民歌,虽仅是文字记载,却足以表明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前六世纪,我国民歌以具有相当完整、成熟的艺术形式。几千年来,民革一直紧密地伴随着人民,表达着他们的思想、意志,记录着他们的历史,哺育着历代文艺家。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唐宋的“曲子词”元代的“散曲”、“小令”,明清以来的“歌谣”、“小曲”……就是民歌这汪洋大海留存下来的几颗珍珠。他们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上放射着不灭的光辉。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革也随之走上了新的历程。这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新民歌,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 在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生活方式、劳动方式的影响下,民歌形成了题材形式、风格色彩、表现手段、艺术经验、音调素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有许多分类的方法。 从题材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反映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生产劳动的;反映爱情、婚姻的;反映日常生活的;逗趣、启智的;歌唱传说故事、人物新闻、景物古迹的等等。 从题材形势来看,大致可分为:号子、山歌、小调、舞歌、风俗仪式歌曲等。近半个世纪产生的新民歌中,又出现了进行曲和颂歌两种新的题材因素。从风格色彩来看,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各民族的民歌都以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征丰富着祖国音乐文化的宝库。在一些人数多、居住地域广的民族,如汉、藏、蒙、哈萨克、维吾尔、壮等,还可以按照不同的地方特点再行细分。 众所周知,戏曲、曲艺、民族器乐等其他类别的民族民间音乐都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音乐创作也离不开民歌的滋养。而它们又以各自的艺术特点和专业技巧丰富着民歌的内容,提炼这民歌的形式,给民歌的发展以积极的影响。 我国各民族、各地区、各时期的民歌有如绚丽的白花遍野盛开,美不胜收。这里介绍的不过是民歌中的沧海一粟。
---简论鲍元恺《炎黄风情》的艺术构想学东 鲁琦《黄河之声》1999年第一期就在世人感叹交响音乐知音难觅、抱怨交响新作排演艰难之际,作曲家鲍元恺创作的《炎黄风情》却有着另外一番命运。这部作品自1991年10月首演以来,远播中外、续演不衰、遍受赞誉。先后由国内外多家交响乐团在世界多座城市和地区竞相上演,该作品的多种版本的激光唱片先后问世。如今,《炎黄风情》不仅已经荣获中国音乐金钟奖,而且其中的部分曲目,已经被国家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列入普通高中《音乐欣赏》教材,一些城市的小学、初中音乐教材也选用了这部作品的部分曲目。可以想见,当那些不同年龄的青少年耳濡着《炎黄风情》一天天长大,《炎黄风情》将不仅从空间的广袤上,且会在时间承续的持久中,释发着深远的影响力。(一)上世纪初以来,随着交响音乐这一外来音乐形式的引入,中国作曲家开始了这一新领域内的探索。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作曲家知识构成和审美追求的差异,他们在中、西音乐这两极之间所选取的融合处和切入点各不相同,而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的交响音乐作品,却是他们共同的夙愿。归纳起来,他们的创作无外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以民族民间音调为素材,用交响乐的多声技法加以丰富和深化;二是抽取出民族音乐中最具特性的“细胞”加以自由发挥;三是于音响结构的内部组织和创作构思的审美特色中,把握中国风格之神似。本来,这几种思路各有其功能和侧重,从而构成了中国风格交响音乐创作的“生态平衡”。它们只有创作水准的高下,并无创作层次的贵贱,它们都有可能也已经各自产生出一些传世的精品。然而,也许是因为不同时期作曲家对不同思路创作侧重和提倡的诱导、听众欣赏层面的差异,尤其是若干年来“新潮”音乐的影响,这种“平衡”出现了某种倾斜。不少人的头脑中出现了这样的观念:“十二音技法、序列音乐、无调性、听不懂=创新、现代、先进、高级;而传统技法、有调性、有旋律、能听懂=保守、陈旧、落后、低级。”在这样的观念下,以民族音乐为创作素材、对民族音调、风味的追摹,自然就变作了过时的把戏被抛在了脑后。相反,另一些作曲家记起了“画鬼容易画人难”的古训,深感把那些早已存在且为民众熟若家珍的民族旋律,用交响音乐的语言重新结构,既不失华夏传统之神韵,又能合今人之情趣,别有难处。由于“受到最简单的素材的限制”,“通常要求作曲家掌握更加熟练、高超的写作技巧。”②为此,他们宁愿从民族民间音乐宝库的门前走过,去另辟新境了。应该说,近年来雅俗共赏的交响音乐作品的奇缺,与以上两种思潮不无关联,而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鲍元恺却一头投入了中国民歌的海洋,既不蔑其“易”,更不畏其“难”,从容献上了他的交响音乐新作《炎黄风情---中国汉族民歌24首管弦乐曲》。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曾产生过不少以民歌为素材的交响音乐作品,如贺绿汀的《森吉德玛》、马可的《陕北组曲》、李焕之的《春节序曲》等等。可以说,民歌不仅是中国作曲家取之不尽的素材源泉,也是听惯了单声旋律的中国人了解和接纳交响音乐的桥梁。正因为有了这些人们倍感亲切的民歌旋律作中介,交响音乐这一多声的外来形式,才有可能在中国生根、开花。鲍元恺的《炎黄风情》可以说是其前辈的同类作品在现代的延续和继承,是一次更全面、更系统地运用和展示汉族民歌的民族管弦乐的尝试和探索,它由从河北、云南、陕西、四川、江苏、山西六省区精选出的24首民歌(加上作为结构中部的《哭五更》、《放风筝》等共计31首)组成大型的交响音乐作品,其民歌体裁之多样(包括山歌、小调、号子等全部汉族民歌体裁)、调式之丰富(共计宫、商、徵、羽四种调式),都是空前的,不啻是一次在交响乐队带领下的对汉族民歌的巡礼。其实,鲍元恺的《炎黄风情》与以往的以民歌为素材的创作在创作动机上不尽相同。后者更着眼于“请进来”,即“为交响乐队创作如何才能做到群众化和民族化作一些探索。”③而前者更立意于“走出去”,即以交响音乐这一形式为桥梁,把中国音乐推向世界。确切地说,《炎黄风情》不是一部以民歌为素材的作品,而是一部以展示汉族民歌为目的的作品。这种创作动机的微妙变化,是中国音乐家在求索和反思中对自己民族音乐价值的重新确认,是鲍元恺在进行了各种创作实践后“蓦然回首”的产物。几十年来,中西方音乐并没能真正做到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流。中国音乐“落后”、“简单”、尚处于欧洲音乐发展的初期阶段的思想颇有市场。“欧洲音乐中心论”的魔影在西方也在中国徘徊着。中国作曲家们依照西方音乐的“榜样”塑造着自己的作品;西方音乐家则对中国的音乐知之更少,他们一方面将那些纯粹的中国民歌视作对欧洲音乐的抄袭,一方面又创作着根本不似中国音乐的中国音乐。鲍元恺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作曲家,他赞赏巴托克关于民间歌曲有着“巴赫的赋格曲与莫札特的奏鸣曲”④同样价值的观点,意识到中国传统音乐“有着西方专业音乐难以望其项背的独特神韵和丰富积淀。这些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古老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灿烂音乐遗产,向我们展示了无比广阔的艺术创造的天地。”⑤中国丰富的汉族民歌必将使专业音乐创作获得新的生命。多年的创作实践使鲍元恺意识到:当我们对汉族民歌的规律还没有透彻地把握、对其美的内涵还没有充分发现的时候,我们从中提取出的“基因”往往并非其神髓,因而也就不可能“嫁接”出优良的新作。与其让那些“仿民族性”的作品流传,还不如把原原本本的汉族民歌展示于人。他自信中国音乐独特的魅力。于是,他在《炎黄风情》中让西洋乐器尽力摹仿中国民歌的滑、抹、颤音;加入板胡、唢呐、三弦等中国乐器;对20多首原民歌的旋律未动一音,甚至《蓝花花》的几次变奏也是依据民歌的分节演唱。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让人们听到“原汁原味”的中国音乐。而正是从“洋为中用”到“中为洋用”这一观念的转变,使《炎黄风情》不仅从数量上,也从本质上完成了对以往同类作品的超越。(二)然而,鲍元恺在强调民歌“纯正性”的时候,没有将“纯正”的涵义作狭隘的引伸。他意识到,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的音乐不仅有相异的个性,也有相通的共性。在人类交往臻密、地球愈发显小的当今,各民族音乐间的相互融合,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衡量任何民族的音乐价值既要看它与其他民族音乐的区别程度,也要看它能够接纳外来因素和被外域音乐所接纳的程度。因此,那种远离国际交流的封闭自赏的音乐,也终将会被世界与时代所远离。只有携带着民族优质基因融入国际音乐交往,且能为其他民族所接纳和敬重的民族音乐,才能成为参与构筑人类音乐大厦的基石。这也许正是鲍元恺最终选取中国汉族民歌与西方交响音乐形式联袂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汉族民歌作为最具中国音乐特色的形式,是祖先留给我们最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只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隔绝和交通工具的局限,汉族民歌所暗含的种种技巧与成就常呈分散的状态。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使各地民歌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妥善地搜集、整理和保存民歌(如正在进行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工作),以及以其作为我们发展当代音乐永久的参照是至关重要的。而我们也该注意到,当现代的音乐传播多由民间转入音乐厅场、人们的欣赏口味已不可避免地发生某种转变的条件下,纯民歌的演唱已不可能作为带有普遍意义的表演和欣赏方式了,这无疑会大大限制民歌的传承范围。于是,最能代表中国音乐精神的汉族民歌与最能体现西方专业作曲水平、且为世界成熟的主流艺术形式的交响音乐的结合,无疑会打破中国民歌的封闭状态、拓展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发挥难于替代的作用。既是中西合壁,自然要涉及到对中西音乐特质长短强弱的比较与剖析。鲍元恺以为,蕴含着丰富的单音内涵的优美旋律,是中国音乐最具特色的属性,也是西方音乐难于比拟之所在;而西方音乐所擅长的丰富和声基础和系统的多声创作经验,是中国音乐最为薄弱的环节。他不能接受那种把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绝对化的做法,似乎由于单音音乐乃中国音乐之本质属性,就注定了中国音乐只能永远沿着单音音乐的道路走下去。他以为,中国传统音乐历史地走上单音盛行的道路,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既是社会实践中多声音乐土壤贫瘠的结果,也是包括儒道等音乐美学思想制约及文化心理模式封闭守旧的产物。因此,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审美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大量的多声音乐实践、产生了大量的优秀多声音乐作品,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不满足于欣赏单音音乐的听众的今天,僵化地看待民族审美习惯、以单音音乐为绝对审美准则的做法,不仅是迂腐的,更是行不通的。乍看起来,鲍元恺的音乐价值观似乎有些前后矛盾:单音神奇,多声亦佳,如何为之?其实,这恰恰反映出鲍元恺独特而辩证的中西融合观。总体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没有局部的优劣,更不意味着彼此没有学习、借鉴的必要。他曾说过:“我所说的融合,是黑与白的融合,但不是灰色;是驴与马的融合,但又不是骡子。我要求我的作品中有此也有彼,但绝不能把彼和此的特色都抹杀;是把不同性质的‘元素’放在一起,但只让它们融合,而不是化学中的溶合是‘太极’和‘无极’的同时存在。”⑥显然,《炎黄风情》正是基于这样的融合观而创作的。它没有以牺牲中国音乐的旋律美为代价,换取多声语言的丰满;也没有以摈弃多声思维为筹码,赢得民歌曲调的完美。它既保持了传统单声民歌的旋律、音势、甚至演唱特色,又充分展示出管弦乐队丰富的多声表现力。单声的纯美与多声的繁复被令人信服地、完美地统一在同一部作品之中。也许,《炎黄风情》中的诸多作曲“技法”,并不是鲍元恺的首创,但却经过了悉心的选择和巧妙的组接。这种选择和组接不仅要以音乐的内容、情感为依据;以多样性及避免雷同为准则,还要以不破坏中国的艺术趣味为条件。在鲍元恺的笔下,传统的技法焕发出新鲜的活力;“西方”的手段充溢着“中国”的情调。譬如,为了突出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炎黄风情》大量运用了复调性的织体写法,它们中包括《小白菜》中严格的五度模仿,《走西口》中严格的八度模仿,《小河淌水》中扩展时值的八度模仿;更多的则由于民歌旋律的限定而采用对比式的复调声部和自由的非严格模仿。即便是和声织体,也多通过各声部不同节拍位置的休止、延留、辅助音和经过音的手法给以复调化的处理。从纵向和声结构来看,鲍元恺不排斥以物体振动的泛音原理为依据的三度结构原则,又注重通过转位和弦、高叠和弦和非三度叠置和弦淡化“洋”味,使音响更加绚丽多姿。从横向的和声进行来看,全曲多以二、三度关系的弱进行为主,辅以四度强进行,流畅而又富于色彩。另外,双重调性的和声结构在这部作品中也时有出现,或是因旋律的简洁给和声配置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或是因旋律于和声同主音不同宫音而形成的双重调性的交叠(如《槐花几时开》的旋律与和声竞相差三个降号)。这些技法无疑对丰富民歌的音响色彩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风格的强调还体现在《炎黄风情》的转调技法上。综观全曲,24首分曲每曲都有转调,却没有一处采用西方传统的功能性转调手法。它们或为旋律自身的调式转换,(如《绣荷包》的羽宫交替、《看秧歌》的羽商交替)或为段落间色彩性的调性对置(如《杨柳青》中的大三度转调、《夫妻逗趣》中的小二度转调、《小河淌水》中的小三度转调)。而更多的,则是通过前乐段尾音与后乐段首音的同音相承(即“鱼咬尾”),由于两音为同音高的不同调式音所形成的转调。又因为首音和尾音在转调前后的调式中所处音级的不同,造成了同主音不同调式、同调式不同主音等二度、三度、四度多种转调的可能性(如《茉莉花》中以前段徵音为后段羽音的大二度转调、《雨不洒花花不红》中以前段羽音为后段角音的四度转调、《绣荷包》中以前段宫音为后段羽音的小三度转调等)。其中,又以大二度羽徵调式转换为最多(除《茉莉花》外,尚有《猜调》、《小放牛》、《放马山歌》等)。这一大量存在于我国民间音乐中的转调手法(如民间乐曲《江河水》即是),不仅大大丰富了旋律的调性变化和色彩对比,而且突出了中国音乐连绵展衍的线性思维,从而充满了中国音乐的神韵。(三)真情,是鲍元恺几十年来音乐创作的终极追求。他重视创作技巧,一种新技法的研习,一种新音响的追摹,常使他夜不能寐。但那是因为他懂得音乐的情感要在他对各种形式要素的调配与运用中,才能体现出来。为了音乐情感的需要,他敢于使用最“前卫”的技法;而为了同样的目的,他又不惜砍掉任何多余的手段。这次的《炎黄风情》,由于是以汉族民歌作为其表现内容,这就既决定了鲍元恺所运用的技术不能超出调性音乐的范畴,也决定了他本人的情感及创作个性只能在民歌的限定中、在管弦乐对民歌情感的诠释中显现出来。这既给鲍元恺带来了便利,又为他平添了约束。民歌是一种通过听觉记忆和口头流传进行创作的艺术形式,其歌词与曲调经一代代普通民众和无名艺术家的打磨、提炼,蕴含了丰富的社会价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因而往往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民俗、气质和情感的最集中的体现。明代冯梦龙说过:“世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道出了民歌的魅力恰在于它“法天贵真”的品性、在于它是用欢乐和血泪凝聚而成的真情实感的宣泄。正因如此,人们才不仅把民歌看作具有音乐形态学的研究价值,更看作是情感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范例。从这个意义上说,《炎黄风情》所包含的民歌,为鲍元恺的创作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情感基础。《对花》的欢悦、《猜调》的谐谑、《蓝花花》的凄怨、《太阳出来喜洋洋》的豪壮、《绣荷包》的依眷、《走绛州》的豁达,它们或是景色的素描,或是心言的表露,或是借景寓情,或是分节叙事,可谓喜怒哀乐俱全,酸甜苦辣皆有。而鲍元恺的创造在于,通过管弦乐队的调色板,把这些率真而简约的民歌所蕴含的情感进一步渲染、揭示出来,尤其是他遵从民歌的情感基调而又不囿于歌词限定,循着音乐自身的规律,将民歌演化为精致而独立的器乐作品,使民歌的情感含量和幅度常常得以创造性地扩展和深化。《小白菜》中弦乐声部的五度模仿,象是小女孩与生母灵魂的对话;《闹元宵》里管弦乐队与唢呐的交响,似纯朴乡民的载歌载舞;《走西口》中小提琴与大提琴深情的倾诉,让人更深地体会“悲莫悲兮生别离”的内涵,而《蓝花花》悲楚全奏的嘎然休止,则让人顿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真谛。这样的音乐自然不会被你拒于心门之外,因为这声声旋律不知在中国人的血脉里涌动了多少个春秋;这样的音乐当然也不会让你觉得索然无味,因为作品中无论是风格的对比和统一,情绪的对置与转换,配器布局的迁跃与层递,音乐高潮的积聚与消退,总能把你引入到一个出乎意料又合于情理的艺术境地。表面看来,《炎黄风情》不过是以地域为线索,将24首单曲顺序编排在一起。实际上,鲍元恺在作品的宏观结构和布局上,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炎黄风情》的体裁和内容决定了它不能从中外现成的曲式中找到归宿,而必须在借鉴中外曲式中诸如反复、变化、对比、并置、递进、高潮等原则的同时,营构出自己独特而严谨的结构样式。在每一组乐曲中,鲍元恺总是把较慢的、带有散板特性的单曲安排在最先(如《小河淌水》、《无锡景》、《走西口》的开始部分),而将快速火爆的单曲安排在最尾(如《对花》、《猜调》、《太阳出来喜洋洋》等),使人感到它与中国传统曲式中散慢中快和起承转合原则的血肉联系。唯一的例外在上半场的最后,鲍元恺以缓慢悲怆的《蓝花花》收尾,耐人寻味。它既奠定了上半场从《小白菜》到《蓝花花》的总体悲剧基调,又通过这种悲剧气氛所造成的心理的空旷感和期待感,加强了与下半场音乐的联系,并使听众最终在《看秧歌》大团圆的喜庆气氛中得到心理的满足。实际上,《炎黄风情》的上下半场恰似悲喜的两大“乐章”。从乐队的编制和配器中我们不难发现,整部作品只有五曲运用了大型乐队(以加入小号组、长号组为标志),它们分别为上半场第一组、三组的尾曲和下半场第四组、六组的末曲及六组的二曲。三弦、板胡、唢呐、锣鼓等中国乐器也都安排在上、下半场的最后一组(即三组、六组)之中,这样在上下半场的两大“乐章”中,自然形成了强--弱--强两个拱形结构。在这个大的框架下,鲍元恺也注重了乐曲间情感的反差和调配,极力避免音色和乐思呈示的单一化,做到反复多姿(如《杨柳青》完全运用弦乐的拨奏、《夫妻逗趣》采用乐队与钢琴的竞奏),最终将全曲集中在同一个调中心上(由《小白菜》的G徵到《看秧歌》的G羽)。这样,原本是一首首零散的民歌就被汇集于一个多样而统一的系统之中了。《炎黄风情》自创作至今,已经十年有余了。今天,它的妙响仍时常回荡在我们的耳畔,它留下的启示和思考更时常萦绕于我们的心头。它告诉我们,“传统的民族形式未必旧,最现代的手法也未必新。关键却在于我们能否从传统的深厚基础中吸取出新的精神力量。”⑦它提醒我们,不管世界如何变幻,不管技巧怎样翻新,追求使听众强烈共鸣的艺术境界,永远不会过时。它证明,中国作曲家前面的道路不仅很漫长,而且通往成功的途经也很多样,作曲家尽可以在自己偏爱的领地和擅长的角度驰骋创作才华。注释:①《乐府新声》1992年4期3页。②《巴托克论文书信选》(1985年版)140页。③ 李焕之《音乐论文选集》(1966年版)6页。④《巴托克论文书信选》(1985年版)30页。⑤ 鲍元恺《中国风》(载《音乐研究》1994年2期)。⑥ 侯军《东方既白》(1993年版)403页。⑦ 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1990年版)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