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族之乡
水族之乡
青藏铁路遇到冻土难题,我国是如何解决,并取得世界独立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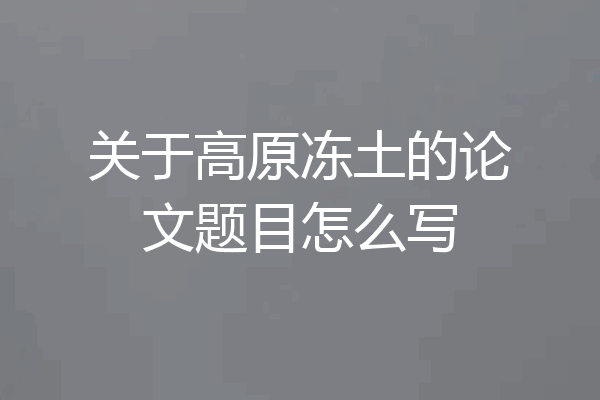
课题是什么?论文题目是什么?氢能源一.氢能源简介作为现有主要燃料的汽油和柴油,生产它们几乎完全依靠化石燃料。随着化石燃料耗量的日益增加,其储量日益减少,终有一天这些资源将要枯竭,这就迫切需要寻找一种不依赖化石燃料的、储量丰富的新的含能体能源。氢能正是一种在常规能源危机的出现、在开发新的能源的同时人们期待的新的能源。氢位于元素周期表之首,它的原子序数为1,在常温常压下为气态,在超低温高压下又可成为液态。作为能源,氢有以下特点: 所有元素中,氢重量最轻。在标准状态下,它的密度为0899g/L;在-7℃时,可成为液体,若将压力增大到数百个大气压,液氢就可变为固态氢。 所有气体中,氢气的导热性最好,比大多数气体的导热系数高出10倍,因此在能源工业中氢是极好的传热载体。 氢是自然界存在最普遍的元素,据估计它构成了宇宙质量的75%,除空气中含有氢气外,它主要以化合物的形态贮存于水中,而水是地球上最广泛的物质。据推算,如把海水中的氢全部提取出来,它所产生的总热量比地球上所有化石燃料放出的热量还大90O0倍。 除核燃料外氢的发热值是所有化石燃料、化工燃料和生物燃料中最高的,为351kJ/kg,是汽油发热值的3倍。 氢燃烧性能好,点燃快,与空气混合时有广泛的可燃范围,而且燃点高,燃烧速度快。 氢本身无毒,与其他燃料相比氢燃烧时最清洁,除生成水和少量氮化氢外不会产生诸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氢化合物、铅化物和粉尘颗粒等对环境有害的污染物质,少量的氮化氢经过适当处理也不会污染环境,而且燃烧生成的水还可继续制氢,反复循环使用。 氢能利用形式多,既可以通过燃烧产生热能,在热力发动机中产生机械功,又可以作为能源材料用于燃料电池,或转换成固态氢用作结构材料。用氢代替煤和石油,不需对现有的技术装备作重大的改造,现在的内燃机稍加改装即可使用。 氢可以以气态、液态或固态的金属氢化物出现,能适应贮运及各种应用环境的不同要求。由以上特点可以看出氢是一种理想的新的能源。目前液氢已广泛用作航天动力的燃料,但氢能的大规模的商业应用还有待解决以下关键问题: 廉价的制氢技术。因为氢是一种二次能源,它的制取不但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而且目前制氢效率很低,因此寻求大规模的廉价的制氢技术是各国科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安全可靠的贮氢和输氢方法。由于氢易气化、着火、爆炸,因此如何妥善解决氢能的贮存和运输问题也就成为开发氢能的关键。许多科学家认为,氢能在二十一世纪有可能在世界能源舞台上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能源。氢能是一种二次能源,因为它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利用其它能源制取的,而不象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可以直接从地下开采。在自然界中,氢已和氧结合成水,必须用热分解或电分解的方法把氢从水中分离出来。如果用煤、石油和天然气等燃烧所产生的热或所转换成的电分解水制氢,那显然是划不来的。现在看来,高效率的制氢的基本途径,是利用太阳能。如果能用太阳能来制氢,那就等于把无穷无尽的、分散的太阳能转变成了高度集中的干净能源了,其意义十分重大。目前利用太阳能分解水制氢的方法有太阳能热分解水制氢、太阳能发电电解水制氢、阳光催化光解水制氢、太阳能生物制氢等等。利用太阳能制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这却是一个十分困难的研究课题,有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工程技术问题要解决,然而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投入不少的人力、财力、物力,并且业已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因此在以后,以太阳能制得的氢能,将成为人类普遍使用的一种优质、干净的燃料。二氢的应用及展望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氢即用作A—2火箭发动机的液体推进剂。196O年液氢首次用作航天动力燃料。1970年美国发射的“阿波罗”登月飞船使用的起飞火箭也是用液氢作燃料。现在氢已是火箭领域的常用燃料了。对现代航天飞机而言,减轻燃料自重,增加有效载荷变得更为重要。氢的能量密度很高,是普通汽油的3倍,这意味着燃料的自重可减轻2/3,这对航天飞机无疑是极为有利的。今天的航天飞机以氢作为发动机的推进剂,以纯氧作为氧化剂,液氢就装在外部推进剂桶内,构成燃料电池。每次发射需用H21450 m3,重约100t。反应方程式如下:(以氢氧化钠为电解质)负极:2H2-2e-+2OH-=2H2O正极:O2+4e-+2H2O=4OH-总反应方程式:2H2+O2=2H2O现在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种“固态氢”的宇宙飞船。固态氢既作为飞船的结构材料,又作为飞船的动力燃料。在飞行期间,飞船上所有的非重要零件都可以转作能源而“消耗掉”。这样飞船在宇宙中就能飞行更长的时间。戴姆勒·奔驰公司的燃氢汽车在超声速飞机和远程洲际客机上以氢作动力燃料的研究已进行多年,目前已进入样机试飞阶段。在交通运输方面,美、德、法、日等汽车大国早已推出以氢作燃料的示范汽车,并进行了几十万公里的道路试验。其中美、德、法等国是采用氢化金属贮氢,而日本则采用液氢。试验证明,以氢作燃料的汽车在经济性、适应性和安全性三方面均有良好的前景,但目前仍存在贮氢密度小和成本高两大障碍。前者使汽车连续行驶的路程受限制,后者主要是由于液氢供应系统费用过高造成的。美国和加拿大已联手合作拟在铁路机车上采用液氢作燃料。在进一步取得研究成果后,从加拿大西部到东部的大陆铁路上将奔驰着燃用液氢和液氧的机车。氢不但是一种优质燃料,还是石油、化工、化肥和冶金工业中的重要原料和物料。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精炼需要氢,如烃的增氢、煤的气化、重油的精炼等;化工中制氨、制甲醇也需要氢。氢还用来还原铁矿石。用氢制成燃料电池可直接发电。采用燃料电池和氢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其能量转换效率将远高于现有的火电厂。随着制氢技术的进步和贮氢手段的完善,氢能将在21世纪的能源舞台上大展风采。白色污染变燃油城市周围堆积如山的塑料垃圾和交通沿线满地飘飞的塑料食品袋完全可以被回收冶炼为汽油、柴油,北京市梦蓝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公司经过八年多的研究和中试,成功解决了废弃塑料油化技术中焦化、排渣、温控等关键问题,开发出自已的工艺系统和成套设备。国家石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该公司送审的样品进行了严格检测并认定其符合国家对车用燃油的标准和环境排放标准。有关专家建议尽快组织推广应用,以缓解白色污染给人类带来的环境危机。目前,废弃塑料的治理渠道,国内外多年普遍采取填埋和焚烧方式。但研究表明,废弃塑料在填埋后200多年才能分解完毕,且分解过程中会溶出有毒物质,易产生对土质的破坏;焚烧方式会使有害气体释放到空中,影响大气环境及周边环境。北京市梦蓝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有限公司认为把废弃塑料经催化裂解制为燃料,才是物质重新循环同时也能避免二次污染的重要途径,代表着废弃塑料的处理方向。实践证明,采用该项技术设备在连续生产的情况下,日处理废弃塑料能力强、汽柴油转化率高,符合车用燃油的标准和环境排放标准。可燃冰——人类能源的新希望可燃冰的学名为“天然气水合物”,是天然气在0℃和30个大气压的作用下结晶而成的“冰块”。“冰块”里甲烷占80% 9%�未来能源”。1立方米可燃冰可转化为164立方米的天然气和8立方米的水。科学家估计,海底可燃冰分布的范围约4000万平方公里,占海洋总面积的10%,海底可燃冰的储量够人类使用1000年。随着研究和勘测调查的深入,世界海洋中发现的可燃冰逐渐增加,1993年海底发现57处,2001年增加到88处。据探查估算,美国东南海岸外的布莱克海岭,可燃冰资源量多达180亿吨,可满足美国105年的天然气消耗;日本海及其周围可燃冰资源可供日本使用100年以上。据专家估计,全世界石油总储量在2700亿吨到6500亿吨之间。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再有50-60年,全世界的石油资源将消耗殆尽。可燃冰的发现,让陷入能源危机的人类看到新希望。重大战略意义下的联手勘测今年6月2日,26名中德科学家从香港登上德国科学考察船“太阳号”,开始了对南海42天的综合地质考察。通过海底电视观测和海底电视监测抓斗取样,首次发现了面积约430平方公里的巨型碳酸盐岩。中德科学家一致建议,将该自生碳酸盐岩区中最典型的一个构造体命名为“九龙甲烷礁”。其中“龙”字代表了中国,“九”代表了多个研究团体的合作。同位素测年分析表明,“九龙甲烷礁”区域的碳酸盐结壳最早形成于大约5万年前,至今仍在释放甲烷气体。中方首席科学家、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黄永样对此极为兴奋,他说,探测证据表明:仅南海北部的可燃冰储量,就已达到我国陆上石油总量的一半左右;此外,在西沙海槽已初步圈出可燃冰分布面积5242平方公里,其资源估算达1万亿立方米。我国从1993年起成为纯石油进口国,预计到2010年,石油净进口量将增至约1亿吨,2020年将增至2亿吨左右。因此,查清可燃冰家底及开发可燃冰资源,对我国的后续能源供应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黄永样介绍,在未来十年,我国将投入1亿元对这项新能源的资源量进行勘测,有望到2008年前后摸清可燃冰家底,2015年进行可燃冰试开采。战略性与危险性共同打造的“双刃剑”迄今,世界上至少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进行可燃冰的研究与调查勘探。1960年,前苏联在西伯利亚发现了第一个可燃冰气藏,并于1969年投入开发,采气14年,总采气17亿立方米。美国于1969年开始实施可燃冰调查。1998年,把可燃冰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能源列入国家级长远计划,计划到2015年进行商业性试开采。日本关注可燃冰是在1992年,目前,已基本完成周边海域的可燃冰调查与评价,钻探了7口探井,圈定了12块矿集区,并成功取得可燃冰样本。它的目标是在2010年进行商业性试开采。但人类要开采埋藏于深海的可燃冰,尚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有学者认为,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方面,甲烷所起的作用比二氧化碳要大10 20倍。而可燃冰矿藏哪怕受到最小的破坏,都足以导致甲烷气体的大量泄漏。另外,陆缘海边的可燃冰开采起来十分困难,一旦出了井喷事故,就会造成海啸、海底滑坡、海水毒化等灾害。由此可见,可燃冰在作为未来新能源的同时,也是一种危险的能源。可燃冰的开发利用就像一柄“双刃剑”,需要小心对待。新闻背景羌塘盆地可能富藏可燃冰我国冻土专家在对青藏高原进行多年研究后认为,青藏高原羌塘盆地多年冻土区具备形成天然气水合物的温度和压力条件,可能蕴藏着大量可燃冰。据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吴青柏介绍,青藏高原是中纬度最年轻、最高大的高原冻土区,石炭、二叠和第三、第四系沉积深厚,河湖海相沉积中有机质含量高。第四系伴随高原强烈隆升,遭受广泛的冰川——冰缘作用,冰盖压力使下伏沉积物中天然气水合物稳定性增强,尤其是羌塘盆地和甜水海盆地,完全有可能具备可燃冰稳定存在的条件。可燃冰又称天然气水合物,是固态的天然气,广泛存在于地球上,其储量预计是常规储量的6倍。它还是一种清洁的能源,燃烧几乎不会产生有害的污染物质。这使得这种有望成为新世纪能源新贵的物质的开采利用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我国是世界上多年冻土分布面积第三大国,约占世界多年冻土面积的10%,其中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面积占世界多年冻土面积的7%。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分别在祁连山海拔4000米的多年冻土区和青藏高原海拔4700米的五道梁多年冻土区钻探发现类似天然气水合物显示的大量征兆和现象。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和中南石油局第五物探大队在藏北高原羌塘盆地开展的大规模地球物理勘探成果表明 继塔里木盆地后,西藏地区很有可能成为我国21世纪第二个石油资源战略接替区。吴青柏说,目前,他们正在开展寻找可燃冰的计划,大量在实验室内做的前期工作已经开始。此后,他们将分三步研究 在羌塘盆地寻找天然气水合物,如确实存在,则研究其分布规律和基本性质;估算储量和研究开发前景;研究开采工艺和环境保护问题。“但这是一个非常长的阶段,至少要10多年时间。”“一旦找到这些可燃冰,将对我国宏观能源战略决策、开拓新学科领域和保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均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世界屋脊,人类“生命的禁区”。生物学家们这样断言青藏高原。 从内地到西藏,曾经难于上青天。当年文成公主进藏,走了两年多的时间。如今从西宁去拉萨,汽车两天就可跑到了。司机在青藏公路尽可以任随自己的“铁马”松缰驰骋。低速行驶的司机,往往会被同行嘲笑为“老牛慢马”。 文成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天地仿佛因路而缩短了时空距离!1954年,全长1948公里的青藏公路建成通车,这条路始于西宁,经格尔木至拉萨,是祖国内地通往西南边疆的国防、经济主干道。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改造和整治,如今的青藏公路是一条能常年进出西藏的公路,承担着全区85%的客运和90%的货运任务,被誉为西藏的“生命线”。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青藏高原上的筑路条件是怎样的恶劣?又有多少人知道公路工程技术人员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和牺牲,才敲开“禁区”大门,修通这条“通天”之路的呢? 世界性难题 冰峰、雪山、风暴、强烈的紫外线和严重缺氧,是青藏公路的自然标记。特别是格尔木至拉萨段,海拔在4000米至5231米之间,要翻越昆仑山、风火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等大山脉,穿过630多公里生态环境恶劣、地质条件复杂的高原多年冻土区。大片连续、岛状多年冻土及季节冻土,加之高原多年冻土区特有的地下冰、冰堆、冰丘及热融湖塘等不良地质条件,形成了青藏高原独特的地质、地貌。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发展的强音敲响了西藏封闭的大门,毛泽东主席“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号令唤醒了沉寂的青藏高原。1954年11月25日,在人民解放军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青藏公路建成通车。随着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1972年,中央决定改建青藏公路并铺筑沥青路面,修建永久性桥涵。 这是极富挑战的决定,很多人不无怀疑:在高原多年冻土之上铺筑沥青路面,全世界都没有先例,中国人能成功吗? 冻土是一种对温度极为敏感的土体介质。冬季,冻土在负温状态下就像冰块,随温度的降低体积发生剧烈膨胀,顶推上层的路基、路面。而在夏季,冻土随着温度升高而融化,体积缩小后使路基发生沉降,这种周期性变化往往很容易导致路基和路面塌陷、下沉、变形、破裂。 而铺筑沥青路面公路,等于在冻土上既加了一个吸热器又盖了一层封水膜,使冻土在夏天吸热而融化程度加剧,路基内水分不能蒸发,这是一个在公路修筑技术史上始终没有解决的世界性技术难题,缺乏成功技术资料供借鉴。多年来,有着大面积冻土的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国,一直都在苦苦探索解决方法,然而奇迹总没有出现。辽阔的西伯利亚等地留下了一个个筑路专家的深深遗憾。 由于青藏公路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国防地位,保证其畅通,不仅牵动着西藏同胞的心,更牵动着党中央、国务院、交通部领导的心。1973年,交通部成立了青藏公路多年冻土科学研究组,拨专款专项研究青藏公路多年冻土问题。此后,交通部投入大量专项资金,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原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在交通部的直接领导下,系统组织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地区公路修筑成套技术研究,期间集中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系统的科技攻关,取得了一系列有科学价值并受到国际同行广泛关注的研究论文、学术专著和成套应用技术成果,这些不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用于青藏公路的历次改造整治中,为高原腹地青藏公路的整治和改建,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保证了青藏公路的畅通。 禁区探索 对青藏公路多年冻土的研究,凝聚着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关怀与厚爱以及交通部等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和广大交通职工的牺牲奉献。 记者从查阅的大量资料中了解到,几十年来,多位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先后视察过青藏公路;潘琪、钱永昌、黄镇东、张春贤、王展意、李居昌、胡希捷、冯正霖等十几位部领导以及李劲、杨盛福等几十位司局长都对此项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 在交通部的直接领导下,1973年,一个由交通部公路科研所、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设计院等单位专家、学者组成的“青藏公路科研组”踏上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1999年,青藏公路科研组由于经费缺乏等问题举步维艰。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张春贤了解情况后,斩钉截铁地说:“交通部机关的同志就是勒紧裤腰带,也得支持你们把科研进行下去。”一席话让科研人员看到了希望。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冻土研究执行办公室主任李祝龙博士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动不已:“就因这句话,几年来我放弃了几次参与其他项目研究的机会,和同志们一起坚持冻土研究。” 那是怎样的工作环境啊! 三四月,内地春意盎然、鸟语花香,青藏高原却是寒风刺骨、白雪皑皑。气候更像孙悟空的脸,说变就变。一会儿骄阳似火,一会儿狂风大作,一会儿阴雨绵绵,一会儿飞雪漫天,有时一天变幻十几次。有两首民谣道出了这里的险恶环境:“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氧气吃不饱”;“上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 上青藏高原别说搞科研,能够住下来,就是英雄好汉。刚登上高原,科研组近一半的成员都头痛欲裂、气喘吁吁、四肢瘫软、食欲减退。有的人勉强吃上几口饭,也带着黄水呕了出来。 剧烈的高原反应考验着研究人员的毅力,为了公路的畅通,为了几百万藏族同胞的出行,他们在里雪山脚下,搭好帐篷,砌好锅灶,安营扎寨。晚风掀得帐篷“呼啦、呼啦”作响,被窝里冰窟窿似的,加上高原反应,科研人员根本无法入睡。有时帐篷被大风刮倒了,也没有力气起来再支。 在冰天雪地里施工,十字镐刨一下只有一个白点,机械也因缺氧而经常罢工。科研人员只好捡来牛粪,烘烤冻土,用钢钎和铁锤开凿炮眼,进行科研数据收集。 有时风力达到十一二级,“呼呼”地刮个不停,且夹着雪和冰雹,20米以外看不见人,汽车停止了行驶,野驴和黄羊也躲进了深山。但是,为了取得第一手科研资料,观测人员仍要蹒跚于连绵起伏的青藏高原上,冒着被狂风卷走的危险,将仪器脚架放低,跪在地上读数据。他们一米一米地测量沥青路面的变化,凛冽的寒风透过皮大衣,穿过紧身棉袄,直吹到皮肤上。实在熬不住,他们就围着汽车跑几圈,出出汗取暖。冰凉的金属仪器,黏住手能揭掉一层皮,他们把手伸到怀里暖暖后又工作。渴了,没有水就化雪水、化冰水;饿了,就吃冷馍,像石头一样的冰馒头经常啃上半天还没吃上一口。 由于缺氧,科研人员一动脑筋思考问题,头就疼得厉害,但是每天又必须处理大量的数据,研究大量的新问题,头更是像被钢锯来回锯着般疼痛,这给许多人留下了后遗症。其他如心脏病、雪盲症、关节炎等高原病也时刻威胁着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 在漫长荒凉的公路线上,科研人员不仅要经受环境的折磨和体力劳动的考验,还要忍受人迹罕至的痛苦和无聊寂寞的滋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内地,电视已较为普遍,但高原上没有电视信号,他们到附近兵站上看到的电视节目一般都是一两个星期前从西宁录制后送来的。一封信从高原走到内地亲人手中,至少要一个多月时间。许多夫妻长期分居,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说起高原工作,总也离不开一个苦字。高原上的公路科研人员苦得悲壮,苦得心酸。多少人在筑路的进程中忘情拼搏,默默付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武憼民,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国家级专家,23岁投身于青藏高原多年冻土研究,74岁高龄的他现在仍然对冻土情有独钟,几十年来到青藏高原近百次。 汪双杰,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副院长,2002年起涉足青藏高原多年冻土研究,几年来奔波于西安与青藏高原之间,多年冻土研究的论文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 章金钊,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寒区道路工程研究所所长,1984年大学毕业后研究青藏高原多年冻土,20年来绝大部分精力扑在冻土研究上。 李祝龙,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冻土研究执行办公室主任,博士毕业后第一项工作就是研究青藏高原多年冻土。 …… 为了公路的畅通,仅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就先后投入20个勘测设计队,近千人次承担青藏公路工程勘察设计任务。以武憼民、汪双杰、章金钊、李祝龙等为代表的一代代科研人员“献了青春献终生”,武憼民教授患了肺病、章金钊所长患了心脏病、李祝龙博士患了支气管炎……但他们始终凭着一种青藏高原人特有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坚持青藏公路多年冻土问题研究,默默地耕耘生命的土地,默默地奉献人生精华。 由于多年冻土变化相对较慢,一组数据的收集比较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研究周期很长,是个“不容易出科研成果的地方”,科研人员在克服恶劣条件的同时,克服科研成就上的失落感、名誉感显得更为重要。 是什么精神让这些科研人员心甘情愿地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默默奉献呢? 章金钊,这位憨厚的汉子想了半天回答说:“当你在高原时,你会觉得天空离你很近很近,大山毫无保留地向你展示它的一切。在这里,连空气都‘吃’不饱,还有谁会去争夺享乐、待遇、名利呢?再说,我们这些专业的公路勘察设计人员不来研究,谁来研究?” 质朴无华,言情明志。 30余载耕耘成果丰硕 30多年来,几代科研人员一直坚持在高原地区进行现场冻土勘测、试验。为了取得第一手科研基础资料,有时一组人员一天要定时记录下几百个观测点的地温、冻胀、融沉数据。武憼民感叹:“在近两千公里的青藏路上取得的勘察、观测数据资料,足以装满几卡车!” 1973年到1978年,第一期青藏公路科研组经过艰苦努力,在总结工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路基研究中提出了“高原多年冻土地区路基,除少冰冻土、多冰冻土地段及融区外,一般均应遵守宁填不挖”的设计原则,并取得了根据不同地基条件和路基干湿类型,推荐9种路面结构组合类型等成果。这些成果为青藏公路第二次改建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提供了初步依据。 1979年到1984年的第二期青藏公路科研组,提出地下冰的形成和融化是多年冻土区地表变形和工程建筑物破坏的主要原因,地下冰的分布受地质、水文和热物理因素的制约等理论;在路基稳定性研究中,将提高路基作为保护冻土的基本措施;提出了适用于高原多年冻土地区不同地带的9种较为经济合理的路面结构组合和部分计算参数;首次在我国使用无规聚丙烯砾石混合料面层;对多年冻土地区的桩基设计提出了建议等。这些成果基本解决了高原多年冻土地区沥青路面修筑与大中小桥基础设计、施工等技术难题,满足了青藏公路沥青路面改建工程的需要。 1985年至1999年的第三期青藏公路科研组,采用钻探、挖探和地质雷达探测等综合手段,进行多年冻土工程地质勘探,将青藏公路沿线多年冻土划分为高温冻土、低温冻土,并提出以零下5摄氏度为划分界限;首次提出将冻土温度与路基设计原则结合起来,并将其融入路基高度设计中;首次提出高原多年冻土路基在不降低道路服务水平的前提下,通过加强侧向保护,允许冻土上限适量下移的新理论;首次将无机结合料用于高原多年冻土地区的路面结构中;首次将热棒制冷、钢纤维水泥混凝土、EPS隔热层材料、SBR改性沥青、金属波纹管涵等新技术、新材料、新结构引入公路建设。这些研究成果为青藏公路1991年至1999年整治工程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和资料。 2001年至今,结合西部交通科技成套项目“多年冻土地区公路修筑成套技术研究”,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牵头继续对多年冻土进行研究,不仅要解决现阶段多年冻土地区公路建设和养护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其研究成果还将推动多年冻土地区公路建设、管理、养护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出现新情况—技术攻关—解决问题,再出现新情况—再技术攻关—再解决问题……科研人员结合着新要求,运用新技术、新材料,一次次与大自然协商着最好的和谐相处方案。他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收获了丰硕的果实。 由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主持并联合其他科研单位承担的第一期青藏公路科研成果获得交通部重大成果奖。第二期青藏公路科研成果分别获得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交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三期青藏公路科研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技术,获得2001—2002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日前,总结归纳了从1973年到1999年成果的《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地区公路工程》一书正式出版,张春贤部长亲自为该书作序。 目前,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已经大规模应用于青藏公路的历次改建、整治工程,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青藏公路格尔木到拉萨段,上世纪50年代初沿着“顺地爬”的大车路走,需要15天至20天;60年代末70年代初,沿着沙土公路走,需要走8天至10天;80年代末,沿着沥青公路走,还需要4天左右;而90年代末青藏公路整治工程的竣工,把原来的行车平均速度由每小时二三十公里,提高到每小时五六十公里,越野车15个小时左右就可完成1150多公里的行程。青藏公路在青藏铁路建设期间,不仅保证了进出西藏客货运输的正常需求,同时满足了青藏铁路建设期大量设备、材料、生活物资、人员运输需求。据青藏公路五道梁交通量观测站统计,青藏公路交通量比青藏铁路开工前增加了7倍。 为青藏铁路“奠基” 青藏铁路预计2006年7月试运行。但很少有人知道,建设青藏铁路的宏伟计划已提出几十年,之所以一直停留在纸上,冻土问题是“拦路虎”之一。为青藏铁路建设提供冻土方面科学实践依据和理论技术借鉴的,正是青藏公路多年冻土研究的大量基础资料和成功技术。 1999年至2001年,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在进行青藏铁路预可、工可及初步设计期间多次到青藏公路科研组调研,聘请多年在青藏公路科研组工作的武憼民等专家为咨询专家,并于2001年5月以技术服务合同方式购买了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的“高原多年冻土地区公路修筑技术研究”等技术资料。 大半辈子奉献给冻土研究事业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武憼民至今还担任着铁路科学研究院铁路专家咨询组的咨询专家和铁道部大桥局青藏铁路建设高级技术顾问,并多次给青藏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授课,把自己在高原奋斗一辈子积累的高原多年冻土地区工程关键技术理论传授给兄弟单位,为青藏铁路建设工程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作出了贡献。 任重道远 多年冻土有着非常顽皮的特性,受时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它的“脾气”异常复杂和多变,很难让人一下子就摸透。 目前,青藏公路多年冻土区路段在长期恶劣的自然因素和重交通荷载作用下,已出现了裂缝、变形、松散等病害。而多年冻土在我国分布非常广阔,占我国国土面积的5%,约占世界多年冻土总面积的10%,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青藏高原、西部高山和东北大、小兴安岭以及松嫩平原北部,并零星分布在季节冻土内的一些高山上。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重心向中西部倾斜,寒区的大规模开发已势在必行,多年冻土地区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任重而道远。 同时,全球性气候逐步变暖,多年冻土退化日趋严重。因此,更深入系统地开展多年冻土地区公路建设研究,对西部大开发和利用冻土地区国土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尤其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上都有着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科研工作者正沿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继续探索在多年冻土之上修路的奥秘。
世界屋脊,人类“生命的禁区”。生物学家们这样断言青藏高原。 从内地到西藏,曾经难于上青天。当年文成公主进藏,走了两年多的时间。如今从西宁去拉萨,汽车两天就可跑到了。司机在青藏公路尽可以任随自己的“铁马”松缰驰骋。低速行驶的司机,往往会被同行嘲笑为“老牛慢马”。 文成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天地仿佛因路而缩短了时空距离!1954年,全长1948公里的青藏公路建成通车,这条路始于西宁,经格尔木至拉萨,是祖国内地通往西南边疆的国防、经济主干道。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改造和整治,如今的青藏公路是一条能常年进出西藏的公路,承担着全区85%的客运和90%的货运任务,被誉为西藏的“生命线”。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青藏高原上的筑路条件是怎样的恶劣?又有多少人知道公路工程技术人员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和牺牲,才敲开“禁区”大门,修通这条“通天”之路的呢? 世界性难题 冰峰、雪山、风暴、强烈的紫外线和严重缺氧,是青藏公路的自然标记。特别是格尔木至拉萨段,海拔在4000米至5231米之间,要翻越昆仑山、风火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等大山脉,穿过630多公里生态环境恶劣、地质条件复杂的高原多年冻土区。大片连续、岛状多年冻土及季节冻土,加之高原多年冻土区特有的地下冰、冰堆、冰丘及热融湖塘等不良地质条件,形成了青藏高原独特的地质、地貌。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发展的强音敲响了西藏封闭的大门,毛泽东主席“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号令唤醒了沉寂的青藏高原。1954年11月25日,在人民解放军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青藏公路建成通车。随着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1972年,中央决定改建青藏公路并铺筑沥青路面,修建永久性桥涵。 这是极富挑战的决定,很多人不无怀疑:在高原多年冻土之上铺筑沥青路面,全世界都没有先例,中国人能成功吗? 冻土是一种对温度极为敏感的土体介质。冬季,冻土在负温状态下就像冰块,随温度的降低体积发生剧烈膨胀,顶推上层的路基、路面。而在夏季,冻土随着温度升高而融化,体积缩小后使路基发生沉降,这种周期性变化往往很容易导致路基和路面塌陷、下沉、变形、破裂。 而铺筑沥青路面公路,等于在冻土上既加了一个吸热器又盖了一层封水膜,使冻土在夏天吸热而融化程度加剧,路基内水分不能蒸发,这是一个在公路修筑技术史上始终没有解决的世界性技术难题,缺乏成功技术资料供借鉴。多年来,有着大面积冻土的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国,一直都在苦苦探索解决方法,然而奇迹总没有出现。辽阔的西伯利亚等地留下了一个个筑路专家的深深遗憾。 由于青藏公路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国防地位,保证其畅通,不仅牵动着西藏同胞的心,更牵动着党中央、国务院、交通部领导的心。1973年,交通部成立了青藏公路多年冻土科学研究组,拨专款专项研究青藏公路多年冻土问题。此后,交通部投入大量专项资金,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原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在交通部的直接领导下,系统组织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地区公路修筑成套技术研究,期间集中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系统的科技攻关,取得了一系列有科学价值并受到国际同行广泛关注的研究论文、学术专著和成套应用技术成果,这些不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用于青藏公路的历次改造整治中,为高原腹地青藏公路的整治和改建,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保证了青藏公路的畅通。 禁区探索 对青藏公路多年冻土的研究,凝聚着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关怀与厚爱以及交通部等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和广大交通职工的牺牲奉献。 记者从查阅的大量资料中了解到,几十年来,多位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先后视察过青藏公路;潘琪、钱永昌、黄镇东、张春贤、王展意、李居昌、胡希捷、冯正霖等十几位部领导以及李劲、杨盛福等几十位司局长都对此项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 在交通部的直接领导下,1973年,一个由交通部公路科研所、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设计院等单位专家、学者组成的“青藏公路科研组”踏上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1999年,青藏公路科研组由于经费缺乏等问题举步维艰。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张春贤了解情况后,斩钉截铁地说:“交通部机关的同志就是勒紧裤腰带,也得支持你们把科研进行下去。”一席话让科研人员看到了希望。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冻土研究执行办公室主任李祝龙博士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动不已:“就因这句话,几年来我放弃了几次参与其他项目研究的机会,和同志们一起坚持冻土研究。” 那是怎样的工作环境啊! 三四月,内地春意盎然、鸟语花香,青藏高原却是寒风刺骨、白雪皑皑。气候更像孙悟空的脸,说变就变。一会儿骄阳似火,一会儿狂风大作,一会儿阴雨绵绵,一会儿飞雪漫天,有时一天变幻十几次。有两首民谣道出了这里的险恶环境:“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氧气吃不饱”;“上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 上青藏高原别说搞科研,能够住下来,就是英雄好汉。刚登上高原,科研组近一半的成员都头痛欲裂、气喘吁吁、四肢瘫软、食欲减退。有的人勉强吃上几口饭,也带着黄水呕了出来。 剧烈的高原反应考验着研究人员的毅力,为了公路的畅通,为了几百万藏族同胞的出行,他们在里雪山脚下,搭好帐篷,砌好锅灶,安营扎寨。晚风掀得帐篷“呼啦、呼啦”作响,被窝里冰窟窿似的,加上高原反应,科研人员根本无法入睡。有时帐篷被大风刮倒了,也没有力气起来再支。 在冰天雪地里施工,十字镐刨一下只有一个白点,机械也因缺氧而经常罢工。科研人员只好捡来牛粪,烘烤冻土,用钢钎和铁锤开凿炮眼,进行科研数据收集。 有时风力达到十一二级,“呼呼”地刮个不停,且夹着雪和冰雹,20米以外看不见人,汽车停止了行驶,野驴和黄羊也躲进了深山。但是,为了取得第一手科研资料,观测人员仍要蹒跚于连绵起伏的青藏高原上,冒着被狂风卷走的危险,将仪器脚架放低,跪在地上读数据。他们一米一米地测量沥青路面的变化,凛冽的寒风透过皮大衣,穿过紧身棉袄,直吹到皮肤上。实在熬不住,他们就围着汽车跑几圈,出出汗取暖。冰凉的金属仪器,黏住手能揭掉一层皮,他们把手伸到怀里暖暖后又工作。渴了,没有水就化雪水、化冰水;饿了,就吃冷馍,像石头一样的冰馒头经常啃上半天还没吃上一口。 由于缺氧,科研人员一动脑筋思考问题,头就疼得厉害,但是每天又必须处理大量的数据,研究大量的新问题,头更是像被钢锯来回锯着般疼痛,这给许多人留下了后遗症。其他如心脏病、雪盲症、关节炎等高原病也时刻威胁着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 在漫长荒凉的公路线上,科研人员不仅要经受环境的折磨和体力劳动的考验,还要忍受人迹罕至的痛苦和无聊寂寞的滋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内地,电视已较为普遍,但高原上没有电视信号,他们到附近兵站上看到的电视节目一般都是一两个星期前从西宁录制后送来的。一封信从高原走到内地亲人手中,至少要一个多月时间。许多夫妻长期分居,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说起高原工作,总也离不开一个苦字。高原上的公路科研人员苦得悲壮,苦得心酸。多少人在筑路的进程中忘情拼搏,默默付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武憼民,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国家级专家,23岁投身于青藏高原多年冻土研究,74岁高龄的他现在仍然对冻土情有独钟,几十年来到青藏高原近百次。 汪双杰,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副院长,2002年起涉足青藏高原多年冻土研究,几年来奔波于西安与青藏高原之间,多年冻土研究的论文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 章金钊,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寒区道路工程研究所所长,1984年大学毕业后研究青藏高原多年冻土,20年来绝大部分精力扑在冻土研究上。 李祝龙,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冻土研究执行办公室主任,博士毕业后第一项工作就是研究青藏高原多年冻土。 …… 为了公路的畅通,仅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就先后投入20个勘测设计队,近千人次承担青藏公路工程勘察设计任务。以武憼民、汪双杰、章金钊、李祝龙等为代表的一代代科研人员“献了青春献终生”,武憼民教授患了肺病、章金钊所长患了心脏病、李祝龙博士患了支气管炎……但他们始终凭着一种青藏高原人特有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坚持青藏公路多年冻土问题研究,默默地耕耘生命的土地,默默地奉献人生精华。 由于多年冻土变化相对较慢,一组数据的收集比较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研究周期很长,是个“不容易出科研成果的地方”,科研人员在克服恶劣条件的同时,克服科研成就上的失落感、名誉感显得更为重要。 是什么精神让这些科研人员心甘情愿地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默默奉献呢? 章金钊,这位憨厚的汉子想了半天回答说:“当你在高原时,你会觉得天空离你很近很近,大山毫无保留地向你展示它的一切。在这里,连空气都‘吃’不饱,还有谁会去争夺享乐、待遇、名利呢?再说,我们这些专业的公路勘察设计人员不来研究,谁来研究?” 质朴无华,言情明志。 30余载耕耘成果丰硕 30多年来,几代科研人员一直坚持在高原地区进行现场冻土勘测、试验。为了取得第一手科研基础资料,有时一组人员一天要定时记录下几百个观测点的地温、冻胀、融沉数据。武憼民感叹:“在近两千公里的青藏路上取得的勘察、观测数据资料,足以装满几卡车!” 1973年到1978年,第一期青藏公路科研组经过艰苦努力,在总结工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路基研究中提出了“高原多年冻土地区路基,除少冰冻土、多冰冻土地段及融区外,一般均应遵守宁填不挖”的设计原则,并取得了根据不同地基条件和路基干湿类型,推荐9种路面结构组合类型等成果。这些成果为青藏公路第二次改建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提供了初步依据。 1979年到1984年的第二期青藏公路科研组,提出地下冰的形成和融化是多年冻土区地表变形和工程建筑物破坏的主要原因,地下冰的分布受地质、水文和热物理因素的制约等理论;在路基稳定性研究中,将提高路基作为保护冻土的基本措施;提出了适用于高原多年冻土地区不同地带的9种较为经济合理的路面结构组合和部分计算参数;首次在我国使用无规聚丙烯砾石混合料面层;对多年冻土地区的桩基设计提出了建议等。这些成果基本解决了高原多年冻土地区沥青路面修筑与大中小桥基础设计、施工等技术难题,满足了青藏公路沥青路面改建工程的需要。 1985年至1999年的第三期青藏公路科研组,采用钻探、挖探和地质雷达探测等综合手段,进行多年冻土工程地质勘探,将青藏公路沿线多年冻土划分为高温冻土、低温冻土,并提出以零下5摄氏度为划分界限;首次提出将冻土温度与路基设计原则结合起来,并将其融入路基高度设计中;首次提出高原多年冻土路基在不降低道路服务水平的前提下,通过加强侧向保护,允许冻土上限适量下移的新理论;首次将无机结合料用于高原多年冻土地区的路面结构中;首次将热棒制冷、钢纤维水泥混凝土、EPS隔热层材料、SBR改性沥青、金属波纹管涵等新技术、新材料、新结构引入公路建设。这些研究成果为青藏公路1991年至1999年整治工程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和资料。 2001年至今,结合西部交通科技成套项目“多年冻土地区公路修筑成套技术研究”,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牵头继续对多年冻土进行研究,不仅要解决现阶段多年冻土地区公路建设和养护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其研究成果还将推动多年冻土地区公路建设、管理、养护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出现新情况—技术攻关—解决问题,再出现新情况—再技术攻关—再解决问题……科研人员结合着新要求,运用新技术、新材料,一次次与大自然协商着最好的和谐相处方案。他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收获了丰硕的果实。 由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主持并联合其他科研单位承担的第一期青藏公路科研成果获得交通部重大成果奖。第二期青藏公路科研成果分别获得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交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三期青藏公路科研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技术,获得2001—2002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日前,总结归纳了从1973年到1999年成果的《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地区公路工程》一书正式出版,张春贤部长亲自为该书作序。 目前,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已经大规模应用于青藏公路的历次改建、整治工程,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青藏公路格尔木到拉萨段,上世纪50年代初沿着“顺地爬”的大车路走,需要15天至20天;60年代末70年代初,沿着沙土公路走,需要走8天至10天;80年代末,沿着沥青公路走,还需要4天左右;而90年代末青藏公路整治工程的竣工,把原来的行车平均速度由每小时二三十公里,提高到每小时五六十公里,越野车15个小时左右就可完成1150多公里的行程。青藏公路在青藏铁路建设期间,不仅保证了进出西藏客货运输的正常需求,同时满足了青藏铁路建设期大量设备、材料、生活物资、人员运输需求。据青藏公路五道梁交通量观测站统计,青藏公路交通量比青藏铁路开工前增加了7倍。 为青藏铁路“奠基” 青藏铁路预计2006年7月试运行。但很少有人知道,建设青藏铁路的宏伟计划已提出几十年,之所以一直停留在纸上,冻土问题是“拦路虎”之一。为青藏铁路建设提供冻土方面科学实践依据和理论技术借鉴的,正是青藏公路多年冻土研究的大量基础资料和成功技术。 1999年至2001年,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在进行青藏铁路预可、工可及初步设计期间多次到青藏公路科研组调研,聘请多年在青藏公路科研组工作的武憼民等专家为咨询专家,并于2001年5月以技术服务合同方式购买了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的“高原多年冻土地区公路修筑技术研究”等技术资料。 大半辈子奉献给冻土研究事业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武憼民至今还担任着铁路科学研究院铁路专家咨询组的咨询专家和铁道部大桥局青藏铁路建设高级技术顾问,并多次给青藏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授课,把自己在高原奋斗一辈子积累的高原多年冻土地区工程关键技术理论传授给兄弟单位,为青藏铁路建设工程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作出了贡献。 任重道远 多年冻土有着非常顽皮的特性,受时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它的“脾气”异常复杂和多变,很难让人一下子就摸透。 目前,青藏公路多年冻土区路段在长期恶劣的自然因素和重交通荷载作用下,已出现了裂缝、变形、松散等病害。而多年冻土在我国分布非常广阔,占我国国土面积的5%,约占世界多年冻土总面积的10%,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青藏高原、西部高山和东北大、小兴安岭以及松嫩平原北部,并零星分布在季节冻土内的一些高山上。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重心向中西部倾斜,寒区的大规模开发已势在必行,多年冻土地区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任重而道远。 同时,全球性气候逐步变暖,多年冻土退化日趋严重。因此,更深入系统地开展多年冻土地区公路建设研究,对西部大开发和利用冻土地区国土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尤其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上都有着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科研工作者正沿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继续探索在多年冻土之上修路的奥秘
某位主持铁路设计的高人介绍过,忘了是谁了冻土问题是在春季(或夏季,我对气候不太了解)冻土解冻时土壤中冰融化造成路基不稳那想办法让路基里的冰不融化就行了冰融化是因为热量被积聚在土壤表层所以设计时在路基下面每隔一段距离打个通风洞让风进入带走热量而高原上的风大气温又低的这样路基就不会融化了自然就没问题了这个是在央10的<人物>(或是<大家>,抱歉记不清了)里看的介绍的是一个设计师他们的灵感是来自自己住的房间的稳定,因为冻土问题他们的房子每年也要受影响你可以找个去仔细看下,节目里介绍的比较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