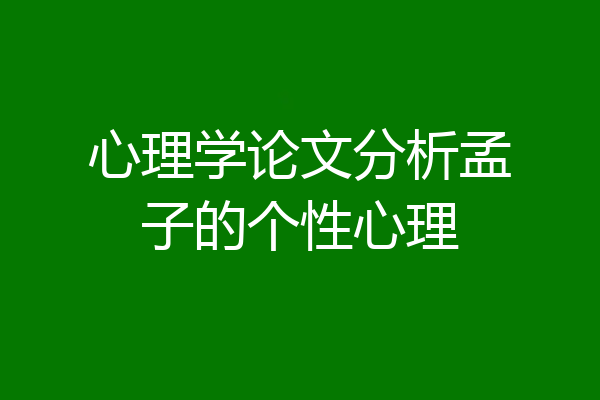xiaoxiao87
xiaoxiao87
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是我国学术史上未曾解除的悬案,两说对峙了2000多年,相持不下。孟子说:人性皆善,主张仁义化民;宋儒承袭其说,开出理学一派,创出不少迂谬的议论。荀子生在孟子之后,反对他的学说,说人性恶,主张用礼制裁它:他的学生韩非,认为礼的制裁力弱,不如法律的制裁力强,于是变而为刑名之学,其弊流于刻薄寡恩。于是儒法两家,互相排斥,学说上、政治上生?出许多冲突。究竟孟、荀两说,孰得孰失?我们非把它彻底研究清楚不可。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这个说法,是有破绽的。我们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她亲生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抱着他吃饭,他就伸手来拖母亲的碗,如不提防,就会落地打烂。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又母亲手中拿一糕饼,他见了,就伸手来拖,如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他立刻会伸手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他的口中。又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小孩在母亲怀中,吃乳吃糕饼,哥哥走近前,他就用手推他打他。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敬兄?五洲万国的小孩,无一不如此。事实上,已经有这种现象,孟子的性善说,难道不是显然露出破绽?所有基于性善说发出的议论,订出的法令制度,就有了不少流弊。但是孟子所说“孩提爱亲,少长敬兄”,究竟从什么地方生出来?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只好用研究物理学的法子去研究。大凡人的天性,以“我”为本位,我与母亲相对,小儿只知有我,所以从母亲口中将糕饼取出。放在自己口中。母亲是哺乳我的人,哥哥是分我食物的人,把母亲与哥哥比较,觉得母亲与我更接近,所以小儿就爱母亲。稍微长大后,与邻人相遇,把哥哥与邻人比较,觉得哥哥与我更接近,自然就爱哥哥。由此推论,走到别的乡,就爱邻人;走到别的省,就爱本省的人;走到外国,就爱本国的人。我们细加研究,就知道孟子说的爱亲敬兄,都是从为我之心流露出来的。可见孟子所说爱双亲敬兄长,内部藏了一个“我”字,不过没有说出来;假若补个“我”字进去,绘图一看就自然明白了。如图一,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亲,第三圈是兄,第四圈是邻人,第五圈是本省人,第六圈是本国人,第七圈是外国人。这个图,就是人心的现象。这个现象,很像物理学上讲的磁场一样,所以牛顿所创造的公理,可运用于心理学。但上图是否正确,还须加以考验。假如暮春三月,我们邀约二三友人出外游玩,看见山明水秀,心中非常愉快,走到山水粗俗的地方,心中就不免烦闷,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山水是物,我也是物,物我本是一体,所以物的样子好,心中就愉快;物的样子不好,心中就不愉快。又走到一地方,见地上有许多碎石头。碎石之上,落花飘零,我心中对于落花不胜悲伤,而对于碎石头就不怎么注意。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石头是无生命的物体,花与我同样是有生命的物体,所以常常有人作落花诗、落花赋,而不作碎石歌、碎石行:古今诗词中,吟咏落花的诗中写得空前绝后的,没有一首不是连同人生来描写的。假如落花的上面横卧一条即将死去的狗,发出哀鸣宛转的呜咽声,令人震耳惊心,立刻就把悲感落花的心绪打断。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花是植物,狗与我同是动物,所以不知不觉,对于狗特别表示同情。又假如路途中看到一条凶恶的猛狗拦着一个人狂咬,那个人拿着木棍乱打,面对着人与狗相争的情况,我们只有帮人的忙,绝对不会帮狗的忙。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狗是犬类,我与那人同是人类,所以不知不觉,对于人更表示同情感。我与友人分手回家,刚走进家门,便有人跑来报告:你先前那个友人,走在街上,同一个人在打架,正打得难分难解。我听了立即奔往营救,本来同是人与人打架,因为友谊的关系,所以我只能营救友人。我把友人拉到我的书房。询问他打架的原因,正在倾耳细听,忽然房子倒下来,我抢先急忙逃出门外,回头再喊友人说:“你还不跑出来吗?”请问一见房子倒下,为什么不喊友人跑。必定等待自己跑出门了,才回头喊友人呢?这就是人的天性,以“我”为本位的明证。我们把上述事实再绘如图二: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第四圈是狗,第五圈是花,第六圈是石。这中间的规律是:距离我越远。爱的情感越减少,爱的情感和距离成反比。此图与前图是一样的。此图所设的境界与前图完全不相同,但得出的结果还是一样。足以证明天然的道理实在是如此。现在再总括的说:大凡有两个物体同时呈现于我的面前,我心里一时来不及安排,自然会以“我”为本位,看距离我的关系的远近,决定爱的情感的厚薄,这正和地心吸引力没有区别。力有离心向心两种,图一层层向外发展,是离心力现象;图二层层向内收缩,是向心力现象。孟子站在图一里面,向外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孩提爱亲,稍长爱兄,再进则爱邻人,爱本省人。爱本国人,层层放大;如果再放大,还可放至爱人类爱物类为止,因此断定人的性善。所以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举斯心,加诸彼。”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性善扩而充之。孟子喜言诗,诗是宣导人的意志的,凡人只要习于诗,自然把这种善性发挥出来,这就是孟子立说的本旨,所以图一可看为孟子的性善图。荀子站在图二外面。向内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看见花就忘了石,看见犬就忘了花,看见人就忘了犬,看见朋友,就忘了他人,层层缩小,及至房子倒下来。赤裸裸的只有一个我,连最好的朋友都忘去了,因此断定人的性恶。所以说:“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又说:“拘木待檗栝蒸矫然后直。钝金待砻厉然后利。”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恶性抑制下去。荀子喜言礼,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凡人只要习于礼,这种恶性自然不会发现出来。这就是荀子立说的本旨。故图二可看为荀子性恶图。一、二两图,本是一样,但从孟子、荀子眼中看来,就成了性善、性恶,极端相反的两种说法,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并且有时候,同是一事,孟子看来是善,荀子看来是恶,那就更奇怪了。例如我听见我的朋友同一个人打架,我总愿我的朋友打胜,请问这种心理是善是恶?假如我们去问孟子,孟子一定说道:这明明是性善的表现,怎么这样说呢?友人与他人打架,与你毫无关系,而你希望他打胜,此乃爱友之心,不知不觉,从天性中自然流出。古圣贤明胞物与,无非基于一念之爱而已。所以你这种爱友之心,务须把他扩充起来。假如我们去问荀子,荀子一定说道:这明明是性恶的表现,怎么这样说呢?你的朋友是人,他人也是人,你不救他人而救友人,此乃自私之心,不知不觉,从天性中自然流出。威廉第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无非起于一念之私而已。所以你这种自私之心,务须把它抑制下去。上面所举,同是一事,而有极端相反的两种说法,两种说法,都是颠扑不灭,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只须绘图一看,就自然明白了。如图三: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人,第三圈是他人,请问友字这个圈,是大是小?孟子在里面画一个我字之小圈,与之比较,就说它是大圈。荀子在外面画一个人字之大圈,与之比较,就说它是小圈。若问二人的理由,孟子说:“友字这个圈,乃是把画我字小圈的两脚规张开来画成的,怎么不是大圈?顺着这种趋势,必会越张越大,所以应该扩充之,使它再画大点。”荀子说:“友字这个圈,乃是把人字大圈的两脚规收拢来画成的,怎么不是小圈?顺着这种趋势,必定越收越小,所以应该制止它,不使它再画小。”孟荀之争,就是这样。营救友人一事,孟子提个我字,与友字相对,说是性善的表现;荀子提个人字,与友字相对。说是性恶的表现。我们绘图观之,友字这个圈,只能说它是个圈,不能说它是大圈,也不能说它是小圈。所以营救友人一事,只能说是人类天性中一种自然现象,不能说它是善,也不能说它是恶。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乃是一种诡辩,二人生当战国,染得有点策士诡辩气习,我辈不可不知。荀子以后,主张性恶者很少。孟子的性善说,在我国很占势力,我们可把他的学说再加研究。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个说法,也是性善说的重要根据。但我们要请问:这章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何以下文只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是何道理?性善说之有破绽。就在这个地方。怵惕是惊惧之意,譬如我们共坐谈心的时候,忽见前面有一人,提一把白亮亮的刀。追杀一人,我们一齐吃惊,各人心中都要跳几下,这就是怵惕。因为人人都有怕死的天性,看见刀,仿佛是杀我一般,所以心中会跳,所以会怵惕。我略一审视,晓得不是杀我,是杀别人,登时就把怕死的念头放大,化我身为被追之人,对于他起一种同情心。想救护他,这就是恻隐。由此知道,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没有怵惕,就不会有恻隐,可以说:恻隐二字,仍是发源于我字。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共有三物:一是我,二是孺子,三是井。绘之为图四,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孺子,第三圈是井。我与孺子,同是人类,井是无生物。见孺子将入井,突有一“死”的现象呈于我们面前,所以会怵惕,登时对于孺子表同情,生出恻隐心,想去救护他。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我们须知:怵惕是自己畏死,恻隐是怜悯他人的死,所以恻隐可称之为仁,怵惕不能称之为仁,所以孟子把怵惕二字摘下来丢了。但有一个问题,假如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请问此心做何状态?不消说:这刹那间,只有怵惕而无恻隐。只能顾及我的死,不能顾及孺子。不是不爱孺子,是变生仓猝,顾不及。一定是我身离开了危险,神志略定,恻隐心才能发出。可惜孟子当日,未把这一层提出来研究。留下破绽,才生出宋儒理学一派,创出许多迂谬的议论。孟子所说的爱亲敬兄,所说的怵惕恻隐,内部都藏有一个我字,但他总是从第二圈说起,对于第一圈的我,则略而不言。杨子为我,算是把第一圈明白揭出了,但他却专在第一圈上用功,第二以下各圈,置之不管;墨子摩顶放踵,是抛弃了第一圈的我。他主张爱无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杨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们两家。都不知道: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荀子说是层层缩小,就不免流于一偏了。我们取杨子的我字,作为中心点,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我们综合孟、荀的学说而断之日:孟子所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一类话,没有错,但不能说是性善,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荀子说“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一类话,也没有错,但不能说是性恶,也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但学者服从谁呢?我说:我们知道,人的天性,能够孩提爱亲,稍长敬兄,就把这种心理扩充了。适用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说法。我们又知道:人的天性,能够减少对父母的孝,减少了对朋友的诚信,就把这种心理纠正过来,适用荀子“拘木待檗栝蒸矫然后直,钝金待砻厉然后利“的说法。孟荀的争论,只是性善、性恶名词上的争论。实际他二人所说的道理,都不错,都可以在实际中看到。我以为我们无须问人性是善是恶。只须创一公例:“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把牛顿的吸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心理学上,心理物理,打成一片而研究之,岂不简便而明确吗?何苦将性善性恶这类的名词,没完没了地争论不休。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其时游说之风最盛,往往立谈而取卿相之荣,其游说各国之君,颇似后世人主临轩策士,不过是口试,不是笔试罢了。一般策士,习于揣摹之术。先用一番工夫,把事理研究透彻了,出而游说,总是把真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成为偏激之论,愈偏激则愈新奇,愈足以耸人听闻。苏秦说和六国,讲出一个道理,风靡天下;张仪解散六国,反过来讲出一个道理,也是风靡天下。孟荀生当其时,染有此种气习。本来人性是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从整个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论,日性善,其说新奇可喜,于是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荀子出来,把孟子遗下的那半面,揭出来说性恶,又成一种新奇之说,在学术界,又树一帜。从此性善说和性恶说,遂成为对峙的二说。宋儒笃信孟子的说法,根本上就误了。然而孟子尚不甚误,宋儒则大误,宋儒言性,完全与孟子违反。请问:宋儒的学说乃是以孟子所说(一)“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二)“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两个根据为出发点,何至会与孟子的说法完全违反?现说明如下: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共有三个场所:(一)一个小孩,一个母亲,一个外人,同在一处,小孩对于母亲,特别亲爱,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母亲。(二)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小孩对于母亲依恋不舍,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母亲。(三)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发生了利害冲突,例如有一块糕饼,母亲吃了,小孩就没得吃,母亲把它放在口中。小孩就伸手取来,放在自己口中。这个时候,断不能说小孩爱母亲。孟子言性善,舍去第三种不说,单说前两种,讲得头头是道。荀子言性恶,舍去前两种不说,单说第三种,也讲得头头是道。所以他二人的学说,本身上是不发生冲突的。宋儒把前两种和第三种一块讲,又不能把他贯通为一,于是他们的学说,本身上就发生冲突了。宋儒笃信孟子孩提爱亲之说,忽然发现了小孩会抢母亲口中糕饼,而世间小孩,无一不是如此,也不能不说是人之天性,求其故而不得,遂创一名词叫做:“气质之性。”假如有人问道:小孩何以会爱亲?说道“义理之性”也。问:即爱亲矣,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说道“气质之性”也。好好一个人性,无端把他剖而为二,因此全部宋学,就荆棘丛生,迂谬百出了……朱子出来,注孟子书上天生蒸民一节,简直明明白白说道:“程子之说,与孟子不同,以事理考之,程子更严密。”他们自家就这样说,难道不是显然违反孟子吗?孟子知道:一般人有怕死的天性,见孺子将入井,就会发生恐惧心,跟着就会把恐惧心扩大,而生恻隐心,因教人把此心再扩大,推至四海,这是孟子立说的本旨。恐惧是自己怕死,不能说是仁,恻隐是怜悯他人的死。方能说是仁,所以下文摘去恐惧二字,只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孟子本没有错,不过文字简略,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恐惧扩大出来的”。不料宋儒读书不求甚解,见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一句,以为人的天性一发出来,就是恻隐,忘却上面还有恐惧二字,把凡人有怕死的天性一笔抹杀。我们试读宋儒全部作品,所谓语录也,文集也,集注也,只是发挥恻隐二字,对于恐惧二字置之不理,这是他们最大的误点。但是宋儒毕竟是好学深思的人,心想:小孩会夺母亲口中糕饼,究竟是什么道理呢?一旦读《礼记》上的《乐记》,见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等语,恍然大悟道:糕饼就是物,从母亲口中夺出是感于物而动。于是创出“去物欲”之说,叫人切不可为外物所诱惑。宋儒又继续研究下去,研究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头,只是赤裸裸的怕死之心,并无所谓恻隐,于是诧异道:明明看见孺子将入井,为什么恻隐之心不出来,反发出一个自己畏死之念?要说此念是物欲。此时并没有外物来引诱,完全从内心发出,这是什么道理?继而又醒悟道:怕死之念,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抢母亲口中糕饼,也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我就是人,遂用人欲二字代替物欲二字。告其门弟子说: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就是恻隐,尧舜和孔孟诸人,满腔子是恻隐,无时无地不然,我辈有时候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是怕死之心,不是恻隐之心,此气质之性为之也,人欲掩盖它了,你们须用一番“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才可以成为孔孟,成为尧舜。天理是什么?是恻隐之心,就是所谓仁也。这种说法,即是程朱全部学说的主旨。于是,程子门下的第一个高足弟子谢上蔡。就照着程门教条做去,每日在高石阶上跑来跑去,练习不动心,以为我不怕死,人欲去尽,天理自然流行,就成为满腔子是恻隐了。像他们这样的“去人欲,存天理”,明明是“去恐惧,存恻隐”。试想:恻隐是恐惧的放大形,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恐惧既无,恻隐何有?我身既无,儒子何有?我既不怕死,就叫我自己入井,也是无妨。见孺子入井,哪里会有恻隐?程子的门人。专做“去人欲”的工作。即是专做“去恐惧”的工作。门人中有个叫吕原明的。乘轿渡河坠水。跟从的人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恐惧的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宋,朱子的好友张南轩。其父张魏公,符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张魏公也是去了恐惧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孟子说:“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撄冠而救之可也。”吕原明的随从、张魏公的兵士,岂非同室之人?他们这种举动,岂不是显违孟子家法?大凡去了恐惧的人。必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贼,往往身临刑场,谈笑自若。是其明证。程子是去了恐惧的人。所以发出“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议论。所以戴东原日:宋儒以理杀人。有人问道:恐惧心不除去,遇着大患临头,我只有个怕死之心,怎能干救国救民的大事呢?我说:这却不然,在孟子是有办法的,他的方法,只是培养仁义二字,平日专用培养仁义的工夫,见之真,守之笃,一旦身临大事,义之所在,自然会奋不顾身的做去。所以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平日培养仁义,把这种至大至刚的浩气养得完全全全的,并不像宋儒去人欲,平日身蹈危阶,把那种怕死之念去得干干净净的。孟子不动心,宋儒也不动心。孟子的不动心,从积极地培养仁义得来;宋儒的不动心,从消极地去欲得来,所走途径,完全相反。孟子的学说:以我字为出发点,所讲的爱亲敬兄和恐惧恻隐,内部都藏有一个我字。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是我,其也是我,处处不脱我字,孟子因为重视我字,才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才有“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说法。程子倡“去人欲”的学说,专作剥削我字的工作,所以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孟子业已判决了的定案。韩愈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程子极力称赏此语,公然推翻孟子定案,难道不是孟门叛徒?他们还要自称继承孟子道统,真百思不解。孔门学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利己利人,合为一事。杨子为我。专讲利己,墨子兼爱,专讲利人。这都是把一整个道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学术界公例:“学说愈偏则愈新奇,愈受人欢迎。”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孔子死后,不到百年,他讲学的地方,全被杨、墨夺去,孟子奋臂而起,力辟杨墨,发挥孔子推己及人的学说。在我们看来,杨子为我,只知自利,墨子兼爱,专门利人,墨子的价值,似乎在杨子之上。等到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反把杨子放在墨子之上,认为离儒家更近,于此可见孟子之重视我字。杨子拔一毛而有利天下不做也,极端尊重我字,但杨子同时尊重他人的我。其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不许他人拔我一毛,同时我也不拔他人一毛,其说最精,所以孟子认为高出墨子之上。但由杨子的学说,只能做到利己而无损于人,与孔门仁字不合。仁从二人,是人与我中间的工作。杨子学说,失去人我的关联,所以被孟子所驳斥。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其要点是损已利人,与孔门义字不合。义字从羊从我,故义字之中有个我字在;羊者祥也,美善二字皆从羊。由我择其最美最善者行之,是之谓义。事在外,选择的人是我,故日义内也。墨子兼爱,知有人不知有我。所以孟子极端排斥之。但墨子的损我,是牺牲我一人,以救济普天下之人,知有众人的我,不知自己的我,这是菩萨心肠。其说只能行于少数圣贤,不能行之于人人,与孔门中庸之道,人己两利的宗旨有异,自孟子观之,其说反在杨子之下。为什么呢?因其失去图一图二的中心点。孟子说:“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一本是什么?是中心点。墨子的损我,是我自愿损之,非他人所能够干预的;墨子善守,公输盘九攻之,墨子九御之,我不想自损,他人固无如我何也。墨子摩项放踵,与“腓无跋,胫无毛”的大禹有什么区别?与“栖栖不已,席不暇暖”的孔子有什么区别?孟子极力贬斥他的原因,无非学术上门户之见而已。但墨子摩顶放踵,所损者外形也,宋儒去人欲,则损及内心矣,其说岂不更出墨子下?孔门之学,推己及人,宋儒也推己及人,无如其所推而及之者,则为我甘饿死以殉夫,于是希望天下的妇人,皆饿死以殉夫,我甘诛死以殉君,遂欲天下之臣子,皆诛死以殉君,仁不如墨子,义不如杨子。孟子已斥杨墨为禽兽矣,使见宋儒,未知作何评语?综而言之:孟子言性善,宋儒也言性善,实则宋儒的学说,完全与孟子违反,其区分之点在于:“孟子之学说,不损伤我字,宋儒之学说,损伤我字。”再者宋儒还有去私欲的说法,究竟私是个什么东西?去私是怎么一回事?也非把他研究清楚不可。私字的意义,许氏说文,是引韩非的话来解释的。韩非原文:“仓颉作书,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环即是圈子,私字古文作厶,篆文作厶,画一个圈。公字从八从厶,八是把一个东西破为两块的意思,故八者背也。“背私谓之公”,就是说:把圈子打破了,才称之为公。假使我们只知有我,不顾妻子,环自身画一个圈,妻子必说我徇私,我于是把我字这个圈撤去,环妻子画一圈:但弟兄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环弟兄画一个圈;但邻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弟兄这个圈撤去,环邻人画一个圈;但国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邻人这个圈撤去,环国人画一个圈;但他国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这只好把本国人这个圈子撤了,环人类画一个大圈,才可谓之公。但还不能谓之公,假使世界上动植矿都会说话,禽兽一定说:你们人类为什么要宰杀我们?未免太自私了。草木问禽兽道:你为什么要吃我们?你也未免自私。泥土沙石问草木道: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吸收养料?你草木未免自私。并且泥土沙石可以问地心道:你为什么把我们向你中心牵引?你未免自私。太阳又可问地球道:我牵引你,你为什么不拢来,时时想向外逃走,并且还暗暗地牵引我?你地球也未免自私。再反过来说,假令太阳怕地球说它徇私,他不牵引地球,地球早不知飞往何处去了。地心怕泥土沙石说它徇私,也不牵引了,这泥土沙石,立即灰飞而散,地球就立即消灭了。我们这样的推想,就知道:遍世界寻不出一个公字,通常所谓公,是画了范围的,范围内人谓之公,范围外人仍谓之私。又可知道:人心之私,通于万有引力,私字之除不去,等于万有引力之除不去,如果除去了,就会无人类,无世界。宋儒去私之说,如何行得通?请问私字既是除不去,而私字留着,又未免害人,应当如何处治?回答说:这是有办法的。人心的私,既是通于万有引力,我们用处置万有引力的法子,处置人心的私就是了。本章第五图,与第二章一、二两图,大圈小圈,层层包裹,完全是地心吸力现象,秩序井然。我们应当取法它,把人世一切事安排得秩序井然,像天空中众星球相维相系一般,而人世就相安无事了。孟子全部学说,就是确定我字为中心点,扩而充之,层层放大,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宋儒的学说,恰与之相反,不但想除去一己之私,而且想除去众人之私,通于万有引力,欲去之而终于不可去,而天下从此纷纷矣。读孟子之书,霭然如春风之生物:读宋儒之书,凛然如秋霜之杀物。故日:宋儒学说,完全与孟子违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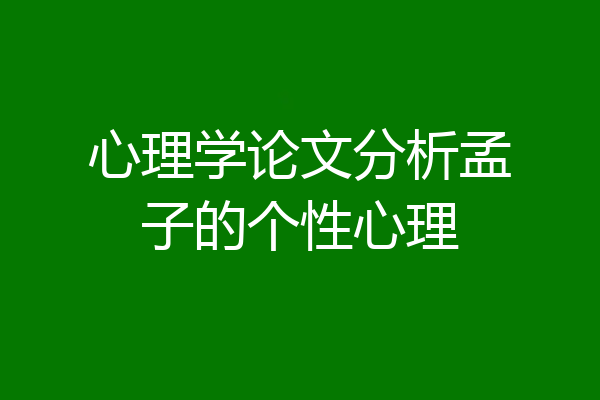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听其言,观其声。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吃一堑,长一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求大同,存小异。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万事不足,败事有余。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孟子性善论的人性观侧重于教化,即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 性善论主要侧重于对他人友善的教育思维。虽然与当下社会脚步稍有分歧,但是这样的理念毕竟是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好的建议终究会被采纳。而也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就是围绕着这条观点。大家都能感受到,国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利益还是很看重的。例如:每当有较大的灾难发生,国家就会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去保护每一个人的财产与健康,最近的几次的大地震,洪水等灾难,政府则派解放军去进行救援,只要有生还的可能性,就一定不会放弃。这就是性善论的教化结果吧、 性恶论在名声上自然没有性善论那么入耳。其实,就如同性善论并不能使人自动行善一样,性恶论的含义也并非准许人随意作恶。其对教育的影响侧重于适者生存,即在激烈的竞争中想办法取胜。 性恶之恶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所本来具有的生存本能。是生物就要生存,就一定要求生。既然一定要求生,也就没有必要否定它,回避它。荀子的做法只是没有回避它而已。 而在人性观上,荀子直指人的本性,较之孟子的多方论辩更具有“因人情”的一面。孟子的学说是以性善论作为开端的,但是却以诋距杨墨作为结束。荀子背负性恶的恶名,但却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性恶论并非一定会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总之扬长避短,结合应用,至于教育史见下文 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转载) 在现代社会,由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的本质失落,精神衰退以及道德滑坡等现象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通过道德教育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新的世纪特别是我国社会的转型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是构建转型期道德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宝库,其中,古代儒家追求个体人格完善美的德育目标,外在道德规范与内在心理欲求的统一、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以及强调道德情感培养的德育过程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追求个体人格完善的德育目标 在儒家伦理中心的思想体系中,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构成了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孔子所设想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圣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格,“君子”次之。在孔子看来,能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就是圣人。但是,“圣人”的标准远非常人所能企及,即便是尧、舜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圣人,因为“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由此可见,“君子”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修己”,第二是安人。君子人格的最终完善就是通过修己而治人。与“圣人”、“君子”相应的是“仁”。“圣”是具有效果的客观业绩,“仁”则是主观的理想人格规范。“仁”实际上是对个体提出的社会性义务和要求,它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性的本质和“仁”的重要标准。正是由于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孔子一方面强调学习知识,另一方面强调意志的克制和锻炼。追求知识和控制、锻炼意志成为人格修养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最终使个体人格的“仁”达到最高点。 孟子在完善人格设计上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孟子看来,理想的人格应是“圣人”、“君子”,“内圣外王”是对这种理想人格的基本规定。圣人人格是一种最高的道德人格,它具有“天人合一”的特征。 自孔孟而后,中国古代儒家一直十分重视理想人格的设计,强调对个体完善人格的追求。对于个体完善人格的追求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临事不惧,不计成败得失,不问安危荣辱,具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的道德理想。当然,儒家对于个体完善人格的塑造并非没有缺陷,但是,对于当前的市场经济社会而言,追求个体完善的人格确是应予以重视的一个问题。 二、外在道德规范与内在心理欲求的统一 一般认为,孔子思想的主要范畴是“仁”。但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礼”是对社会的个体成员具有外在约束力的一套习惯法规、仪式、礼节,如:“入则孝,出则悌”等都是无多少道理可讲的礼仪,只是要求人们遵守的一种传统的规范。但是,作为统治秩序和社会规范的礼,是以食色声味和喜怒哀乐等“人性”为基础的。在孔子那里,这种作为基础的“人性”就是心理上的依靠。《论语·阳货》载:“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为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在这里,孔子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这样就把“礼”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原本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道德伦理规范与人的内在的心理欲求溶为一体。[1]外在的伦理道德规范不再是僵硬的、完全强制性的,而是人性化的,属于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由于孔子强调内在的心理依据,实际上使得“礼”从属于“仁”,外在的道德规范(礼)服从于内在的心理(仁)。正如孔子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可见,外在的实体(礼和仪)是次要的,根本和主要的是人的内在的伦理—心理状态,也就是人性。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将道德的内在心理状态或者说心理原则作为其理论结构的基础,把他的“仁政王道”完全建立在心理的情感原则上。“仁政王道”之所以可能,并不在于任何外在条件,而只在于“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在这里,“不忍人之心”成为“仁政王道”的充要条件。这样,就极大地突出了“不忍人之心”的情感心理。何谓“不忍人之心”呢?孟子认为:“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这也就是说,人的道德行为只是无条件地服从于内在的“恻隐之心”,亦即“不忍人之心。”以此看来,孟子把孔子的内在心理原则发展成了一种道德深层的“四端”论。在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强调内在的心理是其重点。荀子的观点则与孟子相反,他更为强调外在规范的“礼”的作用。 儒家思想体系中所蕴涵的外在道德规范与内在的心理欲求统一的思想对于现实的德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道德教育本质上是个体人格和品德的建构过程,是个体的内在需要与社会道德原则的对话过程。[2]道德领域是人自觉活动并充分发挥主体性的领域。道德本身是人探索认识、肯定和发展自己的种积极手段,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由于现实的积极的需要,是人积极性的源泉,因而道德需要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心理学研究表明,道德需要是道德行为发生的心理源泉。人的道德行为总是指向一定的道德需要的满足,从而获得积极的道德情感体验。过去,道德教育的根本缺陷在于过于重视道德教育的社会功能,而忽视了道德教育的个体功能,忽视了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因此,改进道德教育,必须使外在的社会道德规范与个体内在的心理欲求相统一。 三、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 由于道德上的心理依靠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道德规范与人的内在心理欲求的统一使得儒家强调道德自律,从而极大地突出了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所负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为着达到道德的自律,个体的自我道德修养至关重要。所以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十分重视自我道德修养。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志。“志”就是“心之所之(止)”,立志即确立目的和理想,使个体有明确的努力方向,以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孔子非常重视立志的作用,正如他所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应当使自己分清善恶,要“好仁”、“恶不仁”,应“志于道”,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做到“行已有耻”(《论语·子路》),如果“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总之,“苟志于道,无恶也”(《论语·里仁》)。孟子与孔子一样重视立志。他认为首先应“尚志”,就是要“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一个人能以“仁义”为志,就能分辩善恶,认清应为与不应为之事,“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一个人既立志为善,就应当以不能行善为可耻,羞耻之心愈强,积极的为善勇气愈增,“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孟子在强调立志的同时,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养气”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第二,内省。内省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自我道德修养方法。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内省实际上是道德上的一种主观积极的思想活动,能对人产生重要的心理作用,“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孔子认为人应当随时“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内省也”(《论语·里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如果能够宽于责人,严于责已,就能避免与别人发生怨恨,在人与人发生矛盾时,应“求诸己”,从自己身上找根源。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忠恕”思想,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碰到别人以不合理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时候,要“自反”,做到“反求诸己”。他说:“爱人不亲,反其全;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自省的目的在根本上是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记》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慎独”的修养方法。《中庸》指出:“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的方法强调的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人能够独善其身,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这种“慎独”的方法无疑将孔子以来的自省主张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第三,力行。在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中,立志和力行是密不可分的。他非常强调行,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他要求人慎言敏行,少说多做,“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在力行中,孔子特别强调言行一致的重要性,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要求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 第四,改过迁善。改过迁善是儒家自我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要求人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失,有改过迁善的勇气。他说:“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他所重视的不是人不犯过,而是有了过错之后能否改正,并且不重复自己的过失,即“不二过”。他还要求人能够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论语·子罕》),对于他人正确的意见,应认真听取,并加以改正。孟子则继承了孔子改过迁善的思想,主张“闻过则喜”、“见善则迁”。他赞赏子路和夏禹的做法,说:“子路,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一个人能够不固执己见,舍己从人,就能乐取于人以为善,就能日迁于善。人只有通过改过迁善,才能成为道德高尚之人。 道德教育作为个体品德的自我建构过程,离不开个体自我道德修养。古代儒家所强调的自我道德修养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