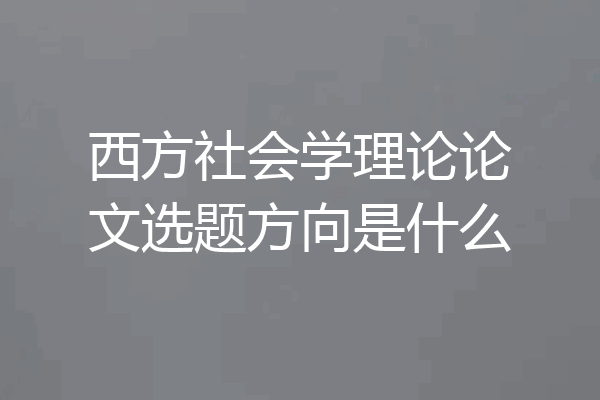手机用户
手机用户
从历史视角重读西方社会学理论2014年08月20日 18:18:26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 张杨波 在20世纪50年代初,一群哈佛大学的在校生开展了一项就业服务活动。他们定期召开会议,每次开会时会先向小组成员提供信息,大家根据这些信息去解决问题。接下来,他们不仅要评价小组任务是否完成,还要保持行动上的一致,等项目顺利结束后,还会开展一些集体活动来保证群体的团结。这是美国社会学家鲁思·华莱士和英国艾莉森·沃尔夫在《当代社会学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扩展》中举的例子。但是如果不交代背景,也许会很难想象这个事例居然是后来帕森斯发展AGIL模型的最初灵感来源。利用历史资料的丰富性和完备性做衬托,就会使得原本晦涩的理论模型更加生动、易懂。但大多数情况是,在学习西方理论时,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那些与理论相关但不属于理论内容的历史背景“剔除”。只知社会学理论,却不知它们缘何而来,成为理论学界的一种现象。 理论与历史背景脱节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什么提出价值中立?这要回到他当时所在的社会。20世纪初,韦伯为了回应当时经济学家间的争论,撰写了《价值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与施穆勒、罗雪尔等经济学家展开论战。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在《自杀论》中为什么与心理学家过不去?如果阅读过创立模仿律的法国心理学家塔尔德的论著,自然就理解了涂尔干的良苦用心。还有近代的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为什么会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提出“回飞镖效应”?假如了解了美国政府当时为了提高士兵士气,特意请到了知名导演拍摄了七部反映二战影片的背景,理解默顿发展论点的经验基础就变得十分容易。遗憾的是,我们知道了价值中立,掌握了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社会学方法准则,记住了“回飞镖效应”的四种情形,但是不知道在这些观点背后有那么丰富的历史细节。在不清楚这些理论背后的历史情况下,就直奔理论的主题,抛弃了经验基础或忽略了历史背景,得到的只是一些干巴巴的概念和理论。 理论体系缺乏整体构建 产生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过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科书重在介绍西方社会学家讲了什么内容。这对初涉西方理论的读者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领略不同流派的观点。然而,要完整地讲述理论产生的历史过程还需要做更深入的功课。此外,这种介绍方式还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社会学方法传统中有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之争,尤其是前者将自然科学奉为圭臬。拿物理学来讲,我们在引进西方观点时重在掌握它的研究对象、方法与结论,而文化和区域因素在这里显得不怎么重要。照这样的思路下去,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也不必关注它背后的历史。这种研究立场隐含的一个前提是中西方社会的差异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此花时间去介绍西方理论的产生过程显得多此一举。 然而,这样做却产生了不少麻烦。没有交代西方理论的历史背景,阅读起来感到晦涩;没有掌握西方理论的整体面貌,运用起来感到别扭。这样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西方理论,更不是强调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而是要提醒人们尝试换一种视角来重新阅读西方社会学理论,从原来广度上的宽泛介绍向现在深度上的纵向拓展,具体做法要因理论的不同情况来区别对待。例如以某位社会学家的观点为例,既要阐述这个观点与其他观点之间的联系,作者发表的论著是做这种研究的素材,又要挖掘这个观点背后的历史过程,作者的回忆录、日志和口头演讲中能提供这些资源。换言之,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知道了一些概念或思想,而是要将与它相关的其他资料一并掌握领会,这样才能还原理论的全貌。其实,社会学家默顿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中就对当时美国流行的理论教材的编写方法提出过含蓄的批评。他认为,逐一介绍每个社会学家的观点对于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贡献是很有限的,围绕社会学家的观点做科学史上的探索才更有价值。 论著变化体现历史化影响 从目前情况看,西方理论论著的发展变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就某位社会学家的生平简介和他的学术观点做全面介绍,不仅强调作者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联系,而且注重探讨作者在什么条件下去发展理论体系。例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塔·格哈特撰写的《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成书背景的介绍让人耳目一新,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撰写的《默顿学术思想评传》也是一个典范。二是选编一些著名的论文和专著,并就这些文献的历史背景做更细致的说明,从更广泛的历史情境来重新解读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过程。上面这两种叙述手法已经不只是介绍西方学者的观点,而是从立体的角度去介绍观点产生的完整过程。当我们再去研读这些文献时,得到的就不只是理论陈述,还有它背后丰富的历史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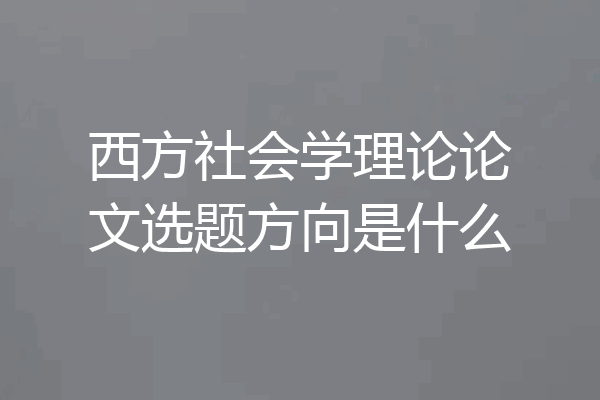
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国内waiyanjiuxianzhuang 一、国内研究现状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作为德国三大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其作用与同时期的韦伯,滕尼斯同样重要,但是在同时代人眼中,齐美尔就是一个“不易归类的使人不安而又令人着迷的形象”[1]加上齐美尔本身的人格特质,个人经历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致使其始终是学术局外人。 而国内对齐美尔的关注始于 1987 年《哲学译丛》第六期刊登的狄塞的《齐美尔的艺术哲学》[2]于次年,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国外社会学》上发表《齐美尔社会学思想评价》,此文是中国学术界对齐美尔最早的研究[3]自此以后齐美尔才逐渐正式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内学术界掀起了研究齐美尔的热潮。 首先体现为有关齐美尔着作的中文翻译作品增多。代表性的有:1990 年出版的 《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2000 年出版的《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2001 年出版的《时尚的哲学》、2002 年出版的《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社会学关于社会化的研究》、《货币哲学》、2003 年出版的《宗教社会学》、《现代人与宗教》第二版、《生命直观》、2006 年出版的《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叔本华与尼采-一组演讲》、《哲学的主要问题》等。 与此呼应,国内社会学教材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对齐美尔的关注很少,片言只语,甚至是被忽略掉了。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国内社会学教材对齐美尔都有所介绍,并且很多不只是对齐美尔思想进行简单介绍,而且从整体上把握,探究其思想逻辑规律。如杨善华编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对包括齐美尔在内的社会学家进行了深刻的解读。 从上可以看出国内至上个世纪 90 年代对齐美尔的关注明显增强,有关其作品翻译显着增加。国内社会学教材也较之以前对其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但是有关其理论的专门的着作却比较鲜见。 本文试图从学者对齐美尔的社会观,现代性理论,社会形式具体类型的研究, 研究方法论四个方面来概括国内有关齐美尔的研究,四个方面并无实质性顺序之分,只是为了叙述方便。 (一)社会观研究社会观作为社会学领域的基本问题,决定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选择。而社会学史上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争论比比皆是,主要体现为社会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执。对象之争的逻辑基础或“本体论预设”乃是社会观,它涉及到对社会的基本性质的看法和认定[4]有关齐美尔的社会观主要散落在相关的社会学教材中,如贾春增的《外国社会学史》,杨善华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侯钧生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周晓虹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体系第一卷》等等。 其中就国内有关齐美尔的社会观,周晓虹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周晓虹认为,唯实论的代表有孔德、涂尔干,唯名论的代表则是塔德和韦伯, 而齐美尔是继斯宾塞之后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的又一调和者。在齐美尔眼中,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既是现实的又不是现实的。社会是现实的,但这种现实性脱离不了个人间的互动;个人也是现实的,但现实的个人又总是经过社会化的。一句话,社会与个人及它们的现实性,就存在于两者间的相互依赖和互动之中[5]姚德薇则认为齐美尔的社会观不是一种对唯名论与唯实论的简单调和,在齐美尔个人和社会不再是权重的两极,而是被赋予参与理解和过程性互动的品质[6]成伯清认为齐美尔的观点带有一定社会建构主义的色彩,因为他分别强调了科学研究是一种对社会的重构,以及社会生活也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7]芮必峰、陈燕从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从社会互动如何形成社会这一点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8] (二)现代性理论国内学者专门着书对齐美尔理论进行详细的解读主要表现在对其现代性的关注。比较突出的有 1988 年出版的着名学者刘小枫的《现代性社会理性绪论》,本书以现代学意识为起点,讨论了现代性问题的积累,个体言说与“主义”话语,审美主义与现代性,怨恨与现代性,宗教与民主社会两种形态等几个方面,旨在表明通过现代性问题来讨论迄今社会学理论的问题性。在本书中就齐美尔研究目的的切入点来讲,刘小枫的看法是“齐美尔以一种审美(感觉)方式来确定现代经济制度与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心性品质之内在关联,以便更切近地把握现代人的生活感觉。 描述现代社会的质态,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和论述方式,这取决于作为个体的社会学家的观察点和设问。齐美尔的文化社会学方法及其概念,是心理主义的,即从感觉层面来分析社会形态”[9]杨向荣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对于齐美尔,“现代性分析的入口就不能是那些宏观的社会系统或者社会制度,而在于社会现实的内在细微处,在于那些被看作是永恒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的瞬间景观,或者说是快照”[10]1999 年出版成伯清撰写的《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研究纲领,现代性的诊断,社会学片段三个方面探究了齐美尔的思想理论,尤其是理论独特的提问方式和运思过程以引起人们对其更大的关注。在本书成伯清认为齐美尔对现代性的说明既不是基于对社会中重大变迁的历史研究,也不是着眼于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主题,比如政治集中、社会分层、科层化、社会团体、平等、公正、法律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甚至像“社会结构”“社会系统”和“社会体制”之类的概念,在他的社会学中只是处于从属地位。齐美尔所关注的主要是以下这个问题:现代生活的状况对个体人格的完善有何影响[11] 2006 年出版的陈戎女的《西美尔与现代性》则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出发,围绕文化的现代性来展开对齐美尔不同侧面的论述。本书中写到:西美尔思想大多不是体系化的理论,而是思想片断式的言述。据此,本书以几个专门的个案,从几个侧面勾勒他的思想轮廓,这几个思想侧面是西美尔的货币论、性别论、审美论、宗教论,论述的焦点则放在文化的现代性[12]2009 年出版的杨向荣的《现代性和距离-文化社会学领域中的齐美尔美学》 本书通过三个关键字:文章里与刘永利认为,在齐美尔那里,现代社会的生活已经裂变成了一个个细小的碎片,而齐美尔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些浸染着现代个体生存图景的生活碎片[13]王小章认为齐美尔关注的是现代社会和文化机体中作为现代生活之最直接的承载者的个体的生命体验、心性结构[14] (三)社会形式类型研究国内就齐美尔社会形式类型的研究更是数不胜数,主要是散布于相关的学术论文中。中国知网显示十多年来(2000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1 月 10 日)有关齐美尔的文章 241 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有 7 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有 31 篇,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有 176 篇,其他散布于特色期刊及其他会议论文中。涉及的类型也是各个方面,在此就不在一一介绍,主要介绍部分代表性特点。其一,货币哲学是关注的重点,不同论文基于不同的分析视角对货币哲学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与研究,但主要共性就是围绕货币从一种手段上升到一种目的及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如异化等[15]其二,有关其文化的研究及其在此基础上与布迪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的比较[16]其三,围绕其冲突理论与其他冲突论者的比较,比较集中于与科塞的比较[17]其四,围绕其美学进行的相关研究,这主要体现在齐美尔的美学观对现代审美的影响与意义[18]其五,围绕齐美尔其他的社会形式进行的小众研究,如生活世界,贫困,生命哲学,时尚等等[19] (四)研究方法论有关齐美尔思想的方法论研究国内关注则是很少。成伯清的《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可谓是最早对研究方法论的关注。在本书的第二章社会学研究纲领中写道,社会学是一种研究方式,一种研究视角,一种研究手段,类似于归纳法。齐美尔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他的研究对象而是研究方式,把社会学看做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手段的研究方式[20]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很少有专门对齐美尔研究方式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张小山的《齐美尔研究方法的后现代主义特质》一文中较为详细的论述了齐美尔的研究方法论带有后现代主义的特色。此外,西北师范大学岳天明的《试论齐美尔社会学研究视角及其学科意义》一文中以齐美尔的调和社会观为起点,论述了齐美尔把社会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的起源及其合理性必要性,对其社会研究方法论并未涉及[21] 二、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理论界对齐美尔的关注与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本人及其思想的碎片化式地把握,但是缺乏对其理论专门细致的研究。索罗金在其 1928 年出版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中,认为齐美尔的社会学缺乏科学的方法,缺乏实验取向、定量调查,是“一种纯粹的思辨、一种形而上学,一种科学方法的阚如”[22]有关微观层次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其现代性的理解与解读。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弗瑞斯比。他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与另一名重要学者波特莫尔合作将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翻译成英文[23]其后,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着作及论文,包括《社会学的印象主义》[24]、《现代性的碎片》[25]、《齐美尔及其后》等,对齐美尔的学术遗产进行了重新整理和挖掘,将齐美尔视为社会学界“现代性研究的第一人”,描绘出一幅“社会学的游手好闲者”的形象,并且深入探讨了齐美尔社会研究中的审美维度,挖掘作为“社会学的印象主义者”的齐美尔的意蕴。弗里斯比还于1994 年主编了三卷本的《格奥尔格,齐美尔:批判性评价》(QGeorg Simmd: Critical Assesment),其中收录了齐美尔本人两篇文章和不同时期研究齐美尔的重要文献 88篇,包括涉及到齐美尔的方法论议题(methodologicalissue)的论文 13 篇[26]他的代表作《现代性的碎片》主要是侧重分析他的现代性思想及货币制度,弗瑞斯比在书中指出,齐美尔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偶尔性碎片和社会互动的飞逝的图画,而并不是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等。对他来说,互动和社会交往是其两个核心概念[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