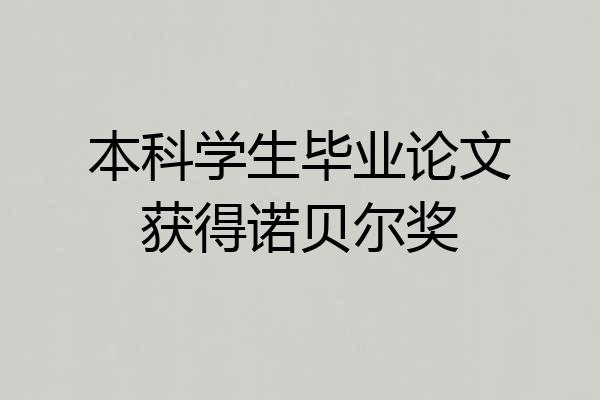ziFox
ziFox
2001年,日本为提高国内科学水平,提出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50年内要拿30个诺贝尔奖”。从2000年开始,在此后的19年内,日本一共获得19个诺贝尔奖,平均是按照一年一个的节奏稳步进行,完成率接近三分之二,照这个速度,“50年30个”目标,几乎已没有悬念。日本诺奖获得者名单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个个都是奇人。比如今天讲的这位日本学渣大叔,他大学时经常挂科留级,工作后是一家公司的底层研究员,拿着寒酸的薪水,穿着最土的衣服,过着混吃等死的日子。这样一个不知上进的上班族,却是日本人崇拜的“国民偶像”,长得也不帅,也不会唱歌,更不会演戏,他凭什么?田中耕一他是200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平淡、碌碌无为的学生时代1959年8月,田中耕一出生于日本富山市,他的童年很不幸,父母相继因病去世,他被送到叔叔家做养子。田中耕一的叔叔是一个木匠,每月工资不高,一家人过着简朴平淡的生活。也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让他从小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田中小时候性格比较内向,不愿意与他人交流,用中国的古语来说:一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长大肯定没出息。他总喜欢自己玩,受叔叔职业的影响,他的动手能力很强,总喜欢自己组装木方,还有一次,他自己组装了一台收音机,大人们都惊叹不已,认为这个孩子脑袋真灵活。田中耕一上小学时,他最喜欢的是化学课,因为化学老师经常带他们做实验,并鼓励学生们凭借着自己的想象力自由发挥,即使做错了,也无所谓。多年之后,田中曾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过这位老师,他认为这件小事对他的学业帮助很大。后来,田中考入了日本排名第三的东北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学专业,他所学的专业不仅与化学毫无关系,还因为挂科留了一级。在大学的这几年时光里,他跟咸鱼没有什么区别。埋头苦干,小失误成就诺奖毕业后,他希望去大企业上班,因为他是东北大学的毕业生。他面试的第一家公司便是索尼,但很快,第一轮就被刷了下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选择接受现实。很快,田中顺利地进入了岛津制作所工作,这是一家专门制造各种仪器设备的公司。根据他的学历,公司让田中参加开发“质谱分析仪”的项目。什么是“质谱分析仪”?就是用激光测量化合物的分子质量的一种仪器。作为一线的研究员,田中决定不再做一条咸鱼,只有高中化学水平的他,每天来到公司后,他总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在实验室埋头苦干,甚至将自己的终身大事都抛在脑后。被采访时的田中田中为了能在实验室第一线从事研究工作,自己拒绝了所有升职考试。日本企业的工资是与职务挂钩的,他的工资可想而知,并没有多少。在入职的几年来,田中一直处于企业员工的最底层,在公司内部,大家都称他“怪人”。几年之后,公司决定让田中开发用激光对生命大分子进行分离的仪器。当时世界上对中、小分子的分离的技术已经成熟,对于分离分子量超过1000的化合物技术,还有待于攻克。临危受命的田中误打误撞叩开了科学之门,不擅长化学实验的他,在实验中手一抖,不小心把甘油当成了丙酮醇倒进了钴粉末里,他心想这试剂应该价格不菲,从小便勤俭节约的他担心浪费了实验药品,于是拿起了混合物做实验,结果喜出望外,他居然分离出了分子量超过1000的化合物。他按照实验中的结果,分析出实验的原理,公司再根据原理设计出了分析仪器。田中虽是误打误撞,但总算扬眉吐气了一把。公司借此申请了分析仪的专利,这让公司后来产生了上亿元的利润,而作为做大的贡献者田中,只获得了11000日元的奖励,约合人民币700元。他的发明极大地推动生物化学领域的发展。田中对这一发现却满不在乎,只是在一次交流会上口述了该实验的原理。后来,有一位好心的大学教授建议他将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在国外的学术杂志上。如果不是这位教授,田中压根就没打算写论文。一夜名动日本在日本科学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当诺贝尔颁奖典礼开始前,国内都要拟定一份可能获奖的名单,名单里写着上榜者的详细资料,在诺贝尔奖公布前就会有一堆记者"驻守"到这些人的家门口,以便第一时间进行采访直播。在可能获奖名单上连续上榜15年的小柴昌俊,终于在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热度仅仅持续一天,接下来公布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一位大家从未听过的名字“田中耕一”。接受采访时的田中他是谁?化学类的专家没听说过他呀?各大新闻记者开始疯狂的寻找田中耕一。而田中耕一自己也不知道获奖了。诺贝尔奖海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了田中这一喜讯,还特意用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而英语水平一般的他,只听懂了"诺贝尔"和"祝贺"两个单词,以为对方是个骗子,只是说了声“谢谢”就挂断了电话。田中的妻子当时正坐在出租车上,听到广播,她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还波澜不惊地说了句:这人的名字怎么跟我丈夫一样?同时,媒体也在网上找到了田中的公司:名不见经传的岛津制作所。大量的记者蜂拥而至,将公司围得是水泄不通。这时田中才意识到,十七年前的论文竟然获奖了。临时被“抓住”采访的田中,还穿着做实验用的蓝色工装。他一脸茫然的被推上了演讲台,43岁的他根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害羞的他憋红了脸才说出一句:如果提前通知我的话,我一定准备一身正装上台。这时妻子打电话过来询问,田中面对了记者,尴尬的对着话筒说道:我老婆来电话了,我先接一下。喂,老婆,我正在接受记者采访呢,有事回家再说。当记者提问道:“先生,你发明了一种激光方法来确定生物大分子簇。你如何打破这一诺贝尔化学奖的技术难题?”他大方的承认:我的化学水平有限,只因为当初加错了试剂,误打误撞发现的。随着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田中在日本火了,他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国民大叔”。公司也为他升职加薪,政府和学术各界都给他颁发各种奖项,而在颁奖典礼之后,田中耕一仿佛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里。他为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呢?他认为自己根本不配拿这个奖!十六年后,王者归来2018年,在田中获得诺奖的十六年后,他接受了日本电视节目的采访,在采访中,田中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但比以前更加自信了。随着采访的进行,田中说出了消失16年的原因,一夜成名的他被名利所困,他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获得诺奖。16年来,他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真正配得上诺奖的人。十六年前获奖后,他回绝了一切的采访邀请,全身心的投入到“血液检测敏感度”的研究中。在十六年的辛苦付出中,他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这项技术能提前30年检测出阿兹海默症的前兆,并在网站上发表了相关论文。面对镜头采访的田中,如今自信满满,他的眼睛里有了光,他的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十六载的岁月,让他变成了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位配得上诺贝尔奖的学者。如今,他总算跟自己握手言和。他说:60岁的我,终于能挺直了腰板走路,真好。目前,我们中国的诺奖人数虽然不及日本,但量变最终将导致质变,每年近数十万的新增科学工程人员,其中一定能不断产生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其中也将有最顶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并在将来,一定能产生不少诺贝尔级的科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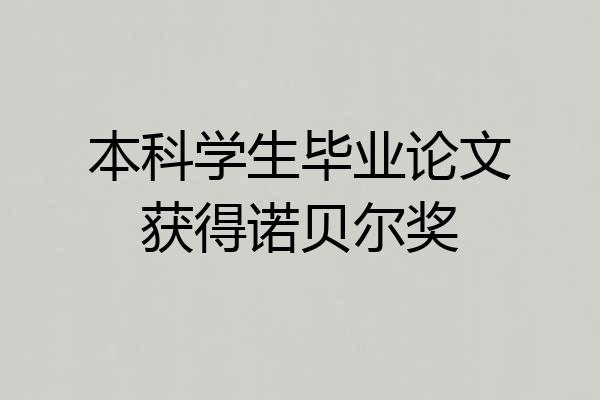
他肯定不是学渣,40多年积累了很多经验,所以肯定有了一技之长,拿了诺贝尔奖。
中国何时才能诞生诺贝尔奖?每年的10月初是诺贝尔奖颁布的日子,我们的诺贝尔奖情结便要发作一次。这似乎成了中国人每年都必谈论不休的话题,不管是华人得奖也好,不受政府待见的中国人得奖也好,从来没有一个真正得到承认的具有中国国籍的合法公民得过诺贝尔奖。中国何时才有本土的诺贝尔奖,这也成了各大媒体以及学者谈论的话题。华人得奖确实令国人心有一丝安慰,但这仅限于心理上和情感上。撇开公正性遭到质疑的和平奖与经济学奖,单从自然科学类的奖项来说,似乎没有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华人是从中国本土的研究机构走出来的。正如高锟教授和其它诺贝尔奖得主一样,他们的大学教育及研究生涯以及成名的研究机构几乎无一例外都在外国。高锟教授研究光纤是在英国,后来长时间在美国工作。他们的成就其实跟中国的关系不大。研究成绩也跟中国的学术及科研环境无关。这些或多或少折射出了中国科研环境的某些弊端。 在我看来,这种弊端便是缺乏独立精神。大学作为培养知识分子的摇篮,最重要的便是她的独立精神。陈寅恪在给国学大师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铭文里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条件,是科学、学术繁荣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前提。 而独立精神,体现在学术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科研工作者个人的独立思考。必须要有独立研究的能力,而不能老是依附于你的老师,或者你所在的研究院,必须要看你自己能不能做,这个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老跟着别人做,永远无法养成独立自主的创新能力。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集体意识,但却抹杀了个人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意志。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现成结论或知识成品,表现出一元化的价值取向,自然不可能创新东西。我们从学校养成的思维模式,就是去所谓的总结经验、揣摩方向,最终被潜移默化成了应试思维、投机模式。这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百害而无一利。 其二,学术研究与行政机关的独立。就现实而言,高校存在两个运作系统,一个是行政体系,一个是学术体系。减少行政权力干预,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减少行政领导在学术组织的任职。因为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具有极强的渗透性,行政领导担任学术委员不仅加重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依附,也会让教师热衷于行政而无心于科研和教学。搞科研的不参与政治,不受政治左右,不玩弄权术,也不被权术玩弄,纯粹的只是好奇和探索,格物和致知。自然科学最需要的是格物致知以及独立思维,脑中太多繁杂的不相关的东西会极大影响研究,而被各种外在的力量左右和控制,是无法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的。 个人的独立思维固然重要,可是在整体的大环境下无法形成独立研究的风气也是枉然。因此,在面对诺贝尔奖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研究与行政机关的独立显得更为重要。匈牙利籍学者米歇尔博拉尼曾经指出,“独创性是科学家的主要德性”,这一点人所共知。这意味着,一个国家要想其科学家取得创造性成就,就得创造一种制度环境,让科学家们能独立地、自由地思考、研究。但同时,“科学又具有最紧密结合的职业传统”,因而需要保持学说的连续性,保持团体内部的协作。为此,科学家们要形成一个科学共同体,个人置身于其内进行创新。当然,这个共同体必须完全按照科学、学术自身的逻辑组织,是一个自治的团体。 反观中国大学,学术腐败蔚然成风。在大学里专心做学术的筹不到经费,不会学术会专营取巧,会剽窃挪用的人反而可以窃居高位。而且又喜欢派系林立,党同伐异,恨不得踩死不同意见的人。学术造假的,学术剽窃的,论文瞎搞胡闹的,答辩如同过家家的。这样的环境,科学家们根本无法独立地、自由地思考和研究,更别提形成一个独立的科学共同体了。 对经费的追求代替对学问的追求,对博导的追求代替了对博学的追求,对权术的探险取代了学术的探险。当教育以培养接班人为目的并为之设置无休止的课程时,当学术期刊的价值大小是按照该期刊所属的行政级别来决定的时候,当研究课题指南是掌握权力的人来制订并受理项目申请的时候,当每个研究人员被强制研究自己不感兴趣的题目的时候,诺贝尔奖的苗子就被连根拔断了。 行政干涉学术所带来的后果,我们是有过沉重教训的。其中最典型的,当数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现代遗传学中的摩尔根学派,即基因遗传学的大批判。这次批判的结果,使本来可以先于世界的我国现代生物遗传学裹足不前,甚至停止倒退,说来令人痛心。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在“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我国学术界先后进行过五次反“伪科学”活动,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批判活动都是错误的。错误的批判不仅推迟了我国科学技术在某些领域的发展进程,而且还使本属我们长期的针刺麻醉机理研究落后于他国,使即将到手的诺贝尔奖与我们失之交臂。 再看同是亚洲的日本。出过多次诺贝尔奖的日本京都大学和名古屋大学的研究风气有共同特点,就是自由、平等、独立、开放式思考讨论和使用科研仪器设备,不束缚学生的思维。为体现平等、避免研究人员受到不必要的束缚,有日本学者规定,在研究室内不称呼每个人的职称和头衔。日本科学家科研经费充足,不受政府与社会的诸如考核、评价、聘任制等各种干扰,可以长期潜心从事研究。另外重视长线、基础研究的科研评价体制和科学精神,也是日本多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重要原因。 美国耶鲁大学的独立精神举世闻名。越战期间,美国政府曾下令凡是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战者均不准领取奖学金,当时包括哈佛以及普林斯顿等诸多名校都遵照政府的指示办事,唯独耶鲁大学仍坚守学术独立的一贯作风,继续以申请者的成绩为考虑奖学金的唯一准则。为此,耶鲁大学失去了来自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几乎陷入困境。时任耶鲁校长的金曼·布鲁斯特有句话意味深长。他说:“最终一般社会上的人士将会了解:只有学校在拥有全部的自治权利,每个教师及学者皆有研究自由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才有完全的自由和平等。而这也正是耶鲁的真正精神所在。”中国的大学原来也是有这些自由独立的传统的,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梅贻琦先生的教授治校思想都是这种传统的体现,他们以后的校长都知道这种传统对大学的重要性,也都知道珍惜。可是在一夜之间,这些美好的传统忽然就被背弃了。想起来,真让人无限唏嘘。 早在50年代就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教授曾经预言中国在20年内可以在本土产生诺贝尔奖。如果成事确实是中国人的骄傲。不过另一位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的一番话却让人对中国的学术情景感到担忧。他批评道,“中国大学缺乏解放人的个性,培养人的独立精神的特点,中国教育机构,计划学术更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这番言辞激烈的话对中国学术界无疑是泼一盆冷水。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的话,中国又怎么能够产生土生土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呢。 所以说,中国不缺诺贝尔式人才,缺的是诺贝尔式环境。中国大学的科研环境使科研工作者无法独立思考研究,没有独立思维,就没有创新,所有的研究也只是照书做实验。具备独立思考和民主科学的自由人格的人是难能可贵的,他们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然而这里需要的是一种独立精神,而这是长期受压抑的民族所缺少的。我们现在要弘扬民族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树立一种自信、自立、自主的独立精神:一切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做自己该做的实事。不为得奖而研究,不为名利而研究,学术研究不与政治体制挂钩,学术研究保持独立性,自主性,科研工作者具有独立意识,不受外界环境干扰,这才是问题的重点所在。 9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2010年本科新生入学报到。该校拟清退307名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消息,震动了初入大学的新生。清退人员里官员、商人、功勋运动员赫然在列。近年来,大学教育媚高官、媚富商、媚虚名现象层出不穷,原本追求真理的象牙塔,变身为权力与文凭交换的名利场,学术独立精神沦丧,已广为有识之士所诟病。我校能以决绝的勇气和信念捍卫大学之道,高扬学术独立精神,斩断与钱权名利的共生脐带,是高校去行政化,实现学术独立的一面旗帜。然而要真正实现探索真理、学术创新的崇高理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个拥有重视长线、基础研究的科研评价体制和科学精神的政府,一个从根本制度上最大限度容忍自由与独立思考、鼓励创新精神和向各种假设提出挑战的国度,离诺贝尔奖就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