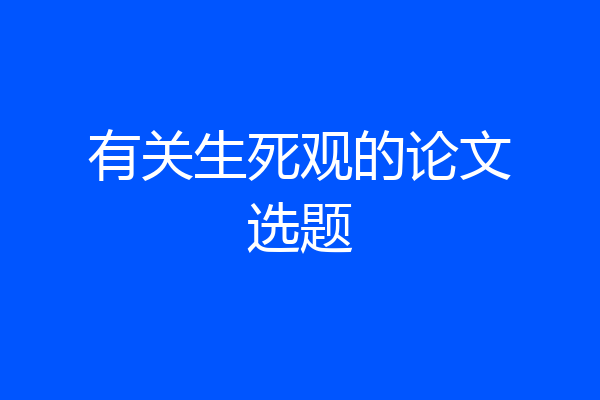rainboe
rainboe
由对待安乐死看中西方生死观的差异摘 要:随着现代医学和生命科学的进步,安乐死成为凸入人类视野的新问题。安乐死的提出及由此引发的纷争在西方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但在我国,尽管医学界和理论界对此不乏研究,普通人却较少对此进行认真思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中西方传统生死观念存在差异:一是对死亡本质的思考不同;二是珍视生命的目的不同;三是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不同。关键词:安乐死;生死观;中西方差异“安乐死”源自希腊文euthanasia,原意为无痛苦死亡,现指病人处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而在自己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安乐死的提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纷争在西方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但是由于中西方传统生死观念的不同,尽管在中国医学界和理论界也不乏对安乐死的研究,普通人却很少去认真思考安乐死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中西方生死观的比较,来分析造成中西方在安乐死问题上不同态度的原因。一对死亡的有意识回避是中国传统生命智慧的根本特征,它的思想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那里。《论语·先进》中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路的一段关于死亡问题的影响深远的对话:“季路问及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在这段对话中,对死避而不谈,从逻辑上表达了孔子重视生命的意向。孔子极少谈到死亡,《论语》中偶有对死丧的涉及,也不过是在考虑一件礼法秩序中的社会事件。孔子的死亡理念对中国人的生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回避对死亡及死后世界的思考,珍重世俗生命,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共有心态。儒家的言论和典籍中充满了惜命养生的气息。《孟子·尽心上》中有“知命者不立乎危垣之下”之语,其意即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生命、避免危险,以享尽天年。《荀子·正名》中更是进一步指出,“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将生的欲望和要求视为人最大的追求与希望。《诗·大雅》载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语,认为明哲之士都应该善于保养身体、爱惜生命。儒家后来的经典之一《孝经》更是将保全受之于父母的生命当作孝的最起码要求。但是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儒家并不是把对生命的珍视看作目的,重视生命是为了养亲,使双亲无忧;是为了延续后代,使宗族的祭祀香火不断;是为了重于泰山的死亡选择,使人生价值能够实现。把重生理论发挥到极端的是道家。道家提出了善生善死与自然相一致的思想。《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内涵正是以“自然”为不能改变的最高境界,认为只有效法“自然”才能保全生命、颐养天年。《庄子·大宗师》有“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之语,它道出的生死之理也充分体现出道家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核心思想,其意是要人们顺化自然,达观生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庄子对生命的漠视。庄子一方面徜徉于对生死问题理性的形而上的思索,认为生死一体并无差别,以此消除人们对于生死一线的恐惧;但同时又将这种思索与世俗的、直感的养生思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劝诫人们尽可能地全生而避死,力争善生善死。《庄子·养生主》通篇所言不外就是养生之道,认为人最首要的就是要保全性命。不过道家的重生与儒家显然不同,道家的重生纯粹是为己的,除了保全生命、完善心性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目的。道家的重生理论后来被道教思想家片面发挥,变成了一种探求长生不老、肉体成仙之方的宗教实践,在更大程度上对人们的生死观念产生了影响。佛教生死观与儒道两家原本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其基本主张是一切皆苦,唯有舍世间而求涅槃才可解脱,可见死亡在佛教中并不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然而中国化了的佛教———佛家思想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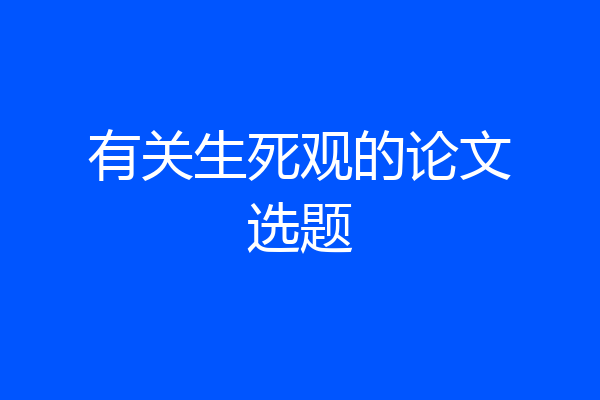
人的一生中生死只有一次,因此自古以来人们都十分重视生与死。古代士人有两种生死观。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司马子长曰:“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简单地说,前者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后者主张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仁者舍生取义,志者卧薪尝胆。而正所谓,仁者见仁,志者见志。因此古代士人无论选择两种生死观中的哪一种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两种生死观显然已不再适合当今社会,或是说已不能再作为现代人的生死观了。那么现代人究竟需要怎样的生死观呢?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认为所谓生,是指人生、生活,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可以做许多事,而正是这些事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但不同人的心中的价值标准是不同的,因此只要一个人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那么他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所谓死,是指死亡、逝去,是一个瞬间。但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对这一瞬间却有 着复杂的心理过程,所以便有了“夫人莫不贪生恶死”的结论。人对待死的态度直接影响着生前的行为。陈涉曰:“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司马迁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因此陈涉伐无道,诛暴秦;司马迁则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现在的人则认为人应看淡死,注重生前对社会的贡献,担当了生前事,何计身后名?这是正确的。我认为,一个人一方面要看淡死,不宜让死成为人生前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要珍惜生,不应轻易放弃生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作为青年人,我们的生死观还不成熟,因此不应妄谈生死,但是我们可以从前人生死观中总结经验。有人曾问我:“人为什么活着?”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忽然想起《与妻书》中的一句话:“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 是啊!在动乱的年代,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生存而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换来了现在和平的社会。而在当今和平年代,许多人却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战乱年代的人想活却活不成,和平年代的人能活却不知怎么活,想来可笑。人的生死大事,一方面在于人的主观因素即人的生死观;另一方面在于客观因素,即外部作用。在外部条件不佳的情况下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外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不错,一个人只要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使命,那么他就无愧于生死,无愧于后世。
我给你写一篇关于娱乐的论文,建议你不要直接使用,有些地方可以根据老师的要求再改一改。 打球是娱乐,打牌是娱乐,看戏是娱乐,看小说也是娱乐,各种娱乐形式所起的作用有一致的地方,即引起快乐,而且这种活动和人的具有明确功利性目的的活动有所区别,如在极度疲劳时睡觉、在饥火烧肠时饱餐,都可以获得极大的快乐,但一般并不将这些活动视为娱乐活动。同时,在参与或观赏这些似乎摆脱现实、忘记一切的纯娱乐活动的过程中,人们也获得一定的自由享受的乐趣,并且也有可能获得对现实的某种超越性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在这些纯娱乐性的活动中,也完全可能包含审美的因素,娱乐和审美显然不是绝然对立的。但是,各种娱乐活动在获得快感的性质、产生的作用等方面又有不同。麻将、台球、扑克等纯娱乐活动带给人们生理上的刺激,但也很难说仅仅是生理上的快感。整天坐着不动打麻将、甩扑克,生理上未必舒服,人们从这些活动中获得的主要还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愉悦和振奋。 和上述纯娱乐活动不同的是,文学的乐趣主要在于通过审美得到自由享受与审美快感。正如韦勒克所说:"文学给人的快感,并非从一系列可能使人快意的事物中随意选择出来的一种,而是一种'高级的快感',是从一种高级活动、即无所希求的冥思默想中取得的快感。"从这一点来讲,文学和其他娱乐活动的娱乐功能并不能等同;文学的娱乐功能与审美功能也不能够完全等同,不能因为由审美而产生快乐,便认为审美即等于娱乐,文艺的本质特点就是娱乐性。文学的这些娱乐功能并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其它娱乐方式的作用。因此也不应该要求文学和其他娱乐形式例如麻将、扑克发挥一样的娱乐功能。这种要求是不适当的,也是不现实的。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意识,就容易助长文学生产中的媚俗倾向。 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文学界有人强调文学的自娱功能,视文学为作家的"游戏",所谓"玩文学",所谓"写作便是我的娱乐方式"之类的说法就是这种倾向的反映。文学确实不但有娱人的功能,也有自娱的功能。白居易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和诗友之间的关系:"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可见即使是在相当强调文学功利性的古人那里,写诗读诗也可以是一种娱乐;但是,作者写作自娱是个人的事情,写作与朋友互娱是个人之间的事情,外人往往不知道也难以置评;而多数作家的作品却不是只给自己或少数几个人看的,通常总发表或出版,要公众阅读、购买,要达到娱人的功效。而自娱和娱人并不互相脱离,有什么样的自娱追求,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娱人效果。这样一来,自娱趣味的高低文野之分便不能不和娱人的社会效果连在一起。 不同受众的娱乐要求是不一样的。娱乐的内涵本来就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就个人的娱乐兴趣而言它也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因此,文艺作品是否能够发挥娱乐功能,能够发挥何种娱乐功能,发挥多大的娱乐功能,不但取决于作品本身,而且取决于接受者的态度,即接受者如何看待作品、对待作品。就社会群体而言,需求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交响乐的欣赏者和通俗音乐的追星族,都从各自的欣赏活动中得到乐趣。街头巷尾的对弈者和高尔夫球的搏杀者,都从各自的参与中得到乐趣。西方现代派文学和中国古典小说的读者,都一样从白纸黑字中欣赏到文学的奇光异彩。但是,这些乐趣又都有明显的差异。作者不应忽视读者趣味和要求的多样性而俯就低俗者,更不应该将自己的并不高尚健康的艺术趣味强加于读者。 毋需讳言,在克服多年来禁欲主义偏向的同时,生活中和文化上的享乐主义倾向正在我们的社会中滋长。享乐主义将追求感官快乐作为人生的惟一价值目标,而文化上的享乐主义则将满足感官快乐视为文化的惟一功能和最高目标,将高级的、复杂的审美过程解释成为简单的、粗鄙的感官刺激和反应。文学上对娱乐功能的种种片面认识,正适应了这种文化享乐主义发展的需要,妨碍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