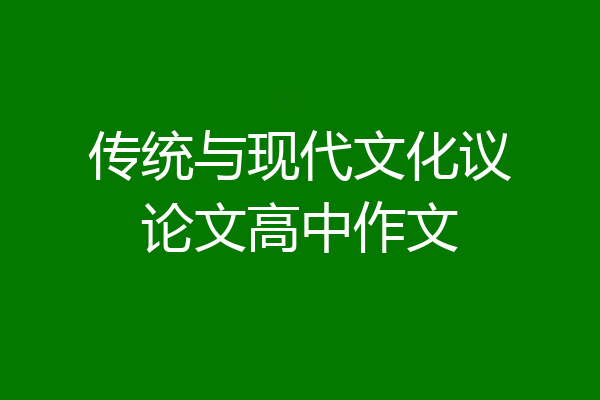cpp陈莫言
cpp陈莫言
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大家都尝试过写作文吧,作文是一种言语活动,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创造性。那么一般作文是怎么写的呢?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高二作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辅相成,各自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一个都不可少。 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优美。当砚台上的墨被研开,墨香顺着空气优雅地钻入鼻腔,我不得不被其儒雅的气息所沉醉;当沾上墨水的毛笔在纸上笔走龙蛇时,一个个汉字从笔下跳跃而出,显现在纸上,我不得不被优雅的字体所震撼;当捏糖人用那双灵巧的双手将一块块麦芽糖捏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小动物时,我不得不被捏糖的趣味所吸引;当雕刻大师手执一把雕刻刀在石头上东刻西磨,一个逼真的物体慢慢出现在眼前,我不得不被其精湛的手艺所折服……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纸上终究是诉说不完的,它就像一杯老舅芳香四溢,回味无穷。 诚然,传统文化之美令人向往,但现代科技也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君不见在极具现代科技的'机床上一瓶瓶墨水岁流水线上应运而生,其生产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君不见手机、网络为我们传达信息提供方便的服务,其神奇的技术令人好奇不已;君不见原来只能通过手工制造的食品现如今都可以在机器上实现量产,解放了劳作的双手;君不见3D打印技术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打造了一个精致又实用的物件……如今发达的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传统文化有传统文化的优点,现代科技有现代科技的优点。那两者相比较孰优孰劣呢?在我看来,两者都有其不可或缺的优势,两者相互交融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各自的优点,为我们人类文明增光添彩。 墨水只靠手工研制,其生产速率就会怠慢下来,若只依靠机器生产,就体现不出墨香独特的气息。所以两者都需要保留下来,既保留传统工艺,又要依靠现代科技升华现代科技。 就拿书写来说,有些同学书写的字迹非常潦草,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手机用久了;平时发消息只在手机上发,忽略了书写的重要性。出现这种情况,就得提醒这些同学多注意书写了。这绝不是在否认现代科技,只是在提醒我们要在学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才可以向现代科技看齐。当我们书写的字迹清楚,再在业余时间用手机打发一下时间,这未尝不可。而且这样也方便我们的生活,一个短信或一通电话就可以与千里之外的朋友、家人联系上,这样的便利不是很实用吗。 传统文化就像一只小船,而现代科技就像一双木桨。只拥有一只小船,没有木桨,小船将无法向前方航行;只拥有一双木桨,没有小船,那就与拥有一双木棍一样没有太大的作用。只有拥有船和桨,并且二者相互合作才能并肩向前迈进。 让我们以传统文化为船,现代科技为桨,向前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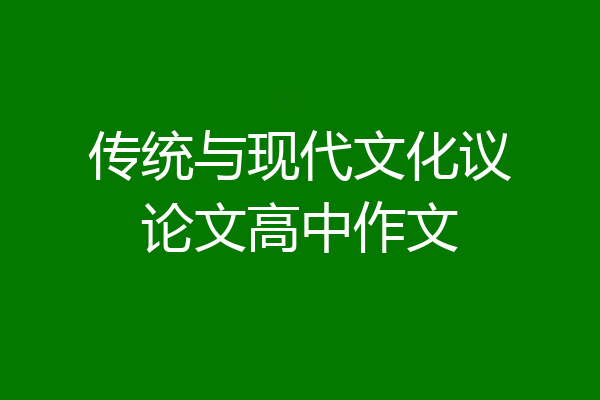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继承这种“实践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真实(reality)的超越性与内涵性具有有机的关连”,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并不追求超越现象的本质真实,而是在现象中追求本质,在现实的人生中内涵着超越的意义,所以不关心身后之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义二是五四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激进精神,以及与西 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本质区别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是中国传统的批判者,却不是破坏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生产者,却不是消费者从传统到现代,只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而已,说中国传统发展到五四造成断裂,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阐述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与近现代文化、文学的连续性,决非意味着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传统的基本特征若用一句话概括,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和谐,两个基本关系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追求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则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方面前者是道家观念,后者是儒家观念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儒道互补”来概括为什么儒道是互补的呢?这是因为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秩序是按照自然模式来建构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是君臣关系要如父子关系,国家秩序要以血缘关系为参照为依托,父子的血缘关系说到底是一种自然关系违背这种关系,父不父子不子,也就会君不君臣不臣了,天下就会失去秩序而大乱中国文化的自足性在此,中国文化的封闭性也在此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农耕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自然欲求是有限的,是极容易得到满足的因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形成,其实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欲求有限性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人的自然欲求的有限性是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所以中国文化也一直以同化或限定人的自然欲求为指归同化方式是一种较理想的方式,如孔子的“仁学”,仁的结构模式就是要求“礼”(社会理性目的)与“欲”(人的感性欲望)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使“欲”自愿接受“礼”、顺从“礼”,从而达到“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效果限定的方式则是一种不得意而为之的做法,它是通过限定感性欲望膨胀的方式来达到和谐目的的如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这一点,也正是五四时期人们所不满意的和攻击的对象 中国近现代文化也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冲突,两个基本关系是中与西及古与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是近现代文化的基础,而古今之争则是这种文化的主导方面古今之争说到底是中西之争,两者可以看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说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等等的矛盾冲突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始终古今之争不仅仅是今人对古人的反驳,而且也是持现代观念的今人与持传统立场的今人之间的争论这也不仅仅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冲击,而且也还表现为同一个人自己内心不同观念的冲突,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抗争,如梁启超近现代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古代以限制或同化人的感性欲望为指归的封闭式模式被打破,人的个人创造性能量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主体论哲学美学开始建立中国近现代文化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冲突的双方必然在同一个文化统一体内会互相牵制,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并没有完全走向西方发展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丝毫不承认发生在本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但是我们承认现代与传统的差异差异是否意味着断裂呢?显然不能这样讲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具体说明了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发生的在认知结构上的变化如果一个人从童年成长为成年,我们能因为这个人所发生的年龄上的变化而否认他成长的连续性吗?西方诗哲尼采说:“上帝死了!”可是并没有人因为西方近代哲学对基督教的批判而声称西方文化断层了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分清两个不同性质的说法: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冲击而造成中国传统的断裂,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影响而实现向近现代的转换这本来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持中国文化断裂论的人,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团,从而得出错误结论的我们显然不赞成第一种说法,而第二种说法涉及到中国文化若没有西方的影响能否实现现代转换的问题,这却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其自身是不能自动发生现代转换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具体说明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而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以较大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他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顾准在70年代也有类似的观点,虽然他当时并没有读韦伯的书,但他的观点却是与韦伯不谋而合的顾准在《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一文中说:“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 他还说:“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大儒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称中国文化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其特点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人与物的关系则是忽略的,现代科技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与物的关系,所以尽管人类文化的方向是中国文化,可眼下中国文化却要首先解决科技文化的问题,要首先走一段西方文化的路因此,为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引入西方文化是必要的 我们自然不能无视西方的冲击和影响在中国传统向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没有必要将这种作用无限扩大化,更没有必要将此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断裂因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首先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母体之中孕育而产生的,它不是突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都承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开辟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重大意义,但是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学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提升如此之高的做法并不就始于梁启超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早就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事实恰如米列娜所说:“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由1919年五四运动引起的剧变而造成的学术观点”是令人怀疑的“人们常常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解释为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激烈而短暂的过程”,而“这种解释是简单化的” 尽管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结构存有差异,但我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是曾说:“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决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假定一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同类之事实而皆合;……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 可以看出,这些方法跟后来胡适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杨东莼在谈到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治学方法时也说“深合于近代科学的精神” 对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破除以往线性单向思维模式的禁锢,不能只看西方的冲击影响,而无视传统中蕴涵着的现代转换的潜能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转换潜能的发挥又离不开西学的冲击和影响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是两者的共同作用,才实现了从传统文学到“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转换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象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就是说,新文学的产生是孕育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已具备了转换变化的趋向,只是由于尚缺乏外部条件,才没能促使这种转换的实现这外部条件也就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而“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渐渐地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将中国文学概括为“言志”与“赋得”两大传统他说:“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的文学” 按照周作人的解释,“言志”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即兴”是自由地表达思想见解;“载道”是传达他人既成的思想见解,“赋得”是限定在固有的形式下表达他人的见解周作人是赞许“言志”与“即兴”,反对“载道”与“赋得”的,这显然也跟他的“自我表现”论有关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言志”传统,尤其是直接继承了明代“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论他认为文学的历史发展,是“言志”与“载道”的交替循环,“五四”新文学作为对清代古典主义文学(尤其是“桐城派”)的反动,是向明代“公安派”的回归,因此新文学可被视为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文学传统的“复兴”他指出:“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外加外来的佛家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虽然,周作人在此未免陷入文学发展的历史循环论,但是他指出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即“五四”新文学虽然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它也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应”,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是衔接汇通的因此在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是直接承继明末浪漫主义文学而来的周作人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五四”传统文学断裂论是很好的驳正 在今天,我们应该走出古代与现代二分法绝对论的怪圈要不然,或者站在古代文化的立场上诋毁近现代文化,或者站在近现代文化的立场上攻击古代文化,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历史已经证明,是不利于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