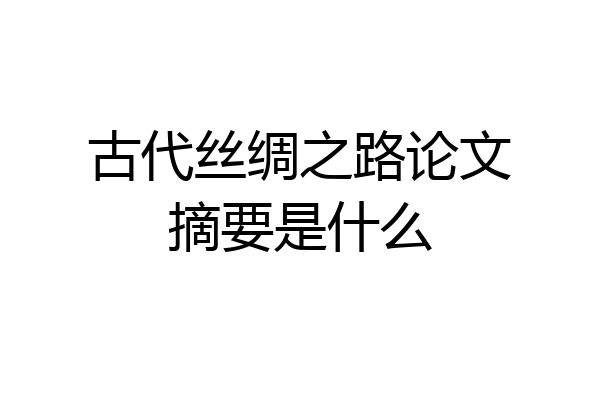murphi
murphi
一、古代丝绸之路开创性地打通东西方大通道,首次构建起世界交通线路大网络。古代丝绸之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堪称世界道路交通史上的奇迹。大大小小、难以胜数的中外交通线路,构成古代丝绸之路的“血脉经络”,构筑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建构了古代东西方世界相互连通的交通网络,成为亚欧大陆之间最为便捷的通道。众多的通道使得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东西方使节、商队、僧侣、学者、工匠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沿线国家商贸与人文交流的半径由此被大大扩展,贸易市场半径由此被大大拓宽。二、古代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大流通,率先实现了东西方商贸互通和经济往来。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往来的生命线,通过丝绸之路,我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输出到沿线国家;来自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珠宝、药材、香料以及葡萄、胡麻、胡桃、胡萝卜、胡瓜等各类农作物络绎不绝进入我国。丝绸是沿线国家商品交易中最主要的高档货物。原产于我国的丝绸,在古代西方国家十分名贵。在古希腊购丝绸、穿丝绸成为富有和地位的象征,甚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和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像等身上都穿着透明的中国丝织长袍。公元5世纪前后,我国茶叶通过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陆续传入南亚、中亚、西亚,15世纪一经传入即迅速风靡整个欧洲。茶叶贸易使沿线国家的贸易收入大幅增加,带动了沿线经济的繁荣及相关行业的突飞猛进,转口贸易也随之长足发展。三、古代丝绸之路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交互传播,广泛而又深刻地推动了沿线国家生产进步乃至社会变革。丝绸之路是我国与沿线各国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欧洲近代工业革命之前,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炼铁术等技术,通过丝绸之路相继传入西方,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因素。我国古代造纸术大约从公元4世纪起传入朝鲜和日本,公元8世纪传入中亚、北非和欧洲。8世纪末,阿拔斯王朝先后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办造纸厂,大马士革一度成为欧洲用纸的主产地,造纸技术又传到埃及、摩洛哥。随着12世纪西班牙、法国出现造纸作坊,中国造纸术席卷意大利、德国、英国。我国古代印刷术是沿丝绸之路西传的又一重要技术。早在公元7世纪我国就发明雕版印刷,在吐鲁番、敦煌等地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北宋时期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不久,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至13世纪,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将这一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登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欧洲第一家印刷厂在意大利设立,印刷技术迅速传遍整个欧洲。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盛赞中国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他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3页)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三大发明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事实上,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为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四、古代丝绸之路助推了多样性文化交流,是东西方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明相互浸染、相互包容的重要纽带。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彼此融合的文明之路,丝绸之路横跨亚欧非数十国,把中华、印度、埃及、波斯、阿拉伯及希腊、罗马等各古老文明联结了起来、交融了起来。东西方文化交流遍及音乐歌舞、天文历算、文学语言、服装服饰、生活习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民乐相互传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通过与当地音乐形式、演奏技巧的有机融合,不仅成为沿线国家民族化、地域化的代表和标志,而且深深地镌刻在了沿线各国各民族文学、戏曲、歌舞伴奏、民间生活等各个方面。在唐代,琵琶从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从我国传入日本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至今收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堪称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品。公元753年,六次东渡终获成功的鉴真,在日本弘传佛法,开创门派,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天平之甍”。早在公元1世纪初,儒学已传入朝鲜,《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成为朝鲜人的经典读物。5世纪以前,儒学经朝鲜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到日本的儒家学者。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互动,与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相伴始终,丝绸之路在把多种文化、多种文明紧紧连接起来的同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丝路文化和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不朽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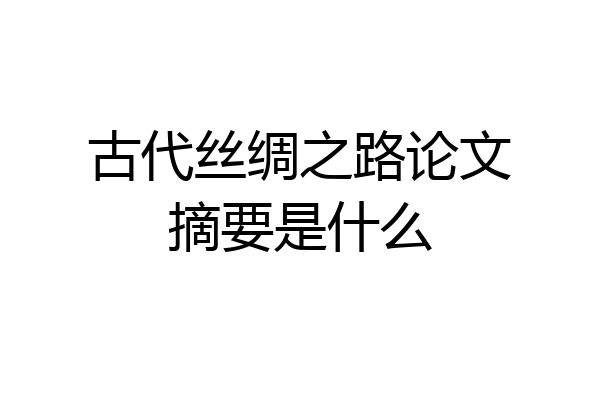
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中外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我在就个人的初步研究,谈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 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田蚕织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东传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随着中国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由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便如,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今爪哇(当时的叶调国)、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当时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缅甸(当时的掸国)都遣使业中国进献方物,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这个时候的特点如下: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达到“敦睦邦交”和扩大对外政治影响;还未注意到通过海外贸易,在经济上能增加国库的收入。民间的海外丝绸贸易,从外国文献来看似早开始。而在我国史书中却很少记载,可见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还不普及和发达。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960-1279)中国丝绸的外传 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国,每人赐绢五匹,共计1,350匹。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报告“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的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布丝绸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时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布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布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两书著者是宁代人,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记载。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唐朝开始设市舶司到宋朝又有发展,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则以市舶贸易为主;开始从过去只注意政治上扩大对外影响,以达“敦睦邦交”,而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住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
一、古代丝绸之路开创性地打通东西方大通道,首次构建起世界交通线路大网络。古代丝绸之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堪称世界道路交通史上的奇迹。大大小小、难以胜数的中外交通线路,构成古代丝绸之路的“血脉经络”,构筑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建构了古代东西方世界相互连通的交通网络,成为亚欧大陆之间最为便捷的通道。众多的通道使得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东西方使节、商队、僧侣、学者、工匠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沿线国家商贸与人文交流的半径由此被大大扩展,贸易市场半径由此被大大拓宽。二、古代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大流通,率先实现了东西方商贸互通和经济往来。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往来的生命线,通过丝绸之路,我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输出到沿线国家;来自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珠宝、药材、香料以及葡萄、胡麻、胡桃、胡萝卜、胡瓜等各类农作物络绎不绝进入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