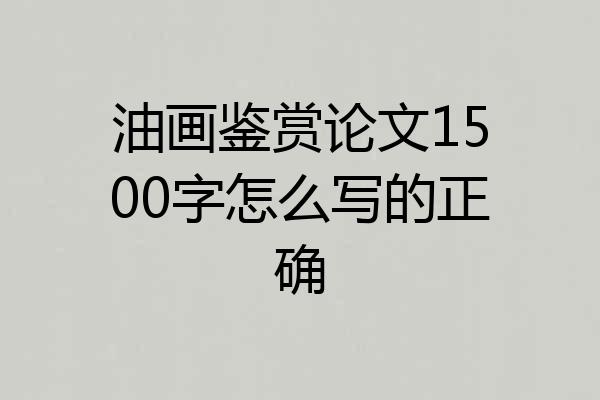BeanGee
BeanGee
这幅祭坛画最初是圣马利亚·德拉·瓦里契拉教堂的订件。描绘的是基督被钉死十字架后,由约翰、尼哥底母、圣马利亚与基督的两个女信徒给他下葬的悲剧场景:微弱的光线只照亮岩洞的一块大石板。在一片昏黑的背景前,约翰与尼歌底母慢慢地把耶稣赤裸的尸体放入墓中。 背后站着耶稣的母亲马利亚与两个女信徒。耶稣的尸体被光线照得透亮。整个场面俨然一个阵亡英雄或战士的下葬情景。耶稣的躯体画得强壮结实,脸上也显出刚毅的意志力,一张留短黑须的脸十分安祥,气氛肃穆,悲怆而庄严。 画家运用准确的解剖技巧表现了肌肉发达的尸体,唯有耶稣垂落的一只手提示他已没有生命。但这只下垂的手与被抬起的双腿,在画面上构成平衡的光感。 尼哥底母在这里是卡拉瓦乔重点刻画的形象。传说他是法利赛人,曾于夜间见过耶稣,和耶稣谈论过人可否重生的问题。耶稣被钉死后,他前来帮助埋葬。画家把他描绘成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形象。并把他画在前景主要位置,尤其展示了他的一双赤裸的大脚。为了加强整个形象的稳定性,这两只脚在前景上起着平衡作用。 在这里,除前景上耶稣尸体与尼哥底母的生动形象外,后面三个妇女形象也处理得很有节奏,尤其是双手高举、脸上表现了悲痛欲绝的心情的抹大拉,她给画面增强了悲剧性。她哭肿了双眼,嘴唇半张,似在呼天抢地。圣母包着头巾,脸容消瘦,她从约翰的肩后伸出一 只右手。这只手被光照射着,因而使分布在右边的受光部分取得均衡。同时这只掌心向下的手又起着对这幕下葬悲剧的指挥作用。 中间一个马利亚形象画得很美。她显得楚楚动人,娇弱可爱。她是拉撒路的姐妹。 一个质朴的农家姑娘。她正低着头,沉浸在悲痛之中,右手用手帕紧擦着眼泪。梳着中间分缝的 并在脑后盘上小辫的发式,更使人感到这个形象的写实性质。所有人物,除了约翰的脸部沉 入半阴影中外,都有清晰的受光部位。画家的典型构思是作了一番精心考虑的。 在色彩上,衣服的红、蓝与皮肤的苍白也形成了一种鲜明的色调对比。这使英雄下葬的 悲怆气氛,与四周的黑暗构成了强烈的冲突。当这幅画公展时,不仅使卡拉瓦乔的崇拜者心悦诚服,连他的宿敌也不得不承认画家的高度艺术修养。此画现藏罗马梵蒂冈绘画馆。 背景说明:卡拉瓦乔的创作进入成熟阶段后,他的画上的明暗对比表现得更强烈了。往往背景的空间都陷入阴暗或看不透的黑暗中,人物形象不是部分被吞没,只露出某部位,就是完全暴露于光照中,黑暗用棕色和深褐色来表现。这种手法被称谓“黑暗法”(意大利语为tenbroso) 或者叫做“酒窖光线绘画法”。他的《召唤使徒马太》一画便是这样表现的。1601-1604年间,卡拉瓦乔完成了这一幅最著名的祭坛画《基督下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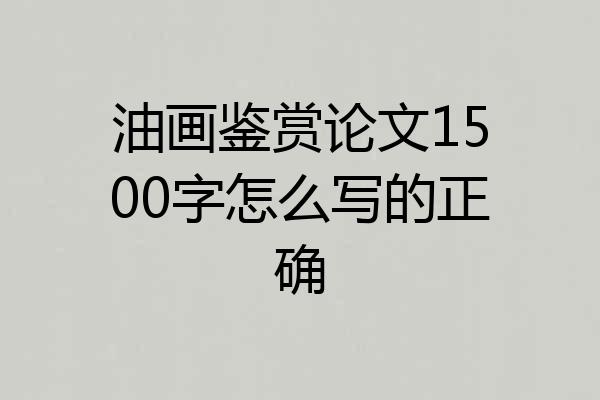
梵高的宇宙,可以在《星夜》中永存。这是一种幻象,超出了拜占庭或罗曼艺术家当初在表现基督教的伟大神秘中所做的任何尝试。梵高画的那些爆发的星星,和那个时代空间探索的密切关系,要胜过那个神秘信仰的时代的关系。然而这种幻象,是用花了一番功夫的准确笔触造成的。当我们在认识绘画中的表现主义的时候,我们便倾向于把它和勇气十足的笔法联系起来。那是奔放的,或者是象火焰般的笔触,它来自直觉或自发的表现行动,并不受理性的思想过程或严谨技法的约束。梵高绘画的标新立异,在于他超自然的,或者至少是超感觉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可以用一种小心谨慎的笔触来加以证明。这种笔触,就象艺术家在绞尽脑汁,准确无误地临摹着他正在观察着的眼前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看,实际确是如此,因为梵高是一位画其所见的艺术家,他看到的是幻象,他就是幻象。《星夜》是一幅既亲近又茫远的风景画,这可以从十六世纪风景画家老勃鲁盖尔的高视点风景手法上看出来,虽然梵高更直接的源泉是某些印象主义者的风景画。高大的白扬树战栗着悠然地浮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的小村庄,在尖顶教堂的保护之下安然栖息;宇宙里所有的恒星和行星在“最后的审判”中旋转着、爆发着。这不是对人,而是对太阳系的最后审判。这件作品是在圣雷米疗养院画的,时间是1889年6月。他的神经第二次崩溃之后,就住进了这座疗养院。在那儿,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在神志清醒而充满了情感的时候,他就不停地作画。色彩主要是蓝和紫罗兰,同时有规律地跳动着星星发光的黄色。前景中深绿和棕色的白杨树,意味着包围了这个世界的茫茫之夜。梵高继承了肖像画的伟大传统,这在他那一代的艺术家里鲜见的。他对人充满了激情的爱,使他不可避免地要画人像。他研究人就象研究自然一样,从一开始的素描小品,一直到1890年他自杀前的几个月里所画的最后自画像都是如此。它如实地表现出疯人凝视的可怕和紧张的眼神。一个疯人,或者一个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画出这么有分寸、技法娴熟的画来。不同层次的蓝色里,一些节奏颤动的线条,映衬出美丽的雕塑般的头部和具有结实造型感的躯干。画面的一切都呈蓝色或蓝绿色,深色衬衣和带红胡子的头部除外。从头部到躯干,再到背景的所有的色彩与节奏的组合,以及所强调部位的微妙变化,都表明这是一个极好地掌握了造型手段的艺术家,仿佛梵高完全清醒的时候,就能记录下他精神病发作时的样子。记得一句关于梵高的话:“灿烂到极致不是黯淡就是死亡,所以梵高也只能,毁灭了自己
《记忆的永恒》,达利作,1931年,布上油画,24x33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除了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也许是最为知名的二十世纪画家。”这是道恩·艾兹(英)在他所著的《达利》一书中的开场白。确实,在超现实主义画派中,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比其他画家更加声名显赫,或者可以说“臭名昭著”——这不仅仅因为他的那些想象力丰富得令人震惊的画面,更因为他那古怪得让人侧目的形象和行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个天才,无论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自我宣传的角度。他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和疯子的区别在于他不发疯。他精心侍弄他的小胡子,使之成为其身体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在画布上“做梦”,表现性、战争、死亡等非理性主题。 达利1904年5月11日生于加泰罗尼亚,曾就学于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学院,不过分别在1923年和1926年两度被逐出校门。他曾经专门学习过学院派方法,并对立体派、未来派等作过尝试探索。1927年他完成了第一幅超现实义油画《蜜比血甜》,并于1929年夏天正式加入超现实主义阵营。达利称得上是一名天生的超现实义者,他的绘画是细致逼真与荒诞离奇的奇怪混合体。 《记忆的永恒》受到弗洛依德的启迪,表现了一个错乱的梦幻世界。我们看到,清晰的物体无序地散落在画面上。那湿面饼般软塌塌的钟表尤其令人过目难忘。无限深远的背景,给人以虚幻冷寂,怅然若失之感。达利的绘画往往是支璃破碎的,充分展示了无意识的梦幻场景。但实际上,这些看似偶得的幻觉形象,必定经过了画家相当的努力;而看似无意识的画面,必定是有意识计划的结果,甚至是惨淡经营的结果。《记忆的永恒》也不例外。弗洛依德曾这样对达利说,“你的艺术当中有什么东西使我感兴趣?不是无意识而是有意识。”作于1931年的油画《记忆的永恒》典型地体现了达利早期的超现实主义画风。达利承认自己在《记忆的永恒》这幅画中表现了一种"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是自己不加选择,并且尽可能精密地记下自己的下意识,自己的梦的每一个意念的结果。而为了寻找这种超现实的幻觉,他曾去精神病院了解患病人的意识,认为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往往是一种潜意识世界的最真诚的反映。达利运用他那熟练的技巧精心刻画那些离奇的形象和细节,创造了一种引起幻觉的真实感,令观众看到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根本看不到的离奇而有趣的景象,体验一下精神病人式的对现实世界秩序的解脱,这也许是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真正的魅力所在。 而达利的这种将幻觉的意象与魔幻的现实主义作对比的手法,更使得他的画在所有超现实主义作品中最广为人知。
弗雷德里克·莱顿( Frederic Leighton , 1830——1896 )是 19 世纪末英国最有声望的学院派画家,他辉煌的艺术光芒甚至冲淡了雷诺兹的影响,成了英国皇家学院派的代名词。不像 19 世纪大部分画家那样,莱顿并没有在皇家艺术学院学习,他在布鲁塞尔、巴黎、法兰克福接受绘画训练, 1852 年他搬到罗马居住,古典艺术给了他很大影响。 1855 年,他回到英国,他的作品 Cimabue's Madonna 展出并被维多利亚女王购买,这是他事业的转折。 1878 年,莱顿当选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长。 1896 年受封为男爵。他是英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画家。他于同年去世。 %%%%%%%%%%%%%%%%%%%%%%%%%%%%%%%%%%%%%%%%%%%%%%%%%%%%%%%%%%%%%%%%%%%%%%%%%%% 《缠毛线》 1878年 弗雷德里克·莱顿 英国 3cm×3cm 布 油彩 悉尼 新南威尔士美术馆藏 画家沿用古典绘画法则,以学院派绘画的严谨,描绘了缠毛线的母女。年轻的母亲坐在凳子上,姿态优美地绕着毛线,衣裙的表现呈现古典风格;小女孩全神专注地配合着母亲,扭动着身体,一幅稚气。莱顿以古典手法去表现生活,因而使作品有呆板僵化之感,并且流露出缺少真实情感表现的缺陷。 %%%%%%%%%%%%%%%%%%%%%%%%%%%%%%%%%%%%%%%%%%%%%%%%%%%%%%%%%%%%%%%%%%%%%%%%%%% 《阅读》 1877年 弗雷德里克·莱顿 英国 2×1cm 布 油彩 利物浦 萨德利艺术博物馆藏 这是一幅富于情节性的肖像画,一少女盘腿坐于地摊上,认真、专心地在阅读画册。女孩身着的浅黄色衣裙极富质感,与深色的背景形成对比,更衬托出女孩的专注神情。女孩面容娇好,纯洁严肃,显示出较好的教养。整个画面体现出一种学院派的严谨与优雅。 %%%%%%%%%%%%%%%%%%%%%%%%%%%%%%%%%%%%%%%%%%%%%%%%%%%%%%%%%%%%%%%%%%%%%%%%%%% 《炽热的六月》 弗雷德里克·莱顿 这幅画模特 Dorothy Dene 自 80 年代(十九世纪)中期之后成为莱顿许多作品的灵感来源。独特的视角,加上模特身体优美的弯曲(拉斐尔的许多作品因此而成功,评论家把这称为女性身体的韵律)使这幅画与众不同。艳丽的色彩也使这幅作品格外抢眼。 %%%%%%%%%%%%%%%%%%%%%%%%%%%%%%%%%%%%%%%%%%%%%%%%%%%%%%%%%%%%%%%%%%%%%%%%%%% 《海边的希腊少女》 弗雷德里克·莱顿 %%%%%%%%%%%%%%%%%%%%%%%%%%%%%%%%%%%%%%%%%%%%%%%%%%%%%%%%%%%%%%%%%%%%%%%%%%% 《陶醉》 弗雷德里克·莱顿 %%%%%%%%%%%%%%%%%%%%%%%%%%%%%%%%%%%%%%%%%%%%%%%%%%%%%%%%%%%%%%%%%%%%%%%%%%% 《音乐课》 1877年 弗雷德里克·莱顿 英国 8cm×1cm 布 油彩 伦敦市政厅美术馆藏 莱顿以学院派极其严谨的态度描绘了音乐课的情景。女教师微微俯身帮助女孩调试琴弦,女孩则依在女教师胸前弹拨着六弦琴。这只是一幕普通的音乐课情景,却被画家描绘得极富美感韵味。女教师面庞秀美清丽,身着长裙,花纹、质地被画家描绘得十分逼真;小女孩则被描绘得天真烂漫,纯真无邪,表情认真,显得十分可爱。衣服、面部及背景的描绘,都体现出学院派画风,但是这幅作品却有着内在的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