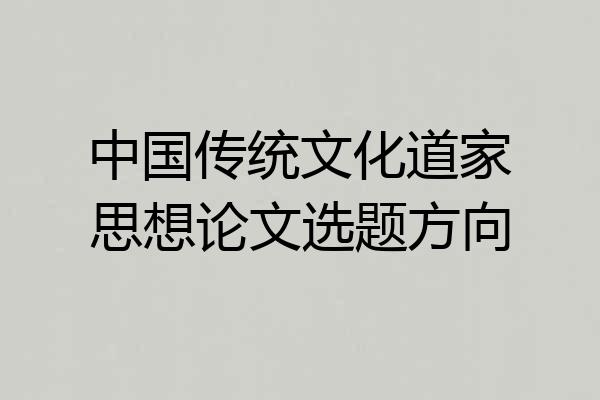adongt
adongt
道家思想可以与现代社会结合,但作为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还是要认真研究古代文献老子五千言(有魏王弼注本,是最通行的本子;有河上公注本、严遵注本;当代陈鼓应有《老子今注今译》,如果再深一些,可以研究郭店楚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庄子七万言(有郭庆藩注本、王先谦注本等),要读上几遍另外,陈鼓应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作为一本专业刊物(年刊),也不错如果你认为单纯论述的话太老套了点,说明你有进一步求知的欲望,很好但是,不能盲目出新对南怀瑾的东西要慎重此公有些时候学问做得很不谨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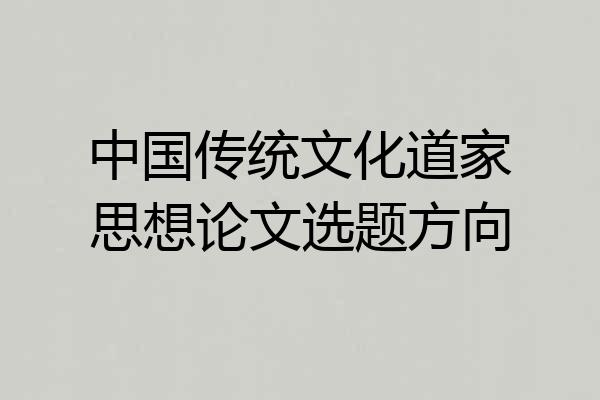
1)中国儒家、道家为基干的古代思想文化 2)书画文化 3)茶文化 4)婚嫁文化 5)酒文化 6)饮食文化 7)姓氏文化 8)园林建筑文化
和谐社会与道相通 当今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然而,要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新局面,就必须以实现人的价值与人的生命质量为焦点。因此,在这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的继续。虽然当今社会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富庶度最为理想社会的标尺,然而,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不难发现古人对理想社会的评价是以和谐度为标准的。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说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可以用“和合”二字来概括。和谐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中国关于“和谐”思想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黄河流域的游牧时代,远古人就把人类对自然世界最佳的依附关系,理解为和谐。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独特的中华精神文化遗产,道教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思想中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和谐思想”,这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意义。谈到道教思想,首先要谈到的就是道祖老子,老子是道教思想的奠基人,也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的思想都集中反映在其五千字的论述《道德经》之中,《道德经》论述了老子关于“道”的理论。老子之道是“道法自然”的自然之道,也是“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和谐之道。《道德经》中蕴含着老子和谐的自然观、人生观、社会观,这些思想可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有益参考。老子认为万物皆源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万物自然运行变化的真理,是万物之宗,万物之始,万物之源,万物在“道”中实现了和谐统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作为万物之源之道也要顺应自然,按照自然的规律运行,那么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时更应该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老子还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老子认为人是与道、天、地并重的,是属于生态系统中的一环,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仅表现在人依赖自然、受制于自然之上,也表现在人能够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并在交换的过程中对自然造成的影响之上。人作为四域之一,虽不卑微于自然之下,但是人更不能带有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目光,为追求最大的现实利益,以人的需求为主导,向自然无度的索取,妄想征服自然,役使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理应爱护自然,促进自然更加和谐与完美的发展。这就是老子思想中“天人和谐”的自然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特征正是对老子这种“天人和谐”的自然观的继承与发扬。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句话集中体现了老子和谐的人生论思想,老子认为上善之人具有能利万物、大公无私、甘处卑下、不与人争、心怀广阔、言而有信、应时而动等品质。社会是由人相互交往而产生的,可以想见,如果人都具有上善之人如水般恬淡,和谐的品质和人生追求,那么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必定会是“民主法治,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充满活力的社会一定是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人的身心自由发展的社会。老子说:“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先后之相随、恒也。”这是老子的矛盾观。万事万物均是矛盾的统一体,因此不可能消除万物的差别取得绝对的统一。老子又说“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可见老子的矛盾观是和谐的矛盾观,和谐是在矛盾的差别对立中产生的。把老子这种和谐的矛盾观,应用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之中,不难看出,社会成员之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是构成社会的自然现象。社会正是因为差异的存在才丰富多彩,才充满生机。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绝不能抹杀人的个性,而是要在能够被社会接受和容许的限度内,实现社会成员身心的自由发展,这样的社会才是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道教传承了道祖老子和谐的自然观、人生观、社会观,并且在长久以来的发展中对老子的和谐思想加以深化,使和谐思想渗透到道教的教义、科仪、戒律之中,构成道教的思想体系的和谐智慧。道教思想体系中的和谐智慧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有深刻的启示。首先道教“慈爱和同”的宽容和谐精神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平。和谐社会不是无差别的社会,但是和谐社会一定是和平的社会。和平的环境是实现社会和谐根本的条件之一。前面也曾提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现世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群体之间,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之间都存在矛盾的差异。这种矛盾差异的存在,使得当今世界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其中以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文化的冲突与宗教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现在,这样的冲突已经破坏了世界和平的局面,如果冲突进一步的激化,必将阻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要怎样才能避免矛盾的激化,在冲突中寻找和谐,在维持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同时促进世界的和平呢?道教慈同和爱的思想为缓和各种矛盾冲突,在理论思想上提供了有益的引导。道教认为万物皆源于道,万物皆有道性。“道”以虚为体,使万物自然生化,各适其性,即是所谓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但是,尽管是世间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但因为万物皆源于道,因此其运行却和谐而有序,事物之间的差异并不导致必然的冲突。道教是慈爱的宗教,也是宽容的宗教。道教的慈爱与宽容不仅是对信众的慈爱与宽容,也是对人、对世间万物,甚至是对其它宗教信仰的慈爱与宽容。因为道作为万物之始,万物之宗,具有慈爱万物的宽容品质。所以人要效法“道”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容慈爱精神去包容万物的差异,在矛盾中寻求和谐。《度人经》中所说“齐同慈爱,异骨成亲”的境界就是道教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境界。在处理当今世界的矛盾冲突时,如果能借鉴道教这种“慈爱和同”的宽容和谐精神,以取得冲突双方的共同发展,那么一定能够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其次,道教“众善奉行”的思想促进了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道教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从道的角度看,万物没有贵贱之分,天地之间万物缺一不可,一切生灵都有平等自由的生存权力,既然万物都没有贵贱,因此要善待万物。同时道教也认为大道普济救世的美德于人而言,表现在现世之中就是要善待万物,这是做人的根本与修道的必须。如《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道教对“众善奉行”的信仰追求,表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要求“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这种大力弘扬人与人之间诚信互助、和谐相处的精神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淳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双赢的过程,对人有善的付出,才有可能得到善的回应。如果人们能够把道家“众善奉行”的精神,作为与人的交往行为的向度,那么必然会对形成诚信友爱的人际关系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道教“重人贵生”的思想,能够促进了个人自我的和谐。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个人自我的和谐促进了社会的和谐。许多宗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人世间的一切快乐都是虚假的,并且把对幸福的向往寄托于虚幻的天堂或渺茫的来世之中。而道教却是“重人贵生”的宗教,道教对世俗生活的态度是积极肯定的,洋溢着浓郁的生命意志和生活情趣。道教追求长生不老,讲究性命双修,追求超脱却不离今生。道教主张在尘世中享受生命的真趣,并且在这种享受中将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入无限的宇宙之中,得到精神境界的升华。既然道教讲求的性命双修是不离尘世的,是把世俗生活与神圣的生活高度的和谐统一。那么要在尘世中达到“贵生成仙”的目的,就要求修行人在现世生活中超脱低级趣味与物欲的奴役,顺应自然,常怀知足之心,感恩之心。如果把道教这样的修身思想应用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对促进个人自我的和谐是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的。最后,道教的戒律还昭示了人道主义的道德归旨。谈到宗教,不得不谈到的就是宗教的戒律,宗教戒律是构成宗教伦理的重要内容。道教的戒律是以五戒为核心的,“第一戒杀、第二戒盗,第三戒淫、第四戒妄语、第五戒酒,是为五戒。”围绕五戒阐发的数百条戒律都体现了道家返璞归真、顺应自然的伦理原则,积极引导人们从善去恶、自洁自律,清净不争,具有现实的意义。当今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如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歪风邪气开始滋长,这些因素不但造成了社会道德的沦丧,也影响到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道教超脱物累的戒律思想可以对社会成员心灵与道德价值的提高产生一定积极影响。综上所述,道教是追求和谐的宗教,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道长也曾说过,和谐社会是道教的人生祈愿。道教的思想中的和谐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重要内容,包含了其对和谐社会探索性的追求;同时道教思想中的和谐智慧也是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六大特征是相通相融的,并且具有创造性的转化力量,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和谐社会与道相通” !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