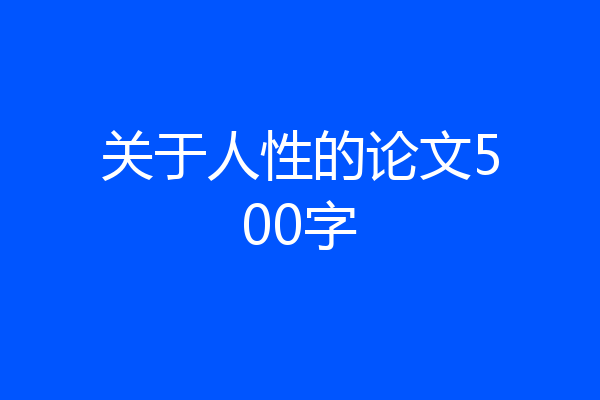qohfxktl
qohfxktl
关于人性“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性本恶”两个关于人性的论述,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深不可测,之前,我对人进行了肤浅的了解和研究,还通过有关书籍来查阅资料,发现了有关人本性的好与坏。这样,我对人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其实很久以前,一些心理学家已经对人做出了深刻的研究。这并不是在研究这种生物的外表,而是研究他的内心。同样,我对这个问题也装模作样地研究了一番。在我看来,人是天使与魔鬼的化身。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会分好坏,完全是受内心所控制。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破坏别人的利益,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而好却恰恰相反。这两个极端也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位美国作家就写过一本长篇小说《人性的弱点》。我阅读后受益匪浅,也给予了我很大启发,我也更清楚地发现了人的本性和思想。我的发现其实很简单,人是分两面的,一面是丑恶的:这有很多案例,人在金钱和权利的驱使下会变的软弱无能,我敢断言,这是很多人都会的,喜欢钱很正常,但是不义之财就是肮脏的,这样得来的钱,还会使人干出令人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人的虚荣心有时会害了自己,有人为了面子和地位,故意地在别人面前不住地表现自己,吹嘘自己,这也是我最厌恶的一种人;还有的人是虚有其表,嘴上说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自己却不愿做出任何实际行动,真乃“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的道理。这也使我像起一副对联来: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就是在狠批那些没有半点本事,却爱自吹自擂的那些人。其实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未来的人干出什么荒唐事来都说不定呢!人有丑恶的一面,也有善良的一面:有时很乐意帮助别人,这时人的心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主动帮助有困难的人。这时,别人回高兴,会感激。得到别人这样的心理回应后,自己当然会快乐;有时可以丢掉虚伪和骄傲,因为这两样东西,可能会改变大家对你的看法和意见,别人对你有个好印象,便会很乐意和你交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这是公认的事实;最重要的得有坚强的意志和精神,许多革命者便是榜样,正因为他们有了这种精神,才能流芳百世。就像高尔基所说,人的肉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一个坚强的灵魂。世界的确不公平,但是你能克服这种不公平的话,也许你就能取得成功。所以,人拥有坚强的意志是很重要的。其实我说这点只不过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它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我对人这两个极端的发现,同样也鼓舞着我——在丑恶的警戒下,在善良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怎样做人。正是我的不断创新和不断发现,我也琢磨出了一些新的大的道理,正因为有了这些道理,我的人生才能不断地向前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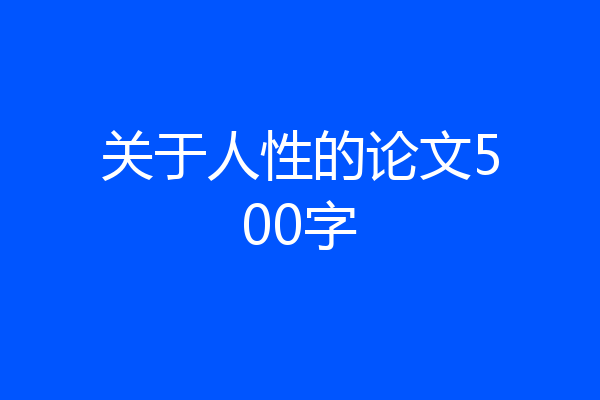
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康德认为以往人们所主张的人性本恶论或人性本善论都是从经验上来判断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诸多失误,甚至产生了如下的问题:是否存在中间状态,人类是既善又恶的、不善不恶亦或是部分善部分恶。由此,他首先指出通过经验来判断人性的善恶是不可靠的,并提出判断人性善恶的标准:“人们之所以称一个人是恶的,并不是因为他所做出的行动是恶的(违背法则的),而是因为这些行动的性质使人推论出此人心中的恶的准则。”也就是说,从经验中看人之行动结果的善恶(或好坏)并不能判断出一个人的善恶,而只能依据人心中的善恶准则来判断,这实质上是将人的善恶问题追溯到人的本性上。一、人的本性在康德著作的中译本中人性既作为人的本性(human nature)的简称,又作为一个专业术语(huinanity)具有独特的含义:就前者而言,“本性”(nature)一词在西方有两层基本的含义:一是自然,二是本质。相应地,“人的本性”可以区分为人的自然性和人的本质性。人的自然性指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这是一种事实上的界定。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几乎都承认这样的事实,人既像动物一样要求满足感性的肉体需要以维持其生存,又高于动物而具有理性能力,要求满足理性的追求。康德的有创见之处在于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现象界与本体界两个领域,认为感性的人属于现象界,服从自然规律,理性的人属于本体界,拥有自由,但作为两者的统一体的人本身既属于现象界又属于本体界,因此人成为宇宙中最特殊的存在者,即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或具有超越性的感性存在者。在康德哲学中,理性通常指宇宙中一般的理性存在者(包括神在内)的理性,理性摆脱了现象界的一切束缚,具有完全纯粹的自由,是本体界的象征,体现着一种超越性,因而又是一种神性。虽然人既有感性本性又有理性本性,但康德并不认为二者平等地分割了人,而认为理性高于感性,感性只是维持人之生命生存的必备条件,理性却代表着人的真正本质,彰显着人性(humanity),“人之为人,就在于他的不可规定性和无限可能性。人是无限可能的,人是能创造奇迹的”。就康德对人之本性的区分而言,人的自然性无疑是一种自然的善,因为感性本性使人得以生存,理性本性使人摆脱动物性,得以成为人,但是它并不涉及道德上的善恶问题,因为人作为被造物,服从绝对必然的自然法则,就算人做出恶的行为,也可以归咎于自然,是自然创造了作恶的人。但是从人的本质性来看,人的理性高于感性,人是自由的行动者,能够出于自己的意愿摆脱感性的束缚而做出善或者恶的行为,这些行为并非自然造成的,而是由人自己造成的,必然涉及道德上的善恶。因此,康德对人的本性之善恶的探讨建立在人的理性本质论的基础上。二、人性善恶的可能性为了表明这一立场,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对“本性”给予了进一步的澄清:“如果本性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显然,“一般意义上的本性”是人的自然性,与之相对的本性是人建立在理性本质上的自由本性,康德说:“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本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本性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在此,人的本性被赋予了具体的含义,它是人在现象界中可察觉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这种主观根据处于本体界中,指向人对自由的一般的运用。我们知道,人对自由的一般运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一般实践理性对自由任意的规定构成日常生活中明智的行为的规定根据,主要体现为目的和手段的考虑,人虽然受到感性欲求的驱动,但是能够克服感性的一时诱惑而坚持长远的目标直到实现,其目标可能仍然是感性的,比如猎人抛出诱饵、农夫留下来年的种子等;二是纯粹实践理性对自由任意的规定构成道德行为的规定根据,道德上的善就是遵循道德法则的行动,道德上的恶就是违背道德法则的行动,因此,康德在探讨人在道德上的善恶问题时更加强调遵循客观的道德法则的条件下也就是人一般地运用自由的第二个方面。由此,康德认为人天生是善的或者天生是恶的无非意味着“人,而且是一般地作为人,包含着采纳善的准则或者采纳恶的(违背法则的)准则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无法探究的)原初根据,因此,他同时也就通过这种采纳表现了他的族类的特性”。作为整个族类,人天生的善恶在于人的本性中既包含采纳善的准则的主观根据,也包含采纳恶的准则的原初根据。康德说人的本性中有三种向善的原初禀赋。(1)动物性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具有自我保存、种族繁衍和与他人共同生活的社会本能,这种禀赋属于纯粹自然的、无理性的自爱,在其上可能会嫁接各种各样的恶习。(2)人性的禀赋。人是一种有生命同时又有理性的存在者,这种禀赋属于有理性的自爱,在与其他人的比较中判断自己幸福与否,在其之上可能嫁接文化的恶习,随之达到最高程度的恶劣性,便成为魔鬼般的恶习。(3)人格性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有理性同时又能够负责任的存在者,这种禀赋就是一种道德情感,使人易于接受对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的敬重,仅仅以纯粹的实践理性为根据,使道德法则作为任意的充分动机,在这种禀赋上绝不可能嫁接任何恶习,因此康德认为,人格性的禀赋是唯一真正可靠的原初禀赋,是道德法则和敬重情感的真正体现,是人类与恶做斗争的坚强力量。显然,人的向善的原初禀赋的三个层次是依照理性来区分的,昭示着人能够逐渐摆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也就是逐渐趋向道德的过程。 人的本性中趋恶的倾向有三个层次。(1)人性的脆弱。人心在遵循已被接受的准则时往往软弱无力,“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2)人心的不纯正,即混淆了非道德的动机和道德的动机,致使合乎义务的行动并不是出自纯粹义务的,而是为了其他的动机或目的。(3)人心的恶劣或人心的败坏。人心具有接受恶的准则的倾向,也叫做人心的颠倒,在行动中将非道德的动机放在选择的首位,而将道德法则的动机置后,这种倾向在根本上是恶的。所有的恶在人性上都只是意念性质上的恶、潜在的恶,只是一种趋恶的倾向或主观可能性,而不是现实的恶行。在本质上,恶是由于人类虽然有理性、但缺乏遵循道德法则的坚定意志力量而产生的。总体来看,人的本性的善恶只是两种主观上的可能性,无论向善的禀赋还是趋恶的倾向都只是为人在现象界中可感知的行为的准则提供了主观根据,在其准则没有得到选择之前,人不能被评判为善的或者恶的,因为“善和恶必须是他的自由任意(任性)的结果”,我们必须从自由的任意中寻找善恶的源头。三、人性的善恶是自由任意的结果自由的任意是人的一种欲求能力。按照康德的划分,欲求能力有高级和低级之分,高级欲求能力是自由意志,意志是欲求能力的主体的意愿本身,意志自身根本没有自身的规定根据,就它可规定任意而言,它就是实践理性本身;低级欲求能力是任意或选择能力,可分为动物性的任意和自由的任意,动物性的任意是只能由爱好(即感性冲动、本能等)所决定的任意,其规定根据植根于对象,自由的任意是任何一个主动的有意的行为,是纯粹理性所能规定的任意。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人的意志是一种不完善的意志,虽然受到感性冲动的影响,但同时又能够独立于感性而具有自决的能力,归根结底就是自由的任意,居于动物性的任意和神圣意志之间。康德说:“在实践的理解中的自由就是任意性对于由感性冲动而来的强迫的独立性……人的任意虽然是一种arbitrium sensitivum,但不是bruturn,而是liberum,因而感性并不使它的行动成为必然的,相反,人身上具有一种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自行规定自己的能力”,“任意的自由是独立于感性冲动对它的规定的;这是自由的消极概念。自由的积极概念则是:纯粹理性使自己对自己成为实践的能力”。可见,自由的任意的自由不仅因其对感性冲动的强迫的独立性,更体现其自己规定自己的行动的绝对自发性。除此之外,任意的自由还具有一种极其独特的属性:“它能够不为任何导致一种行动的动机所规定,除非人把这种动机采纳入自己的准则(使它成为自己愿意遵循的普遍规则);只有这样,一种动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动机,才能与任意的绝对自发性(即自由)共存。”这是因为任意为了运用自己的自由必须为自己制定一个规则,亦即一个准则,由此,任意在实行的过程中可以不受任何动机的规定,无论是感性欲求的客体还是在理性判断中作为动机的道德法则,都不能对人加以规定,除非自由的任意将其纳入准则而引发行动。准则是人的主观原则,康德认为,“自然的每一个事物都按照法则发挥作用。惟有一个理性存在者具有按照法则的表象亦即按照原则来行动的能力,或者说具有一个意志”,一个理性存在者的行动必然受到原则的指导和规范,没有原则的意志不能付诸行动。原则有主观原则和客观原则之分,在行动的选择中主观原则就是准则。准则“包含着理性按照主体的条件(经常是主体的无知或者偏好)所规定的实践规则,因此是主体行动所遵循的原理”。准则往往是每个人出于自己的感性爱好所选取的,只适用于单个的主体,具有主观性,缺乏普遍必然性。与准则相对的就是客观原则,客观原则就是法则,是对每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提出的理性原则,它要求人的理性完全控制欲望,不仅是理性完全摆脱人的感性影响,而且是理性自己为意志立法,具有严格的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所谓道德上的善,就是自由的任意将道德法则作为动机纳入自己的准则,相反,道德上的恶就是自由的任意将与道德法则相反的动机(即感性动机)纳入准则。既然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必须按照原则才能行动,亦即必须通过任意将动机纳入准则的方式才能行动,并且按照人的本性,除了出于理性本性提供的道德法则充当的动机,还有出于感性本性提供的感性欲求对象提供的动机,“假如法则并没有在一个与它相关的行动中规定某人的任意,那么,就必然会有一个与它相反的动机对此人的任意发生影响;而且由于这种情况在上述前提下只有通过此人把这一动机(因而也连同对道德法则的背离)纳入自己的准则(在这时他就是一个恶的人)才会发生,所以,此人的意念就道德法则而言绝不是中性的(决不会不是二者中的任何一个,既小是善的也不是恶的)”。由此可以看出,人在道德上要么天生是善的,要么天生是恶的,没有中间状态,因为道德法则是唯一的、普遍的,一旦人将其纳入自己的准则作为行动的规定根据,就不可能将与其相反的动机纳入准则,否则就会出现自相矛盾,这正是康德关于道德善恶的严峻主义观点。
在这个高度发达和充斥人类对利益歇斯底里的呐喊的世界,物欲的洪流似乎可以将任何一样事物泯灭和扼杀:传统、礼教、良知、道德甚至是灵魂。然而,也同样是在这个世界,同样上演着让我们心灵颤动、思想震撼的一幕幕……“当——”一声清脆的撞击,一枚硬币落在了一个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破旧的罐子里。在哥特式建筑的中央,从衣衫褴褛的乞丐混浊的瞳子里映出了一个清晰的身影,尘土似乎掩盖了这张历经风雨的如雕像般的面孔上的皱纹,但感激之情却更加清晰地从瞳子里流露,微微翕动的双唇祝福着好心人:“神与你同在,好心人!”远处的教堂的钟声琅琅响起,簌簌的雪花震落下来,轻轻地,融化在这片欧罗巴的天空。在被炙热的太阳烘烤下的土地上,一群瘦弱的人伫立着,望向远方。嘿嘿的眸子里笼罩着饥荒、干旱、疾病、恐惧的阴影。炎炎的烈日好像要将一切的生机扼杀。这群人渴求着对他们的生命至关重要的食物和水。而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在这比他们更贫瘠的土地上等待救援。终于,地平线上响起了阵阵轰鸣,装载援救物资的车队终于赶来了!人们挥起了黝黑而瘦弱的双臂,舞动在这人类起源的古老土地上,无望的眼光中终于有了跳动的希望。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还有那美丽的古巴比伦王国,似乎将美丽定格在了那遥远的过去。如今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硝烟和战争的疮痍,辛勤的人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隆隆的炮声和喷着火舍的枪口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更夺走了他们的幸福。巴格达的儿童那噙泪的双眸写满了失去双亲的悲痛;费卢杰医院里充斥着对战争无奈的呻吟;巴士拉的幸存者在废墟中找寻着亲人的尸体,他们却已是天人永隔。这哀怨的眼神,穿透了时空的阻隔,祈求着死者的灵魂能够获得安宁。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反战人士正高举着旗帜,抗议这不义之战。给饱受战火折磨的苦难的人们心里带去一丝慰籍。每当我们看到身旁的人正遭遇着不幸,承受着不该承受的痛苦,我们心中至真至善的情感就会触动,让我们坚定的站到弱者的一边,用我们人性里不受玷污的爱去呼唤和平,安宁和幸福。世界有爱才转动,有爱,就会有希望!
人性的光辉 在灾难中彰显人性的光辉 用人性的光辉 谱写生命的赞歌! 那一刻,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我国四川省以汶川县为代表的小县城,发生了8.0级大地震。这场地震,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派出救援队、医疗队,直奔灾区,积极去营救每一个人;各地人民捐财捐物,还有的自费去灾区,当一名志愿者......促使他们做出这一切的是什么?是爱,是人性爱,也是对亲人的爱。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由于爱,一份份物资及时到达灾区;由于爱,使得全中国更加团结,更加凝聚...... 我曾经听过一个发生在灾区里真实的故事:有一个父亲,他也是救援队中的一员,他的孩子也是地震的受难者。他在营救他的孩子时,忽然发现:如果要救他的孩子,那么,他将跨过很多孩子。于是,他决定先救其他的孩子,而当他救到他的孩子时,他的孩子已再也无法叫他一声“爸爸”了...... 像如此的事情,在灾区里还有很多,很多。而这其中所闪亮着的,不是爱吗?是爱促使着人们,去拯救他们;是爱促使着人们,去不断寻找着幸存的生命。 生命是短暂的,是脆弱的;而爱是永恒的,是延续的。爱所放射的刺眼的光芒,会永远照亮晦暗,留下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