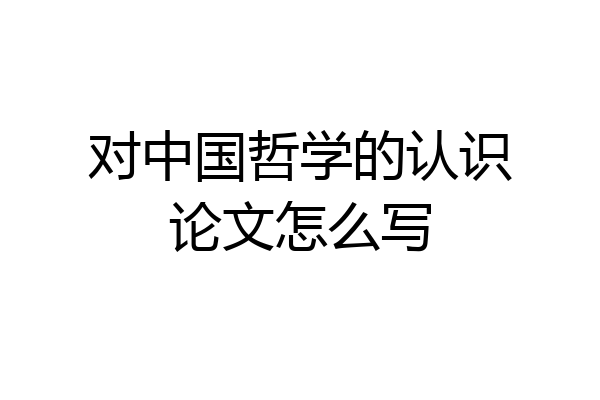无情地平A
无情地平A
所谓“天人合一”,可以看作一个命题,也可以看作一个成语。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先秦时代,而这个成语则出现较晚。汉代董仲舒曾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1)又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2),但是没有直接标出“天人合一”四字成语。宋代邵雍曾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3)“际天人”即是通贯天人,也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也没有提出这四个字。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四字成语的是张载,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4)他又说:“合内外,平物我,自见道之大端。”(5)“天人合一”亦即内外合一。程颢也讲“天人一”,他说:“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6)但他不赞同讲“合”,他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7)程颢讲“不必言合”,可能是对于张载的批评。张程用语不同,但是他们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思想还是基本一致的。我们认为用“天人合一”来概括这类思想还是适当的。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天,在不同的哲学家具有不同的涵义。大致说来,所谓天有三种涵义: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由于不同的哲学家所谓天的意义不同,他们所讲的天人合一也就具有不同的涵义。对于古代哲学中所谓“合一”的意义,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张载除了讲“天人合一”之外,还讲“义命合一”、“仁智合一”,“动静合一”,“阴阳合一”(8);王守仁讲所谓“知行合一”(9)。“合”有符合、结合之义。古代所谓“合一”,与现代语言中所谓“统一”可以说是同义语。合一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立的两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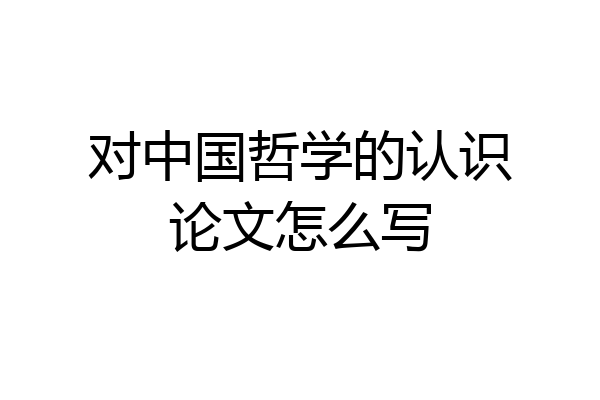
中国哲学是人类的源始哲学中国哲学是人类的源始哲学的哲学根据是,西方哲学的根本哲学原理:哲学的本体决定哲学的主体。中国哲学是一切哲学的本体,则中国哲学就是人类的源始哲学。源始哲学对于哲学自身的自性本然的规定性是:哲学研究同在存在的时显和哲学研究同在时在的实在存在的时显。源始哲学规定:哲学不去直接研究在与自在,哲学不直接研究单一的在与自在的连续消息的变化。哲学通过同在存在的时显和同在时在的实在存在的时显,间接研究同在存在和同在时在的实在存在之中的在与自在的时显过程之中的相对变化,形成了源始哲学的范畴结构,构成范式和构成范例的时显。时思的人为构成的展开,成为人为的时体范畴结构的构成范式,时思人为地将构成范式的时物,再人为的加入具体时料,人为的构成了具体的时物,时思人为的将具体时物展开的演示和推论,为时显的自然开显,由于时物之中的构成具体实物自性本然的连续消息与时偕的共时性集合,自然的发生了具体时物和具体时料的离散消息的自显开显和与时偕行的自然的时显。后来哲学的所谓本体决定主体,绝对不能够成为哲学的说一说而已,本体决定主体就是源始哲学对于意识思维模式的许多的规定性。源始哲学揭示并且规定:时者是意识思维过程的最高统摄者,最权威的规定者,也是最高统治者。但是,时者统摄与规定必须要效法自然的自性本然的时质和时量,时者不能统摄和规定时量,时质,时显。时者不能够以统摄和规定的方式决定时显和时显结果,是源始哲学对于后来哲学极其重要的哲学性质的规定性。源始哲学规定:哲学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集合表达,哲学不只是哲学家的思维方式。源始哲学规定:时者的实在存在,是每一个人都自明性的知道时者实在的存在。
一般说不有三种:天人合一说;天人相分说;天人相胜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天人合一说始终占主导地位。天人相分说是荀子自然观方面的主张。荀子肯定“天”是自然的天。自然界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受人的意志支配。同时天也管不了人事 这种论证“天”与人类社会的治乱毫无关系的“天人相分论”,第一次从理论上把人与神,自然与社会区分开来,是对天命论的有力批判。天人关系是传统儒学的重要议题。这里的天有两种意义:一是指大自然,另一是指人从大自然领悟出的一些规律与道理,即所谓“天道”。前者指大自然本身,后者指大自然的精神。当谈到天人关系时,“天”有时指前者,有时指后者,有时两者混用,不分彼此,视其内容而定。例如周易中的天乾地坤:天、地是大自然,乾、坤是其精神,乾道是刚与健,坤道是柔与顺。天人交相胜是中国唐代刘禹锡关于“天人关系”的问题观点。他在《天论》中作了阐述,起含义是:自然界(“天”)和人类社会具有各自的规律。它们的只能各不 刘禹锡相同,有时人胜天,有时天胜人。这种观点指出社会和自然的区别与联系,主张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并强调人对自然的能动精神。比起古代片面宣扬天人和一是一个进步。“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对这个概念而言,董仲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战国以前的儒家只言阴阳而不论五行。而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合流并用,他一般还被看作是儒门解易的第一人,其代表作为《春秋繁露》。 对天人合一观念需要小心翼翼地分析。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研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部分哲学家把天理解为自然,于是天人关系即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此相应的哲学观点大致分为两派。一部分人,例如道家,特别是庄子学派中的一些人物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消极被动的。因而提倡无为,绝对地顺应自然过程。当代西方某些环境悲观主义者主张人类放弃现代文明,回到原始时代,与这种思想是一致的。另一部分人,例如战国时代的荀子、唐代的刘禹锡等,肯定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倡“制天命而用之”,即利用自然规律造福人类。显示出开发自然的进去精神。中国古代哲学家讨论天人关系,目的在于寻求人生目标。当代某些学者从战略上研究社会发展机器与环境关系,也利用类似的方法论原则。如强调按照环境的约束条件或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目标来规划社会发展,确立相应的价值观念等。这种方法原则是环境条件乃至生态规律对社会和人生目的制约作用的反映。如果由于知道思想不同,或对天人关系的实际状况的判断不一致,采用上述方法论原则并不一定导致相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