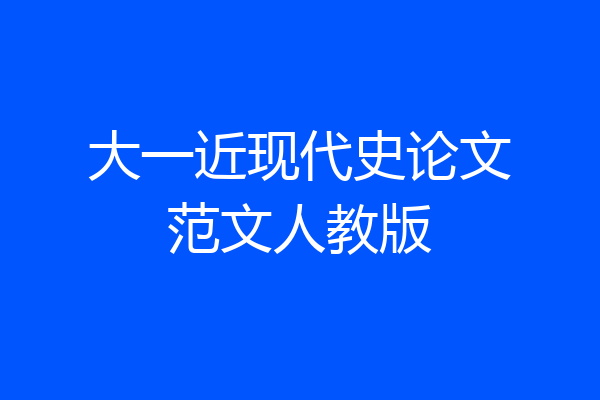牧羊歌女
牧羊歌女
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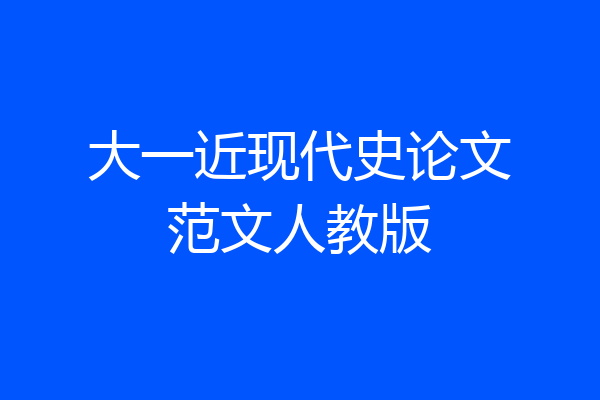
重看洋务运动的成败 这是一场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运动。他在中国饱受凌辱,开明地主想挽救国家危机时开始,失败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 这是场注定失败的运动,就像好多书上所说的那样。1、倡导洋务的几个大臣都是满清高官,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目的是维护清朝的统治。2、洋务派搞此运动的方法是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不是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体制。3、 仅靠地方上几个积极的大臣搞,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造成了活动的涣散,难成大器。这就是现代史学界给洋务运动失败定下的三大失败理由。 我的对这三大理由感到不满。 第一,些史学家们首先就提出了阶级问题。“阶级”是一个令人反感的词,这是人由人划出的。本来一个国家的人很团结的,非要划出三六九等,分化穷人,富人,中产阶级。评价历史事件也是,封建大地主大官僚,明显是贬义词,让人一看就感觉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中棠是坏蛋。洋务派的人确实为当时中国作了不少贡献,左中棠亲自出征收复新疆,他们在各地办新式工业厂局,新式学校,这些功劳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因为阶级这两个字。比如,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通常是说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软弱性。但是,对于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评价,却说成是反动势力的强大,为什么不说成工人阶级的XX性呢? “阶级”确实是一个很迷惑人的词,如果看了一些评价性论文,很容易被这个词给套住思维。所以,我认为,评价洋务运动的成败要先撇开什么阶级原因。我认为着第一条失败理由应该是这样:由于李曾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局限性,比如保守,封闭,导致思想肯定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造成了洋务派行动上不同。我想这只是时代的局限。 第二,按一些史学家的话来说,应该直接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政治体制,而不是搞什么技术。试想,这样可能吗?如果让他们向原始人来传授资本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不相信原始人会接受的了。试想,在原始人中间实行资本主义,这可能吗??这肯定不可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知道这个原理的话,就很容易来理解洋务派学习先进技术的原因:当时清政府正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通过与外国军队的合作中,李曾等人认识到洋人先进的兵器的威力,认识到洋人机械的先进,这样他们自然,而然萌发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引进西方先进设备的念头。这在当时是适应历史潮流的,大多数中国人接触西方肯定不是像极少数的留学生那样,从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体制开始的,大多数的中国人接触西方还是要从接触其先进神奇的机器设备,技术开始。我觉得正是洋务运动的开始才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来出现的可能。 很多人都忽视了洋务派关于培养新式人才的做法。比如送一些儿童出国留学,开办新式学堂,新式图书馆,给当时中国大众的思想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有了洋务派引进新机器,技术作铺垫,人们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也就自然一点。所以我认为洋务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没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是“器物”上的学习,这点理由有点牵强。有力证明就是之后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次运动是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标准的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可结果还是失败了。 第三,洋务派搞的洋务运动,对清政府来说,是一次合法的运动。我想一次合法的运动是有必要在中央搞一个指挥机构。但清政府又不是李鸿章曾国藩家的,建立一个什么机构不是那么随便的,搞不好还会被安个犯上欺君的杀头罪。况且李张等人又是位高权重,我想,搞一个中央性的,特别是能指挥得了李曾等人的机构,实在不好成立。再以前后史实为例,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都是有一个中央指挥机构,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关于对洋务运动“难成大器”的评价,我更不苟同。洋务运动为近代中国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这次运动引进许多先进的机器,设备,可以说为中国的近代化工业开辟了先河;又是戊戌变法甚至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基础,如果这样还是没有成“大器”的话,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所谓的“大器”。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不可忽视的运动,也是中国试图解救民族危机,振兴民族的一种尝试,虽然它失败了,可是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凭这点就应该向这次运动致敬。所以,我认为应该把这点的原因变一下。此次运动清政府的态度仅仅是中立,而洋务派当时的做法在民间看来简直是劳民损财,这样洋务运动虽然兴起了,但是却没人响应,使洋务积极分子热情减退,致使洋务运动后期都没有什么新的作为。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得出上述结论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洋务运动的目的虽说是维护清朝统治,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但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你可以去维普,万方数据,超星什么的去下载专业的论文吧,这边贴的都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