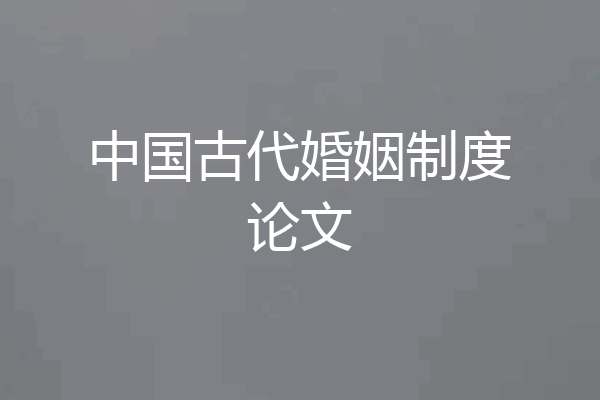shaelly1020
shaelly1020
一、中国古代的形式婚姻制度 中国古代婚姻非常注重形式,婚姻必须符合形式要件, (1)结婚的形式。按周礼之 其次,婚姻关系的缔结除必须符合以上 “六礼”的名称和仪式,在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发展 (二)离婚的形式。在我国古代,解除 在古代,解除婚姻关系也有一 “七出三不去”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二、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婚姻 原始社会后期,由群婚制变为对偶婚制, 进入阶级社会后,男子居于绝对 周朝则吸取了夏商的教训, 一夫一妻制并不能限制周王与贵族占有妻以外的多 “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核心在 三、中国古代的阶级婚姻制度 中国古代无论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其实都是 在夏商周三代即严格实行贵族内部婚姻,贵 唐太宗时为废除土族制度,曾下令将修 四、中国古代的政治婚姻制度 所谓政治婚者,即婚姻对国家、对家族的意义远远大于个 中国婚姻的政治色彩表现 五、中国古代的畸形婚姻制度 (一)掠夺婚。又称“抢婚”, (二)包办婚姻。中国古代婚姻中最具本质特色的 (三)买卖婚姻。是男子以金钱或实物换取 (四)交换婚姻。也称“互易婚”,是双方父母 (五)赘婿婚姻。赘婿俗称“把女婿”, (六)童养媳婚姻。童养媳乃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 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 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 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中国婚姻关系的本质精髓所在,即为“伦理”。它刚开始是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习俗以及道德观念而存在,直至唐朝才以法律的形式完整而全面的确认了这种封建伦常关系,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即《唐律•户婚律》。《唐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婚姻家庭制度包括了婚姻关系的缔结、保持以及解除。在此本文仅从婚姻家庭制度中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来看唐朝伦理道德思想渗入社会生活乃至婚姻关系的状况。 《唐律•户婚律》对离婚有二种规定。第一,强制离婚,它包括官府强制离婚和丈夫强制离婚。官府强制离婚是指夫妻凡发现有“违律为婚”、“嫁娶违律”、“义绝”者,实施强制离婚。丈夫强制离婚是指妻子犯了“七出”之条,丈夫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的“出妻”“休妻”;第二,协议离婚,是指夫妻双方自愿离异,即所谓“和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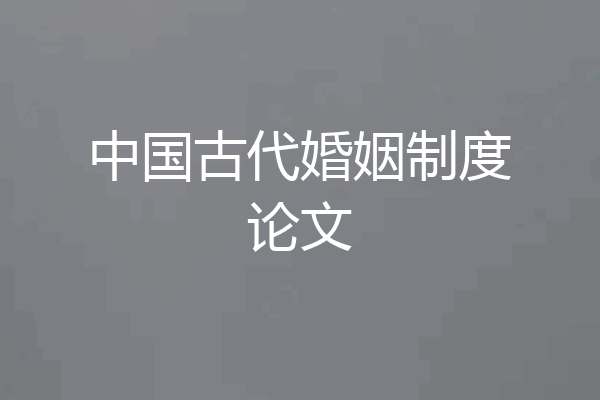
西周的婚姻制度对後世影响极大。西周时期,缔结婚姻有三大原则,即一夫一妻制、周姓不婚、父母之命。凡不合此三者婚姻即为非礼非法。一夫一妻制是西周婚姻制度的基本要求。虽然古代男子可以有妾有婢,但法定的妻子只能是一个,而且只有正妻所生子女为嫡系,其他皆为庶出,在家庭中处於较低的地位。“同姓不婚”是西周时缔结婚姻的一个前提。西周实行同姓不婚原则,主要基天两点:首先,长期经验证明,同姓通婚会影响整个家庭、民族的发展;其次,禁止同婚通婚,多与异姓结好,可以“附远厚别”,即通过联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巩固自己的统治。“父母之命,媒说之言”是西周缔结婚姻的又一原则。《诗经》即说:“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在宗教法制下,必然要求由父母家长决定子女的婚姻大事,并通过媒氏的仲介来完成。否则即是非煽非法,称为“淫奔”,不为宗教和社会承认。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应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与“妾”无论从身份、地位和礼节上,都是绝不可混淆的。 妻,是丈夫的法定配偶,家庭的女主人。在迎娶仪式上,必须经过很正规繁杂的礼仪程序。从周朝开始,便形成了所谓的“六礼”,作为婚娉的标准仪程。这六礼是:纳采(提亲),问名(询问女方姓名和生辰),纳吉(到庙中根据双方姓名和生辰占卜吉凶后定亲),纳征(正式送聘礼),请期(确定婚期),亲迎(男方迎接女方到家)。六礼除了最后一步,前面各环节都要向女方赠送礼物。经过如此正规的仪程,就是为了显示婚姻的重要性,也是对妻子的尊重。 到后世,随着“礼乐崩坏”,实际的婚娶未必有那么麻烦,但也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既然是一生的大事,不仅关系到男女双方,同时也是两个家庭乃至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结,因此很讲究“门当户对”。
从婚姻的原则看:古代婚姻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指主婚权属于父母,即选择配偶,嫁娶方式均由父母做主,而不问男女双方本人的意愿,实质上就是父母包办婚姻。《诗经·齐风·南山》“娶妻何如,必告父母”; 《孟子·滕文公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恩格斯也指出:“古代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媒妁之言”是指婚姻由第三人即“媒人”撮合,它是父母包办婚姻不可缺少的终结,是包办婚姻的组成部分,与父母之命共同构成封建婚姻成立的要件。例如唐律规定:娶妻无媒不可,正所谓“名媒正取”,合礼合法。媒妁在古代之所以重要,在于协调宗族关系,成为宗族联姻的一个桥梁。古人讲究“和”与“睦”,宗族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通过媒妁,缔结成良缘,“合二姓之好”,使两家建立亲属关系;事情办不成,由于双方有媒妁作缓冲,就不会发生直接正面冲突。“父母的意志为子女婚姻成立或撤消的主要的决定条件,他以自己的意志为子授室,为女许配,又可以命令他的子孙和媳妇离婚,子女的意志从来就不在考虑之列。”[1]“家长有包办子女婚姻的权力,无论子女成年与否,他们的婚事都依据家父的意志决定,甚至无须询问本人的意见。”[2]《孔雀东南飞》一文中焦仲卿和刘兰芝故事让人潸然泪下,因婆婆不喜欢媳妇,百般刁难,使得女方在再婚当天“举身赴清池”[3],投河自尽;男方也“自挂东南枝”,上吊自杀了。陆游与唐琬,只能垂泪吟诗:“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4]酿成这样的悲剧原因何在?归根到底就是所谓的“父母之命”。为什么古代能奉行包办婚姻,使子女的婚姻权利掌控在父母的手中?婚姻家庭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形式。中国古代这种婚姻家庭制度是当时社会性质的体现,并与当时社会形态相适应。《礼记·昏义》:婚姻的目的是 “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缔结婚姻一方面是为了外部关系,即“合二姓之好”,也就是通过婚姻这一纽带将两个宗族连接起来,结成一种亲属联盟。古代婚姻是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的,并不考虑男女当事人双方的个人利益,所以婚姻制度在我国古代往往带有婚姻以外的政治含义。 另一方面是考虑内部关系,即“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就是祭祀祖先,延续后嗣,古代社会的婚姻主要是用于传宗接代,维系宗法血缘关系,使家庭兴旺,长盛不衰。总之,不管婚姻关系的缔结还是解除,都是出于家庭、家庭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当事人个人的幸福;婚姻行为实际是家族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家系和宗族利益是包办婚姻的唯一基础,既然是出于亲属集团的利益需要,是家族行为,自然家父和丈夫在家庭中居于至尊地位,妻子和子女则处于无权和服从地位,甚至没有独立的人格,更没有什么婚姻自由可言。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5]中国最早的辞书《尔雅》对“孝”的定义为:“善父母为孝”。“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拆我树杞。岂敢爱也?畏我父母,仲可槐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孔子认为“孝”必须 “无违”。无违就是绝对服从。而古代婚姻包办性已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一“孝的文化”的影响。《孝经》所宣称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意也,民之行也” 在古代中国子女心中根深蒂固。他们认为“父母之命”是天经地义的,毫无自我意识。这一思想的禁锢让中国古代的男女本人在很多场合被置于契约客体的地位,却毫无反抗意识。在古代社会中,在运用思想统治这一“软兵器”的同时,还适用法律这一“硬兵器”以确保婚姻制度的目的。夏商以来形成了“罪莫大于不孝”“罚莫大于不孝”的罪行观念及制度。唐律将“不孝”作为“十恶”罪名之一,“不孝”包括告发或咒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世而别籍异财或供养有缺,不按规定服丧等,确立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原则。古代的“孝”强调它与宗法等级关系密切相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宗法制下父母尊长对子女卑幼的支配权,主婚权就是对人身支配权重的典型。社会上这种宗法等级制度其实是阶级对立关系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男女本人之个性的、情爱的要素被极端地忽视,尤其是女性在这一方面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6]两性地位的等级性是古代婚姻制度的另一特征,封建社会中妇女是弱势群体,毫无地位可言。恩格斯曾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便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思想和制度都是极为突出的,男主女从的不平等关系为封建的礼教和法律所确认,并得到严格的保护。《仪礼·丧服》载:“夫,至尊也。” “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7] “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也。妇者,服业,服于家事,事人者也。”[8]“夫为妻纲”,是封建伦理纲常中的“三纲”之一。这种夫权统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在夫妻关系上的反映,是与封建社会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紧密相关的。女性在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卑贱、屈从、依附、遭奴役的地位。《礼记》阐述妇女必须遵守“三从”“四德”, 《女诫》规定“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认为女子应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一而终”充分说明了夫权的绝对威严和妇女地位的极其低下。夫妻之间,无论是人身关系,还是财产关系,丈夫均处于支配、命令者的地位,妻子则只有屈从。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封建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无权处理家庭财产,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古代女子根据父母的意思一旦缔结了婚姻,就是确定为夫家之成员,在夫家遭受不幸,关系恶劣并受到虐待的场合,社会一般不可能以援救媳妇的立场,加以尝试有效的干涉。这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已经背负了太久太久!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方式也具有独特的一面。中国古代传统法制以维护家族、宗族、国家等团体利益与集体和谐为宗旨,强调社会成员的服从义务,权利意识受到一定的压制,故刑事、行政等公法体系相当发达,民事之类私法相对滞后。有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刑法和行政管理法的“附属规范”,在法律体系中并未取得独立地位,而是包容在统一法典之中。如从汉朝开始通常以“婚律”“户律”“户婚律”或“婚户律”之名置于诸法合体的成文法。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是来源于礼制的习惯法。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是被称为“不得与民变革”的永恒准则,也是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最高原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是处理亲属关系的基本伦理要求;“六礼”、“七出”、服制等等都带有宗族习惯法的性质;记载西周政治体制及政府职能的《周礼》则规定了婚姻家庭事务的管理机构和执法标准。在以上四个部分中,除了伦理规范之外,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宗族习惯法和婚姻行政管理制度都可以纳入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的范畴。我国进入阶级社会起,宗法制度便起了支配作用,宗法的精神和原则——尊尊、亲亲、男女有别是封建家庭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因此,调整封建家庭的民事立法,是以保证父权,夫权为主要宗旨,它体现在婚姻继承各个方面。但是封建民法中所规定的子女对尊长的赡养义务,虐待父母的子女不得享有继承权,对于维护家庭的稳定性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也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剔除封建家庭法的糟粕仍有值得批判继承的内容。[9]在学习古代婚姻制度过程中,我们看到家长漠视子女的权益,专制独断,将其婚姻当作政治筹码,看到女性背负两千多年的沉重枷锁,看到古代男女婚姻的悲惨与不幸,看到了古代婚姻的包办性、人身的依附性、家庭关系和两性地位的等级性等突出特征。两千多年来,中国婚姻立法有无至有,其间经历的艰辛可想而知。今天,我们需要总结中国法制历史的丰富经验,做到鉴古明今,古为今用,总结建国以来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吸收外国法律知识,在完善婚姻家庭等单行民事法的同时,促进民法典的诞生。
婚姻形式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重亲。重亲就是婚姻之家再结婚姻,即所谓“亲上加亲”。重亲可分三种:姻家恒为姻家,婚家恒为婚家,还有姻家、家互为的情况(指《仪礼士昏礼记》的说法,女氏称婚,婿氏称姻)。这种情况,按历史记载,多实行于王室、贵族,当然民间也有,只是未具体地记载于历史罢了。由于亲上加亲,就结成了一个个颇为复杂的关系网,如《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嘉薨,子立嗣。荒王女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宝兄子昭为立后。”至于下面一种情况就更复杂了。《后汉书·耿弇传》:“父况,及况卒,少子霸袭父爵。弇卒,子忠嗣。忠卒,子冯嗣。冯卒,子良嗣,一名无禁,尚安帝妹濮阳长公主。……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女金卒,子喜嗣。喜卒,子显嗣。显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长社公主。……牟平侯舒卒,子袭嗣。尚显宗女隆虑公主。袭卒,子宝嗣,宝女弟为清河孝王妃。”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其实质是为了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相互扶持,相互利用,从而用重重的婚姻形式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关系。从这也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婚姻很少是爱情的结合,往往是以家族利益为前提的。由于“亲上加亲”,结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网,婚姻有时是在同辈之间进行,有时却是在不同辈之间进行。这并不是由于疏忽,封建宗法制度十分严格,这是马虎不得的,只不过是家族利益超过了对辈份的讲究而已。另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周制同姓不婚,而汉朝人结婚似不避同姓。如《汉书·王诉传》:“诉薨,子谭嗣。谭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由此看来,王莽和其妻是同姓。又如《通典》:“吕后妹嫁于吕平”,也是如此。用现代科学观点来看,同姓联姻,并非不可,因为同姓未必有多近的血缘关系。但汉代的不同辈通婚,尤其是血缘关系很近的不同辈通婚,如亲母舅娶外甥女、姨侄娶姨母、表侄娶表姑母等现象很值得分析。可以从政治利益高于一切来考虑,还可能是古代血缘婚的回光返照。由于原文实在是过长,此处只给你摘了一些摘要,具体浏览请见如下参照地址其实这在这点上,以家族为中心的政治婚姻,在欧洲封建社会也是存在类似的情况。你如果是论文的话,可以参照中西对比来得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