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ngfan411
wangfan411
我觉得这个哲学和人生是个永远让人去思考的答案只有在实践中慢慢去体会感受它给人带来前进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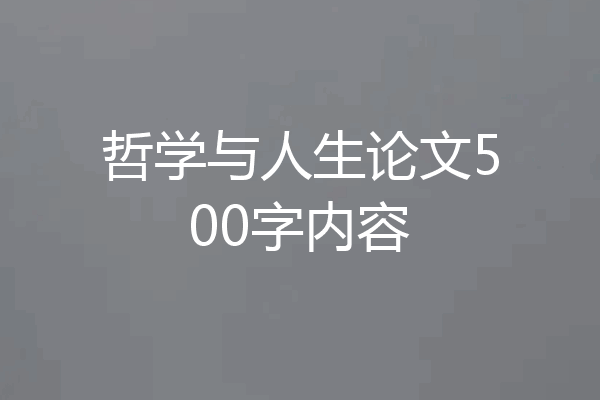
哲学 人生你想 做 好 人,你的前途就是光 明的;你想 做坏人,你的前途就是黑 暗的。很多人想 做 好 人,他就接 触好人;很多人想学佛,他就会见到很多善良的人;而有些人想钻空子,通 过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来达到他赚 钱的目的,他就会去接 触那些吸毒者、贩毒者和抢 劫者,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进监狱。那么这条路是谁给他的呢?就是他的心造成了他的果。师父经常讲一点人间的哲学给你们听,师父又跟你们讲佛法,佛法是融会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听啊?这就是原因。人所处的现实,实际上是由人的心念而来,其实你的心和念头在被现实所吸引住,那你就会进入这个现实当中。如果你的心念在正能量的照耀下,你的心念会处于正能量的状态;否则,你就会处于负能量的状态。为什么有人会得忧郁症?因为他恐惧,他恐 慌,他觉得世界上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陷阱,所以,慢慢地他就会待在家里不出去了,他害怕,他甚至害怕阳光。人家说阳光是正能量,他说阳光下有罪恶。要懂得,有时候人的心念和事实上的吸引力,是在一种没有办法觉察的情况下下意识地进行的。也就是说,我有时候想一件事情,是在我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没有感觉,我就做了这件事情,那到底对不对啊?有时候得罪人也是下意识的,讲一句粗话,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骂人、在讽刺别人,这都是心念所造。如果一个人的心念是消极、或者丑恶的,那他所处的环境也是消极和丑恶的;如果一个人的心念是善良的,那他所处的环境也是积极和善良的。这就是我们佛法所说的,种瓜得瓜,种善得善,种恶得恶啊。如果一个人能够控 制自己的心,就是自身思维,专注于有利于自己的积极、善良的人和事情上,那么这个人就会把有利的、积极的和善良的人和事物吸收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所以,控 制好你的思想、心念是命运修造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说,你一个人的好和坏完全是受于你自己的控 制之下,你想 做 好 人,你的前途就是光 明的;你想 做坏人,你的前途就是黑 暗的。很多人想 做 好 人,他就接 触好人;很多人想学佛,他就会见到很多善良的人;而有些人想钻空子,通 过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来达到他赚 钱的目的,他就会去接 触那些吸毒者、贩 毒者和抢 劫者,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进监狱。那么这条路是谁给他的呢?就是他的心造成了他的果。师父经常讲一点人间的哲学给你们听,师父又跟你们讲佛法,佛法是融会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听啊?这就是原因。有一位老居士问一位心灵法 门的佛友:“你们的师父好在哪里啊?”这位佛友回答道:“我们的师父讲的佛法我听得懂,而有些师父讲佛法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因为我没有比较,所以我就是找那些听得懂的佛法听。如果我听不懂,我怎么能够学习佛法呢?”事实就是这样的,佛法要让人听得懂啊,师父跟你们讲话,你们要明白啊,如果不明白,师父跟你们讲什么?师父最后跟你们讲,要深信因果定律。如果你们深信,我坚信某一件事情会发生,你不管这件事情是善的、还是恶的,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不要去相信不好的,要相信好的。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的,这件事情一定会有善果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今天相信警 察会来抓你,你想着想着,总有一天警 察真的会来抓你。人的心念很重要,一个人深信好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好事就会发生;如果一个人深信自己的生命很快就要结束,那么这个人很快就会死去。其实师父平常也跟你们讲了这些,师父为什么叫你们不要准备寿衣啊?不要准备 棺 材啊?不要去刻墓碑啊?因为人一看这些不好的东西,心态就不一样了。师父告诉你们,人的心是很怪的,回到家里看到一盆花,心情就好起来;看到家里地方很大、环境好,心情会好起来;回到家看到老婆开心,你的心情会好起来……这些全部都是受控于你的心。那么很多人会把一些不好的事情看成是好的,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有修的人,而一般的人只能看到现实所给他的反馈,让他从心中再反射 出一种爱和恨,高兴和悲伤。你们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人的心态完全靠自己调节,今天你说你不开心,你完全有可能让你自己变得开心,问题是你们有没有本事去扭转乾坤啊。用好的心念去取代不好的心念,这就是修心。你们有好的心念在脑子里,这就是福气,这就是一种福。没有福气的人,脑子里整天想着不好的事情;有福气的人,脑子里整天想着好的事情。要记住,人要在心态很放松的情况之下,才能取得好的修心效果,要放松,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为什么师父讲佛法人家爱听?几万 人的法 会现场,那么多人激动欢呼,因为他们是从心里感恩,为什么?因为师父讲到人家心里去了。有些人弘 法讲得再好,他讲不到人家心里去啊, 师父现在是讲到人家心里去了, 你们听得懂吗?放松学佛,任何心态、任何环境的变化,你都不能懈怠,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态不好,你马上就要调整。我今天不开心了,要有感觉,如果控 制不住,我会急躁,我会闯祸的,要马上调整心态,让自己开心,那么你会带来善的果。师父问你们,什么样的心态是最佳心态呢?师父把佛 学和人生的哲学放在一起讲给你们听。师父告诉你们,最佳的心态就是清净无念,我很安静,我没有念头,把目光瞄准在你想要的理想的人格和境界上。你到底想 做什么样的人?你肯定说,我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修心的人。那你就像好人那么去做,那你就像修心人那么去做,去瞄准你的目标,去争取你 的 人格。然后,你用自己的人格和这种境界去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然后放松心态,精进努力,该做的就去做,不该做的,就不要惦记着去做。这句话很有哲理啊。很多人问师父:“师父,这件事情我能做吗?”师父说:“不能做。”过一会儿,他绕着问:“师父,这件事情我可以做吗?”他连续问三次。这种人就是不听人家的,没有用的。很多人看医生时就是这样的:“医生,我这个药一定要吃吗?”医生说:“当然要吃的。”过一会儿又问医生:“我能不能只吃一点点?”医生说:“不行。”病人待会儿又问:“医生,这种药我能不吃吗?”医生被问烦了:“随便你了,你爱吃就吃,你的病不好,不要来找我了。”师父经常也是这样的。要懂得,不要老惦记着不该做的事情。已经不做了,就不要再去做了,就不要再去想它了,你还惦记着要去做,那你等到这些果来的时候,你会吃惊的,明白了吗?你在想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对结果非常的急躁:哎呀,我今天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还不来啊?我今天已经投入进去了,为什么还不回报啊?我今天已经讲了这句话,为什么他对我还没有好感啊?你等啊,你越是着急,你就越是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不能着急,要放掉它,有时候你一着急,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师父跟你们举个例子,大热天的时候,晚上停电了,你躺在床 上汗流浃背。这个时候,你已经很难过了,你受够了,热得不得了,可是没有办法,不想想也会想,所以无所谓了,最后你就自然而然地清净了,清净之后,你反倒觉得凉快了。这就是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的,一个人越是急躁,越是做不成事情。一个人掉到水里了,不会游泳,双手双脚乱踢乱 蹬,身 体会沉得很快,等到他快沉下去了,感觉要死了,反而无所谓了,双手双脚没力气动了,他的身 体反倒慢慢地浮起来了。做任何事情都不要着急,着急的话,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师父最后告诉你们,要懂得念《准 提神 咒》。《准 提神 咒》 为什么有的人念了灵验, 有的人念了不灵验呢?很简单,念《准 提神 咒》要念到无念的地步,就是嘴巴里念,心里在念,念到后来我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念经,就是无念,你就成功了。无念,就是没有念头,没有说“我在求某一件事情,我要成功”,你就成功了,这就是无念。所谓的无念,并不是心里一个念头也没有,而是有念头,但是念头没有住在心中。想想看,你在念《准提神咒》的时候,你肯定是有目的的啊,但是念了之后,就不要再去想了,你就一直坚持念,你的功 力就增强了。你不能念一遍,想想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念一遍,想想自己的痛苦快点解决,这样你就住念了。师父跟你们讲,要念到“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没有什么事情住扎在心中,我哪生得“其心”啊,那才是真正的心啊。
可以去参考傅佩荣教授的《哲学与人生》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是对人生经验的全面反省。哲学与人生的关系是:离开人生,哲学是空洞的,它没有内容。离开了哲学,人生就会盲目,从而找不到方向。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弟子问师傅:“世界上真的有佛祖吗?” 师傅说“有的。” 弟子问:“可是我为什么看不见呢?” 于是师傅带着弟子到了一个漆黑的密室,师傅对弟子说:“你看那边墙角里有一把斧子,你看见吗?” 弟子张大了眼睛,可是密室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于是说:“没有啊。” 师傅点亮了蜡烛,在密室的墙角确确实实放着一把斧子。 你看不见的就一定没有吗?她讲完故事后说道:“同学们,我不想灌输任何东西给你们,请记住,在任何事情没有被证明之前,请千万不要相信;在任何事情没有被证伪之前,也请不要不相信。一切的一切最终都需要你自己找到那根蜡烛,点燃自己的智慧之光。否则你的人生就永远重复着自己的昨天,抑或是重复着别人的昨天。 是啊,我在听了那些话之后真的很激动,我忽然发现,我一直是这个社会的奴隶,听着别人的话,唱着别人的歌,咀嚼着别人的思想,咽下别人的唾沫。面对社会上那么多不公平的现象,我的心灵被污浊,我痛苦的反省自己的罪恶,却无能无力。 在后来这位出色的哲学老师的带领下,我进入了奇妙的哲学世界,其实说起来真正开始看哲学书,还是因为刘墉的一篇文章,那时的我处在成长的躁动期,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往极端想,于是有很多“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写那么多作业有没有意义,背那么多公式有没有意义,每天都要吃饭有没有意义,人反正是要死的,活着又有什么意义,这个世界存在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消沉的时候,忽然看到刘墉说,“其实你问那么多有无意义的问题前,早已经有了答案了,其实你只是在用那些问题不断打击自己而已。”我震惊了,不错,我就是这样,我只是因为无能无力,因为觉得没有意义,觉得没有信心,觉得没有能力,觉得没办法证明自己,所以在为自己找借口而已,只是在用这些“有没有意义”的问题慰藉自己而已。但是在这个社会面前,我没有勇气承认,因为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我必须保护自己,必须寻找自己的面具。但是,我痛恨自己,痛恨自己的虚伪,痛恨自己的罪恶,痛恨自己的无知。 那些陌生的名字在那些空虚的夜里一遍一遍地游荡在眼前,从叔本华到尼采,从加缪到萨特,从胡塞儿到海德格尔,从弗洛伊德到拉康。我的注意力却无意识地集中到了形而上之的悲观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上。 记得第一个让我感动的是休谟,当时翻开书本看到的就是他的学说,他认为人只能停留在知觉的王国,知觉以外的实体是否存在,无法知道。他说:“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因为任何一种个别的动作或活动重复了多次之后,便会产生一种倾向,使我们并不凭借任何推理或理解过程,就重新进行同样的动作或活动。我们经常说,这种倾向就是习惯的结果”。我于是怀疑自己的认知,怀疑我的思想,怀疑一切可以怀疑的存在,我会这样思考完全是因为后天的习惯势力,怎么办,我已经不是纯粹的“我”了,我属于“我们”,我只是那么多我们中的渺小的一个而已。我又一次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是一个人,我真的是一个人吗?我渴望我活着只是为了我是一个人,而不是别的什么。在这五光十色的尘世,我很难保持自己,很难保持自己不受外界的诱惑,而我只要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即使是最高尚的诱惑,我也会立即成为“我们”之中的一个。我已经不属于自己。 当我发现这点时,我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被社会骗了,被这个假装文明的社会骗了,我的周围的虚伪的人只是在用他们的假慈悲在灌输他们的自以为仁义、道德的观念给我。于是我想改变点什么,虽然我也知道结果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是总该做些什么。 当然我不是那种偏激的人,因为我还做不到那么绝对,毕竟我承认了自己的社会性。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但我至少还可以拒绝,对,我可以拒绝我所不认同的东西,当我刚想雀跃时,忽然有一个声音沉重的打击了我,那是柏格森。我没有看过他的什么书,他写过什么《形而上学导言》,在《评述》里记了他关于认识论的理论,从近代以来,西方认识论一直高扬理性或理智,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所相信的东西都是理性。实体或实在性只能为理性所把握,形而上学是理性的产物。但是,柏格森反对西方哲学的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反对在哲学研究中应用理智,主张只有直觉才能达到形而上学,才能把握具有形而上学实在性的“生命冲动”和“绵延”。我对他的“生命冲动”、“绵延”不很理解,但我明确了一点:理性也是有缺陷的。既然如此,我又有什么理由去评判,别人的对与错呢?那么我的拒绝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似乎陷入了绝望的循环,也就是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叔本华。这个名字像中国人的悲观主义哲学家,让我很着迷。不管他说什么,或许我无法理解,但是我却有共鸣,我想每个人对于共鸣的东西总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而像某些干瘪的说教只有讨厌。叔本华是一个悲观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世界既然被意志所驱策,那么,这世界就注定是一个痛苦的世界。而人生活于这样的世界里,他的一生只能是对痛苦的一种体验。 人生之所以注定要痛苦,这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人是世界意志客体化的最高等级。所谓最高,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生命意志中分化出自身的对立面——理智。理智的出现本来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命意志,让人活得更好。但是,理智一出现,就发现人原来注定要死亡。死亡是威胁人类的最大灾祸;人生的最大恐惧来自对死亡的忧虑。那些达官巨贾们可以居则琼楼玉字,宴则通宵达旦,但毕竟也难免一死,在注定要到来的死亡面前,珠玉,珍宝、舞会、盛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叔本华比喻说,人生好像在吹肥皂泡,明知迟早要破,可还是在吹。不但吹,还要比谁吹得大,吹得五光十色、富丽堂皇。为此,就免不了要挖空心思、费尽心力,然而心下却明白地知道这个肥皂泡迟早要破。人生如斯,岂不痛苦。(叔本华:《作为意志初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33页) 我很兴奋,叔本华说的,虽然我不完全认同,但是他的每一个字都敲打我的心灵,因为他不同我以前看到的任何学者的观点,他没有告诉我,要如何如何努力,如何如何为了XXX做贡献,要如何如何提高自己低级的觉悟。《作为意志初表象的世界》的序言里说,西方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社会文明,都是以理性的追求和信仰为基石的。叔本华是现代第一个指出这基石不可靠的人,更进一步的是“尼采”。 很早以前就听说过尼采这个狂人,不是因为他最后精神发狂,也不是因为法西斯对他的学说的暧昧,只是一种出自内心的崇拜,因为他比我认可的叔本华还要更进一步,乘着那时的热情,看了《悲剧的诞生》、《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基本上是一目十行地过去的,因为那些翻译很拗口,有一次问老师,那些是什么意思时?她说你不用去理会那是什么,你只需要体会那应该是什么就可以了,语言是会背叛你的心的。曾经看到某本杂志上说,人类能够证明自己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语言,可是现在它却要背叛我的心? 虽然由于语言的缺陷,或者说自己思想的简陋,虽然没法完全理解,但是有些东西却还是在脑海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一个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描绘的西勒诺斯神对弥达斯王的启示,当弥达斯王费尽周折找到他人西勒诺所,问他什么是对人生最好的东西时,西勒诺所最后笑道,你们这些朝生暮死苦难无边的人啊,为什么一定要逼—我说出你们不愿听的话呢?对人来说,最好的是根本不要出生。既已出生,那第二好的是尽快死去。 还有就是那句有名的“上帝死了”,尼采也许没有想到,他因为这句话开辟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的世纪。上帝死了,它意味着人的终极彼岸消失了。我们知道,只要有上帝存在,人是不会真正死亡的。人死了之后,还要上天堂或是下地狱,还要等待末日审判,这样的死亡,能是真正的死亡吗?如果人生中存在着虚假的死亡观念,便不能真实地面对死亡,因而也不能真实地面对人生。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人生的一切都有意义,就连人的死亡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上帝不存在了,那么先前用上帝的眼光所赋予人生的一切意义和价值都将烟消云散。 上帝死了,于是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必然发生,一切都是偶然的,没有“末日”。我们所面对着的便是一个充满偶然而荒谬的世界。所深切感受的只是自己感性真实的此刻生存,和自己必然走向死亡。宗教的衰落,己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宗教曾是世界的主宰,人的精神支柱,但现在变了。尼采杀死了上帝!宗教不再是人类生活独一无二的中心和统治者,教会已不再是人们生存的最后的收容所。人们关于信仰、意义和价值的观念,再也不是以神为尺度,而必须直接面对残酷的现实,于是便产生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正如萨特所说,上帝死了,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世界是荒谬的,加谬的小说《局外人》再次引起了我的兴趣。存在主义世界中那个经典的西西弗斯快乐使我看到了希望。荒谬的是对象世界,真实的是个人的此刻存在,因此,选择便仅仅只是个人的此在挣扎。它源于个人的生命准则,而非外在的规范要求。人必须得活下去,这便是唯一真实的生命前提,这便是西西弗斯式的存在——西西弗斯被神判处了终身劳役,他推着巨石上山,刚推倒山顶,巨石又滚落下来,于是他又重新开始向上推,这是一种虽徒劳无益却必须不停歇的劳动,虽悲观却仍愤激,虽无所希望却仍奋力前行的人生挣扎。人在这种挣扎体验到生命存在的意义! 活着确实艰苦,我们被抛到这个陌生的世界,等待着的就是一步一个踉跄,跌到死亡的尽头。回头望望,迷迷蒙蒙,朝前看看,又是茫茫然然。但是,既然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为何不让这场悲剧威武雄壮、轰轰烈烈地演下去呢?如果人生原本没有价值,我们不正可以利用它去创造价值吗! 我真的很庆幸,我还活着,不为什么,也没有什么是否有意义?只是活着,我接受西西弗斯的存在;我接受命运给我的宿命安排;我接受不可摆脱的运数。我推着巨石上山,我在一种宿命的力量驱使下活着,但我要活得深刻尊严,活得有声有色,活得辉煌壮丽。 哲学书仍然放在书架上,看完了加谬,我没有去看萨特,也没有理会海德格尔,只是后来关心了一下弗洛伊德,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为了“有没有意义”而思考的少年了。 高中毕业时,那位哲学老师在我的留言本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人注定是要毁灭的。也许如此;然而,就让我们在抗拒行动中毁灭吧,再说,如果等候在我们前面的是“空无”,那么我们不应当在意它,否则它将成为不可改变的运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