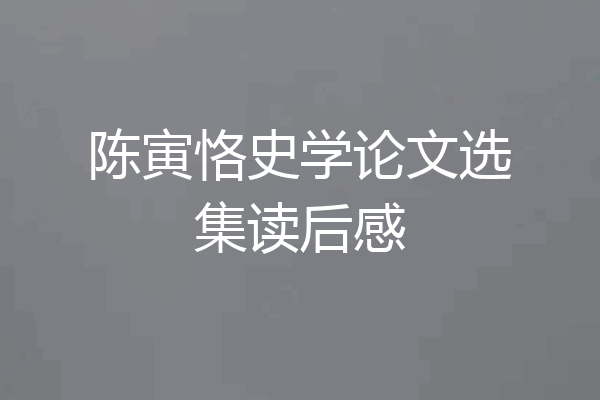wennieliao
wennieliao
且不论古代,就算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今天,互联网链接了全世界,可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仍然很难买到东西,集市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交易平台而非文化现象,不然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拼多多到美国敲钟在国内可以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呢?这部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黄仁宇先生从非常宏大的视角出发,从阶层的角度切入中国史,让吾辈可以明晰王朝更迭喋喋不休背后的阶层逻辑。除此之外,这套书还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汉人越穷越能打,越富有战斗力越低?想当年,汉武大帝逐匈奴于漠北,到魏晋被五胡占去半壁山河,再到宋朝被辽金元不断摁在地上摩擦,直到最后异族可以入主中原。黄先生的解释也非常有意思,因为你没变,你的对手不断更新,打不过,正常。匈奴,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对付他们,只需要“秋防”即可,因为春夏两季,塞外草原一望无际,人家有吃有喝为什么来打你?等到草黄叶落,没吃的了,方才入寇,一年防两季最多了。而且匈奴的政权核心在王庭,是随着部落迁徙而变的,只要被汉军抓住一次,损失就大了去了。等到魏晋,大量游牧民族编入军阀队伍中,已经略有汉化,知道建立政权了,通过设立政权管理游牧民族甚至农耕民族。这一部分我等到分享《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再说。这个时候,汉族需要面对的是已经些许农耕化的游牧民族。更可怕的是,到了宋代,你的对手已经完全实现建国设行政机构了,除了生活习惯已经和农耕文明没什么差异了。此时的战争,不再是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战争,而是国与国的战争。所以,不要认为汉人的武力越来越不行,而是对手进步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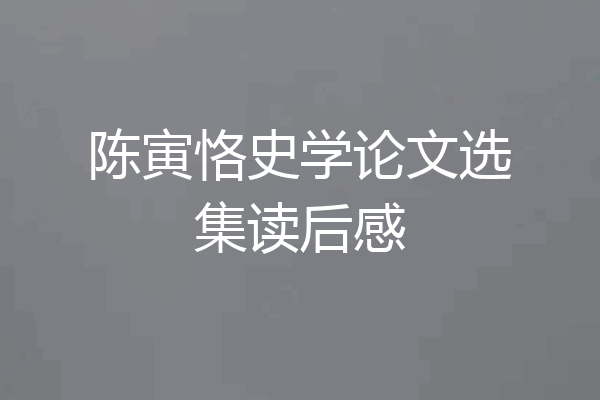
陈寅恪,不重名利,尊敬大才之人,知错能改,博学多才等
推荐一本书——《陈寅恪与傅斯年》读书的目的或意义有很多种。有的是为了陶冶性情,有 的是附庸风雅,有的是满足个人爱好,有的是工作需要…… 在时代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资讯蜂拥而 至、纷至沓来,与二三十年前相比,读书却似乎变成了一种 负担、一种任务。这个时候,稍微喜好读书并长期孜孜不倦 进行积累的人就显得“腹有诗书气自华”了。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读书往往就具有一种十分功利的色彩了。处于个人 喜好,一段时间以来艰难地读了《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 如果一定要从中读出诸如如何做好教育管理之类的味道来, 那这本书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但抛开功利目的,这本书不失 为认识那段历史、了解大师间的往事、 增强个人文化底蕴、 加强个人修养的一本可读著作。 一、偏于凤凰一隅地摊之上,为此书蒙上一层秀丽的文 偏于凤凰一隅地摊之上,为此书蒙上一层秀丽的文 化外衣 感谢机关给了一次外出考察学习的机会,在湘西古城的 地摊上看到了这本书,因为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此地父 母官,政绩显赫,受“闲时争名人,忙来毁故里”的经济利益 驱使,陈家三代亦没有幸免,成了为当地百姓谋福祉的重要 手段。在故里看了陈氏一门名人的介绍,联系在报纸上曾经 看到过的不多的关于傅斯年的难免带有政治色彩的报到,再 加上书内引用史料教委翔实,对于喜欢读史或者有志于培养 史学兴趣的人来说,应该是本值得一读的书。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