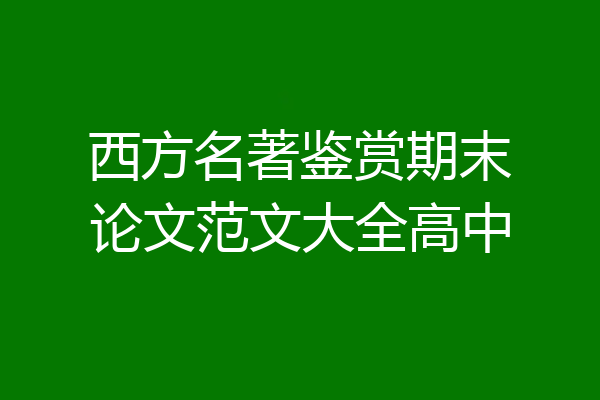yi十一
yi十一
《老人与海》赏析:主题老人每取得一点胜利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遭到无可挽救的失败。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他又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不屈服于命运,无论在怎么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他都凭着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进行了奋勇的抗争。大马林鱼虽然没有保住,但他却捍卫了“人的灵魂的尊严”,显示了“一个人的能耐可以到达什么程度”,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一个失败的英雄。这样一个“硬汉子”形象,正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小说人物。海明威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子”形象。他们多是拳击家、斗牛士、渔夫、猎人、战士等下层人物,生活贫困,屡受挫折,但他们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力,始终保持人的尊严和勇气。在他们身上,具有一种不屈不挠、坚定顽强,面对暴力和死亡而无所畏惧,身处逆境而不气馁的坚强性格。正如肖恩#奥弗莱因所说:海明威小说的主题是“人的本质,人的努力和奋斗,人的追求和痛苦,人的信仰和挣扎,人的倔犟和价值,人的聪明和命运,人的胆略和气魄,人的尊严和灵魂,”即使失败了,也要坦坦荡荡,不失重压下人的“优雅风度”。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自然或是社会中,人应该正视现实,接受一切并超越它,继续自己的人生之旅。纵然面对死亡,也要漠然处之,宁折勿弯,这是桑提亚哥所执著的人生要义,也是《老人与海》的哲理闪光。海明威塑造的一系列“硬汉”形象的理论与思想基础是行动哲学。它主要以主体的行动为表达方式,用主体的行为和动作展示其丰富的内涵。他所揭示的是肉体和精神的永恒生命力来自于不断运动的驱动力,强调的是在深沉的行动中锻造有价值的灵魂,他们用行动来显示自己的勇敢、冷静、果断、顽强和不畏任何强大力量的主体意识。他们所遵循的真理是“命运总是与人作对,人不管如何努力拼搏,终不免失败。尽管如此,人还是要苦苦奋斗,并尽量保持自己的尊严,他在肉体上可以被打垮,但在精神上永远是个强者。”《老人与海》中的老人桑提亚哥在海上经过三天精疲力竭的搏斗,最终拖到海岸上的是一副巨大的鱼骨架子,事实上,老人是一无所获的胜利者。而且今后人们也无法相信这位身衰力竭的老人,能够战胜奔腾不息的大海。在海明威看来,人生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就像老人那张“用好多面粉袋子补过的旧帆,看上去就像一面永远失败的旗帜”。但老人却始终没有停下行动的脚步,是一种面对巨大悲哀的追求,是一种面对死亡和失败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同样是顽强的、执著的。由此我们在桑提亚哥身上看到了诗人的尊严和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审美效应: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的生命的有限和人的追求的无限之间的矛盾。在人生的道路上,谁不经受一些挫折和失败?此时是缴械投降呢?还是顽强拼搏呢?桑提亚哥给我们的启示是:积极的进取和行动,是必然失败面前的不屈不挠的行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行动本身。所以,海明威为他所钟爱的硬汉们找到了灵魂,这灵魂就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与命运作殊死抗争的悲壮与崇高。在桑提亚哥身上表现的是一种深沉而强烈的悲而壮的生命悲剧意识,这完全是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现代回响。尽管海明威笔下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的,但他们身上却有着尼采“超人”的品质,泰然自若地接受失败,沉着勇敢地面对死亡,这些“硬汉子”体现了海明威的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即人类不向命运低头,永不服输的斗士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人生态度。海明威用象征性的寓言向我们昭示了跨越时空的人类永恒的自我求证意识。手法语言在海明威的写作技巧上,他用对话的简洁、明快、有力,修辞的干净,韵调的自然,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海明威使用的语言和刻划的形象鲜明具体,但是他的主题却含蓄隐晦,往往只用警句式的语言就能表现小说中人物的言谈行动。他的笔调潇洒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处,也没有着意的渲染和概括,但却能尖锐地刻画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体现了自然主义的白描手法。《老人与海》没有精雕细琢,也没有微妙深奥,然而只不过是简洁质朴、文字平定而已,开拓了小说的描写空间,丰富了小说的文学意蕴,使人产生一种“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的感受。瑞典文学院院士霍尔斯陶穆称赞海明威:“《老人与海》是一部异常有力、无比简洁的作品,具有一种无可抗拒的美。”[4] 纵式结构他采取了纵式结构的方式,即在众多渔夫中老人作为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桑地亚哥,选择了非常可爱的孩子马诺林做老人的伙伴,选一系列情节的发展按自然的时空顺序安排在两天时间内进行,这样剪裁实际上有许多东西并没有被真正剪裁掉,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完成,达到“一石多鸟”的艺术效果,寓意深厚。一方面集中体现了他作品的主题:“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能把它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他笔下“硬汉子”形象所反映的“重压下的优雅风度”。轮辐式的布局小说的全部时间非常紧凑,前后只有四天:出海的前一天,以老人从海上归来为引子,让周围的人物一个个出场,交代了他们与老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热爱他,跟他在一起学习钓鱼的孩子马诺林;一群尊敬他,但永远不能理解他的打渔人;一个关心他的酒店老板。老人就生活在这样的人物群体中,相比之下,他与众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他很乐观,心胸开阔,是个经验丰富、充满信心、勤劳勇敢、富于冒险、热爱生活的纯朴的古巴渔民。同时,这种轮辐式结构还能产生线索清晰明了、中心集中突出、故事简洁明快的效果。缓急相间的节奏感海明威在论述节奏时曾这样说:“书启动时比较慢,可是逐渐加快节奏,快得让人受不了,我总是让情绪高涨到让读者难以忍受,然后稳定下来,免得还要给他们准备氧气棚”这篇小说给人的节奏感就是这样,故事开始给我们交代老人与周围人的关系时,娓娓道来,速度比较缓慢,随着老人航海的进程,速度也逐渐加快着,当老人与马林鱼、鲨鱼正面交锋时,速度之快达到了极点。特别是鱼在不断的挣扎,起伏波动,鲨鱼在猛烈的进攻,老人很疲惫的情况下。象征西方文学中海的意蕴是丰富多彩的,抑或是清纯可亲的少女,抑或是凶神恶煞的恶魔。在《老人与海》中,海是被当作女性来描写的。在老人打鱼过程中,大海始终宁静、缓缓流动着;即使在鲨鱼夺取老人的鱼肉时,大海依然那么平静。她始终安静、自信、平等地凝视着“硬汉”般的老人——圣地亚哥。把大海描写成女性,外表温柔的她,却有着无穷、强大的力量,她有着闻所未闻的大马林鱼,有着凶残贪婪的大鲨鱼,她是如此得深不可测,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也真正显示了具有柔弱外表却内心坚强的才是“真正的”,显示了外在柔弱谦卑内心却拥有非凡毅力和奋斗精神的才是“真正的硬汉”。小说的主人公圣地亚哥是一位“真正的硬汉”,是“生命英雄”的象征。在面对种种困难的时候,勇于向人类生命的极限挑战。他具有顽强的毅力,在出海84天后一无所获,仍旧在第85天仍旧出海,经历漫长的等待终于在第85天看到了希望——遇到了一条大马林鱼;他具有坚强的斗志,与大马林鱼三天三夜顽强的搏斗,与鲨鱼勇敢的斗争;他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他在逆境中敢于克服种种困难。老人的这些精神是永恒的,即使他死去,他的精神会永远存在,沉睡的身体,依旧挡不住顽强的精神与是世界的对峙。《老人与海》通过对圣地亚哥这个人物的描写,赞扬了具有顽强意志力,不屈服于失败的人类。大马林鱼在这部小说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白劲鹏所言:“去掉那条大马林鱼,《老人与海》就不成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了。”老人在等待了84天漫长的时间之后,大马林鱼出现了,给了老人长久的等待一个回报,满足了老人的愿望。大马林鱼年轻力盛,但是老人坚强的意志力终于战胜了大马林鱼。在老人内心,大马林鱼是理想事物的象征,是美好的理想和追求的目标。这象征着,人类在漫长的征途中不知经历多少苦难,却仍旧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正是凭借这种信念和理想,指引着人类走过漫长的岁月,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和美好的生活。[5] 鲨鱼代表着一切破坏性的力量,是阻止人们实现理想和目标的各种破坏力的集合,是各种邪恶势力的象征。海明威只用了八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具有很高审美价值和意义的小说。而这部小说正是写于上世纪50年代,那时,古巴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运动已经逐步进入高潮。在海明威的笔下,主人翁圣地亚哥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渔夫,而是一个生活在苦难中的古巴低层社会的人们的代表之一,而鲨鱼是那些殖民主义者和贫困现实生活的象征,为了改变现状,人们不得不与邪恶势力作斗争,而这一切都充分展现了古巴人民顽强的意志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生动地展示了人类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的伟大精神,凸显了人类是“真正硬汉”的个性特征。狮子意象在《老人与海》中具有独特地位,它分占五处,尽管着墨不多,作者也未对其作更多的渲染,但作用不容小视:它犹如镶嵌在一串链子上的五颗珍珠,把老人心理流变过程串连起来;它勾连上下文,使小说的结构更加严谨;它与情节紧密相连,和其它意象一样,烘托老人的心灵世界,这对塑造一位鲜明、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小说是在“老人正梦见狮子”中结束,足见狮子这一意象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与其它意象相比,狮子没有大海的温柔和激情,没有鲨鱼的贪婪和凶猛,也没有枪鱼的毅力和耐心,但狮子有自己独特的自信和威严,发自内心,不怒自威,令人敬畏,这一意象丰富了老人的精神世界。正像老人一次次出海为证明自己,迎接生命挑战一样,狮子这一意象也是为老人的再次出海作心理上、精神上的准备,此次梦狮与一梦狮子也就形成了有机的联系。老人反复地出海,证明其内心有一个结,“心理活动有一个规律就是:内容相似的结会相互结合,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结。这个解不开的情结就是老人的未了心愿。它处“在深层的潜意识中”,而“潜意识愿望向随后的一切心理倾向发挥压力,而这些心理倾向却得屈从这个压力,或者是对这个压力进行疏导,以引向更高的目标, 老人显然选择了后者,他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他相信经过自己持续不断的努力,能最终证明自己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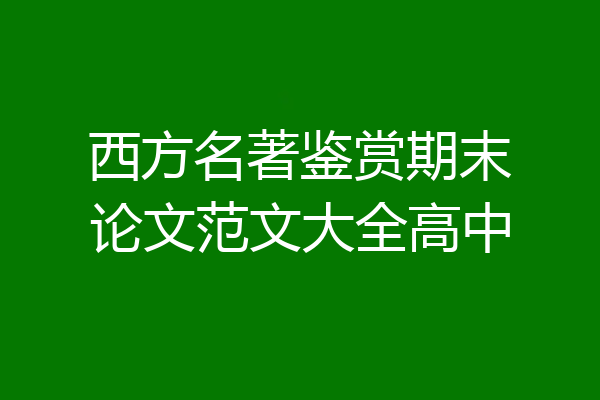
文艺复兴是个别人物的集合成就,因此就某方面来说,与个人主义有关。其中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人物是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但丁是佛罗伦萨人,而佛罗伦萨恰巧在文艺复兴中扮演比其他城市更重要的角色。但丁同时也体现了文艺复兴的中心矛盾:虽然它是有关希腊与拉丁古典文本的恢复和理解,以及优雅拉丁文的写作,但也有关本国语言,特别是意大利语的成熟、整理及使用。我们对但丁的早年生活所知不多,只知道他的双亲在他18岁以前过世。他在12岁时订婚,并在1293年他28岁时结婚。在典型的意大利社会风尚中,婚姻是一件鲜有感情意义的家庭事务。据说他的感情生活始于1274年,那时他9岁,初次瞥见他的比阿特丽斯(Beatrice,即比斯•波提纳利〔Bice Portinari〕,乃一甚有威望的佛罗伦萨公民之女)。他的诗人生涯便是致力于她的存在,在她1290年去世后,则是转为对她的追念;就某方面来说,他的一生和作品都是献给她的。 但丁的教育过程有三个关键要素。一是佛罗伦萨多明我会的诸位修士(Dominican),但丁和他们在13世纪90年代一起研究学习。虽然在那之前,多明我会伟大的导师兼作家托马斯•阿奎那已经去世,但他的作品齐备,因此但丁能够吸收完整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后者已被托马斯•阿奎那消化而基督教化〔1〕。托马斯式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为但丁所有的作品赋予一个架构,带来内在的一致与知性的严密。 但丁教育中的第二个要素是一位良师,即古典学者拉蒂尼(Brunetto Latini)。他也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他的主要作品《宝藏集》(Li Livres dou tr巗or)第二卷第一部分就包含一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译文。《宝藏集》以法文写成,因为当时意大利文尚未被视为可呈现严肃作品的合适语言;该篇译文是以欧洲方言翻译《伦理学》的首批作品之一。多亏了拉蒂尼,但丁得以了解修辞学的重要,即有力和优雅地辩论以及使用拉丁文或其他语言的能力。但丁也是透过拉蒂尼才能至少熟悉西塞罗(Cicero)和塞内加(Seneca)的部分作品。维吉尔特别是他的《埃涅阿斯纪》(Aeneid),是荷马(Homer)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的史诗继承者,即使在黑暗时代的烦扰时期也没有遭到遗弃,总是能找到信奉基督教的护卫者。但是其他的基督徒,包括一些最具分量的,如圣哲罗姆(SJerome)和圣奥古斯丁(SAugustine),都谴责维吉尔是典型的异教徒。拉蒂尼却教导但丁不光是欣赏,还可以利用维吉尔的作品。在但丁的《神曲》(Divine Comedy,它可被视为《埃涅阿斯纪》的基督精神继承者)中,维吉尔便以带领但丁通过地狱和炼狱的向导身份出现,尽管作为十足正统的基督教徒,但丁完全可以将这位拉丁诗人排除在天堂之外,改让他堕入第一层地狱〔2〕。 但丁教育中的第三个要素是他的亲密朋友和同辈卡瓦尔康提(Guido Cavalcanti)的影响与激励。卡瓦尔康提是古典学者,但也是热情提倡意大利语的人,正是他说服了但丁以托斯卡纳(Tuscan)或佛罗伦萨的意大利语来写作。因此很自然的,当但丁以意大利语写作《飨宴》(Convivio)和以拉丁文写作《论方言》(De vulgari eloquentia)时,便提出了文艺复兴对本国语言的第一次伟大辩护:他认为本国语言也是一种适合呈现壮丽作品的语言。《论方言》中有一句预言意大利语的话:“这将成为新的光明、新的太阳。当精疲力竭的太阳落下,它将上升,赐亮光给在阴影及黑暗中的人,因为旧的太阳没有照亮他们。”但丁敏锐地认知到大众无法精确掌握拉丁文,却可以通过教育来阅读自己所说的语言。其实,但丁的观点在完全以意大利语写作的《神曲》中就已显现,即一般的托斯卡纳语可用来写最精致的诗、处理最重要的事务。在但丁之前,托斯卡纳语只是众多的意大利方言之一,整个意大利半岛并无公认的意大利书写语言。而在但丁之后,书写的意大利语(以托斯卡纳语呈现)才得以确立。的确,21世纪的意大利人以及对意大利文有些了解的外国人,都可以轻松地阅读大部分的《神曲》。没有其他作家曾对一种现代语言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 但丁的《神曲》是一部有关善恶与赏罚的基督教史诗,描写他经历地狱、炼狱及天堂的旅程和途中的见闻。它有极多的人物角色,多是和但丁同时代的人。但丁在1294年被卷入佛罗伦萨的政治;佛罗伦萨本就是对政治极为敏感的城市,致力于圭尔夫派的支持教廷的行动。如同大部分的意大利城市一样,佛罗伦萨分裂成两个党派,但丁所属的党派因反对极端的必胜主义〔3〕教皇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而失势,但丁在1301年被流放,后来在1315年又被重新判决。这些意大利城市的派系斗争是邪恶且势不两立的。但丁的财产被充公,他也被判罪,若返回城内会被绑在桩上施以火刑。因此,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在流亡中度过,主要是在他离开人世的拉文纳。他以令人同情的诗句哀叹“吃他人面包,用他人梯子上床”的痛苦。 然而他伟大的《神曲》中几乎没有悲痛。但丁是一个特别宽宏大量的人,对全人类和个人都有包容的爱,他也明了上帝之爱的本质,这爱遍布宇宙并赋予它意义。他的诗是道德和训诲式的,在许多方面就像中世纪大教堂中的大祭坛画一样坦率直接。他以令人敬畏的严肃精神看待基督教信仰,并不会试图忽视地狱的惨况和炼狱的痛苦。从这点来看,他是中世纪的人,他对教会描述的伟大超凡的宇宙结构深信不疑。他也是极机智的说书人和天才诗人。他的故事进展极为流畅,充满了令人欢喜、十分震撼又惊悚的事件,且时常闪耀着鲜活的口述色彩和灵感。 此外,但丁不只是中世纪人,也是文艺复兴人。他大力批评教会,就如同许多跟随他的学者。虽然他身为圭尔夫派,却对日耳曼皇帝亨利七世留下深刻印象,这位君主曾在1310年攻入意大利,改变了但丁的政治思想,接受单一的普世君主政体。但丁在他的拉丁文论文《论君主政制》(De monarchia)中表现出此点,却在死后被斥为异端。但丁有伟大的信念,他了解中世纪基督徒的观点,即获得个人平安的唯一方法就是降服于上帝的旨意,无论它有时多难承受。但是但丁也有未来新时代的批评精神。他有一种洞察力,能看穿事物的核心。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受教育或未受教育的人,都能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一点东西,赞叹地阅读或倾听他的诗句。在他去世后,名声迅速散布,而后稳定成长。很快的,曾经放逐他的佛罗伦萨为了保管他那可敬而如今极有价值的骸骨,和拉文纳争斗起来。但丁不仅促使意大利语成为高等艺术的传达工具,就某方面来说,他也发动了文艺复兴:前所未有的天才发挥创意的一个新世纪。他成为一个模范、一座灯塔、一位导师,一如维吉尔之于他;对于较次等的人才来说,但丁也是能力和活力的来源,是最具雄心者能用来自我评判的高耸巨人。在但丁之后,似乎没有任何事物是人类不可及的。 这是另一个托斯卡纳人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观点。他出生于1313年(当时但丁仍然在世),他的商人父亲决定他必须一生从商。因此,他被送到那不勒斯,却在那里寻得了毕生之爱费亚梅塔(Fiammenta),她不断出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像比阿特丽斯之于但丁。薄伽丘是但丁的继承人:他有但丁操纵新成熟语言的能力,也有但丁出类拔萃的说故事能力。他的母亲是法国人,他将法国中世纪的传奇故事收入作品。他采用吟游诗人的八行诗(ottava rima),赋予文学形态,使它真正成为意大利文学中最有活力的诗歌。他的《十日谈》(Decameron)是1348年黑死病的产物,是仅次于《神曲》的文艺复兴欧洲的趣事来源。书中有七个青年女子和三个青年男子因躲避传染病而逃出佛罗伦萨。他们在乡间停留两周,其中十天都在说故事,总共编了一百多篇故事,每篇皆以民谣或诗歌结束。因此这本书其实是故事和诗的摘录,在接下来200多年内是没有创作才能的人搜取灵感的对象。教会和社会中的古板人士并不喜欢它,因为它呈现了更自由的生活方式和年轻一代的想法,与过去的拘谨陈腐形成对比。而其他人喜欢它却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如此说来,它是一本前卫的书,是渐长的文艺复兴趋势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