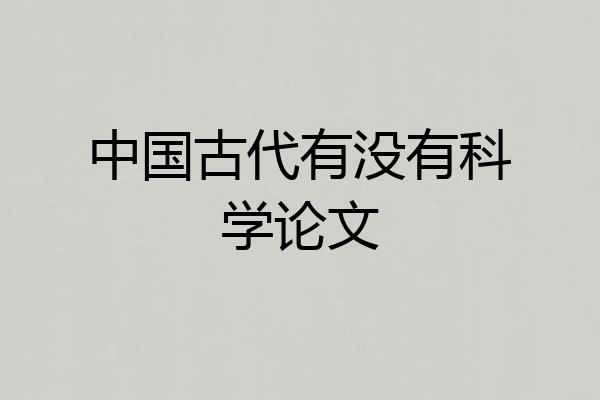nj_xiaomin
nj_xiaomin
《自然科学史所》主办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中就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持不同见解的诸位学者,都以自己对科学定义的理解作了否定或肯定的论证。争论的焦点多倾向于对“科学”定义上的分歧。除了有从广义(放宽标准)、狭义(严格界定)的不同见解认为“宽则有,严则无”的论证外更有以某权威对科学名词的注释为依据作肯定或否定标准解释的
我认为上述论点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若以宽严为标准,如果不存在西方文化的偏见,单就中国古代文库中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成就而言,至今仍有许多现代人所望尘莫及的知识,其复杂、深刻和精确的程度,许多西方有识之士都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东方文化在二十一世纪对实现全球一体化,为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将发挥积极的影响。仅以人体科学中,古代中国所发现的“经络学说”为例,现已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现实就足以证明,如果对科学定义不存偏见,再严也不能说中国古代无科学。反之,如果以《黄帝内经》的标准下科学定义,又可以说:因为西方的科学缺乏整体(天人合一)的思想,至今用这种办法(现代科技)对经络为何物还说不清,西方不懂“形而上”的“道”,只懂“形而下”的“器”,故西方没科学。
商鞅说:“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如果不肯认真地研究东方文化,仅仅拘于受西方文化影响由权威为科学所下的定义(本本和教条)以偏盖全作为是与非的标准,年龄再大,知识再多,实际上仍在受惑。知识(教条、本本)如果成为约束和禁箍人们进行独立思想的障碍,那就是溺于所闻。法与礼存在愚者制、不肖者拘焉的现象尚且情有可原,思维还是以解放为好。如果要不被存有偏见的教条所制约,就必须对你所有的知识有批判能力,善于从相互矛盾的论述中找到中和点,克服滞而不通的部份,大家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史所》研究的是中国科学史,如果中国无科学又何来科学史?既然没有异议,为什么对《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则可以提出“无”的论证呢?
科学与迷信尽管名词不同,在学术实践中从哲学角度看又是相互渗透,相反相成的互根关系。宗教哲学中有许多非常精辟的科学知识,绝不能简单地用一句“迷信”或“精神鸦片”就可以否定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在没有找到终极真理之前,都有特定时空的局限性,离开它适应的条件,盲目地坚持就是迷信,两者都有个适度的问题
,能正确对待也并非易事。
科学与迷信两者共寓于—个统一体中,“辩证法”称“对立(矛盾)统一”,“阴阳学”称“阴阳互根”,其共性是:两者都是存在(客体)与意识(主体)相互作用的一种效应。像导体中的电流,任意点都不是只有正极而没有负极或者相反。这是因为,人的认识能力不仅有先天的差异,后天所受教育的程度和内容更是千差万别,不同人对社会和自然的感受(机遇)和观察(角度和深度)也不同。不同的处境和社会地位又将伴生相应的利与弊,因立场不同又有各种不同的感情倾向,故在使用科学或迷信对同一现象进行评判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是会经常发生的。
任何权威学者,如果不能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及时完善和纠正自己的不足或失误就是迷信,所谓一世英明毁于一旦。至于个别人对自己不理解的事情随便下结论,甚至以“科学卫士”自居,任意对别人扣帽子、打棍子,自以为是在捍卫科学和真理,不承认自己知识的有限性,其效果既是反对党的双百方针,又是在搞“迷信的科学”或“科学的迷信”。
仅以近年来争论较多的“人体特异功能现象”为例:不能否认,确有一些人借此胡吹骗人骗钱,但骗术又何只就此一种?五花八门骗人的手段多得很。终不能因此就认为人人都是骗子吧?你发现了一种骗人的手段,对别人不调查研究就下结论,甚至以势压人,对谁都不相信,包括钱学森一类的著名科学家,那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你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了。我相信钱老在相信和承认确有特异功能绝不会是不经过调查研究就盲目相信的,更不会因为相信有特异功能就对胡吹自己有特异功能的人都相信。要论证确有特异功能并不难,仅就中国古人在两千年前就能发现“经络”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巨系统,并经两千多年临床实践证实,
古人的发现不仅借助现代科技都不可能,现代科技尚不知为何物。又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经络学说在临床实践中,一再证明确有“行气血,营阴阳,决生死,处百病”的功效。难道这是正常人能做到的吗?这也是魔术和伪科学吗?你的摆台奖还算数吗?如果继续以“科学卫士”自居,继续以势压人,难道不应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吗?错误总是难免的,在学术上不准犯错误就等于扼杀学术研究或文字狱,但如果明知是错误还硬着头皮坚持,最终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坚持错误没有不失败的,有多少人坚持就有多少人失败,态度越顽固失败的越惨,这就是真理的权威。
科学与迷信的辩证关系只能是“科学为科学中的迷信,迷信为迷信中的科学;科学中有迷信,迷信中有科学;以迷信压迷信见真迷信,以科学压科学见真科学。”在终极真理尚未被彻底揭示之前,任何科学成就因为只在特定的时空领域有效,如果以有局限性的科学知识,对无限时空的现象进行裁判,科学就变成了迷信,反之如果你能对一切未知的领域,都认真地进行探索,既不盲目肯定也不盲目否定,也就是迷信中的科学。真迷信与真科学只能在同类中比较,在比较中才能鉴别真假的程度。上述关于科学与迷信辩证关系的表述,是从古典阴阳哲理中,发现了阴阳排列组合的总公式(法则):“明为阴中阳,阳为阳中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以阳压阳见真阳,以阴压阴见真阴。”的总法则中推导出来的。近三十年来本人运用这个总公式联系一切对立现象,验证了该公式的正确性尚未发现失误。提出这个公式更希望能够听到有人提出该公式的否定论据。
为了更好地发掘我国丰富的古代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古为今用,澄清某些盲目崇洋媚外贬低祖国文化的偏见,我认为举办上述学术争鸣是有价值完全必要及时的。对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健康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由于近现代历史上所形成的偏见,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局部的辩论就能达到共识。为了求同存异,如果把重点放在研讨古代哪些知识急待发掘整理,以便更好地做到古为今用,为此多组织一些专题讨论会,我想会更有益。
真理只能在争鸣中集思广益,日臻完善。也只能在争鸣中涌现并显示自己的生命力,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任何借助权力维护的“理”终将被淘汰,只能作为肥料或垃圾存在于史学中。《资治通鉴》中的一段话说:“正直中和谓之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认为上述论点。值得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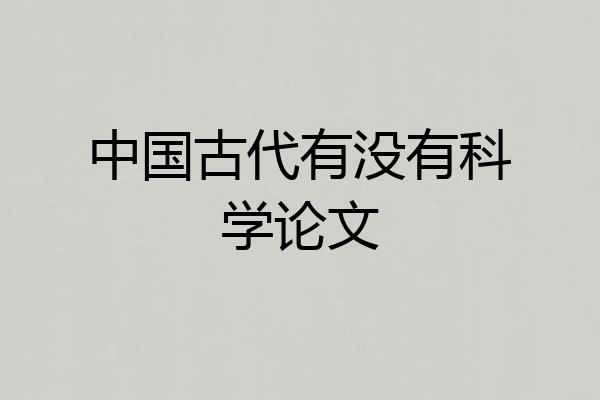
科学,原指分科而学的意思,指将各种知识通过细化分类(如数学、物理、化学等等)研究,形成逐渐完整的知识体系。是关于发现发明创造实践的学问,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总称。你觉得可能没有么?
谈到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很多人脱口而出就是四大发明,熟不知其实在学术界,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都是一热点问题,更别说所谓四大发明是不是属于科学了。一.关于科学的争论对于科学一词的定义,不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学术界,都是一个议论纷纷的话题,在平常人的认知中,科学实际上是一种能够使人们达到某种目的一种存在。举个例子说,一个人想要达到某一个目的,比如想要一种便于书写的材料,然后造纸术为他达到了这种目的,于是这个人就将造纸术视作科学。又比如说另一个人,想要出行得更快,汽车为他达到了这种目的,于是他便把制造汽车所需要的一切知识认为是科学。这是非学术界,包括一部分的学术界对于"科学",在潜意识上,非常普遍的一种认知,如果以这种对于科学的认知来评判中国的四大发明,那么毫无疑问,四大发明属于科学。但是在学术界,有一部分研究科学史的专家学者不认同,清华教授吴国盛认为: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四大发明不属于科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权威的学者便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二吴国盛: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吴国盛教授陈列出了自己的观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来自于希腊的古典思想,和基督教的唯名论批判思潮。前者为科学奠定基础,一方面是制度基础,另外一方面是观念基础。其制度基础是大学,其观念基础是经院哲学。后者则更是为近代科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科学"是西方文化独自创造的人类伟大进步,其历程是西方文明的伟大历程,中国并不在此之中。事实上,古代中国没有西方文化所创造的科学诞生的基础——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唯名论思潮,自然也就根本没有科学。四大发明也不属于科学,因为没有这些伟大的思想作为基础。三四大发明不属于科学有些人可能会反驳吴国盛教授,既然中国古代没有科学,那么四大发明,还有中国古代创造出来那么多独特,先进的东西又是什么?其实,二者分歧的观点在于对科学的认知,对科学的定义。吴国盛教授说的此"科学"非彼"科学",二者的含义上不同,吴国盛教授说的科学是来自西方世界的"science",是一个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知识系统,是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用通俗一点的方法来解释的话,吴教授所说的科学是狭义上的科学。
中国古代有学术论文。这固然与史料的多少有关,也与各时段研究者的学术积累和兴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