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柚----
柚----
什么优势,都是人为的,劣势也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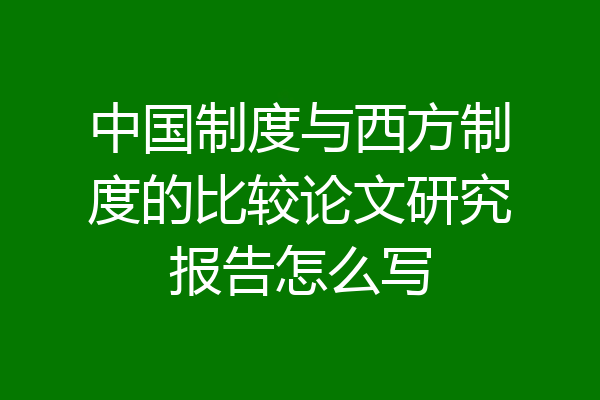
东西方的政治制度最本质的区别是工作方式,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往往通过十几天的会议议程,解决全中国一年里各项工作地实施与落实。而西方议会则是全年都在争论不休与平衡各方关系中度过,一年间只有十几天是给西方老百姓干实事的。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政治的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代表是通过选举与协商产生出来的,他们来自于人民,他们从事各种工作,包括了社会各方民众,代表了最广大社会群体,充分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 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不像西方是两党制或多党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同样来自于人民,他们是行业的标兵模范,他们也是社会的精英人士,他们更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崇高的社会责任告诉他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名中共党员的基本要求与历史任务。党员就是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人大会议现场的掌声,世人就能看到,掌声来自人民,掌声同样也是送给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给老百姓做事的政府,只要是人民群众主张的国事,中央都要尽责去办。同样掌声是真切的、鼓舞的,不会像某些西方人士理解的那样,假惺惺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我们理解西方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们的掌声,来自于他们的支持者,反对者是不会给他们掌声的,他们分的是派别,即使政府做出决议,也只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主张,他们是利益攸关的社会,社会分崩离析,各方势力角逐,争的是权力,争的是能给自己代表的团体谋到利益,并不是给国家和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与付出。 中国从没有主张过,让别的国家学习中国怎样为人民谋福祉的政治制度,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理解并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他们正在探索与学习,包括中国从社会中选拔干部而设的党校这一重要举措。 区别还很多,笔者由于才疏学浅,只能说出上面的一小部分,大的部分还不能做到深刻理会与表述。 东西方需要交流,但交流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尊重的原则基础之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才是世界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才能真正达到全世界人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同进步的新阶段。
中国古代政府制度的起源和形成的时间,与古希腊、古罗马政府制度的起源和形成的时间差不多,但为何古希腊、古罗马能够形成为民主政体的政府制度路径,而中国却形成为君主专制政体并延续了几千年?其中有什么关键性的客观变量和主观变量决定这两条不同的制度路径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西方的政府制度在经历了中世纪的君主政体之后,为何在近代能够回复到古代民主路径并发展为现代民主政府制度?而近代中国的制度转型为何如此艰难? 1、中西古代政府制度起源和形成为两条不同的路径,即单主制(专制主义)路径和共和制(民主主义)路径,前者具有任命制、终身制和集权制等特征,后者具有选举制、任期制和分权制等特征。本文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并认为:中西古代的两条政府制度路径并不是在国家正式形成时才分野的,而是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了雏形的特征,中国在原始社会的酋邦制度中已经出现了单主制的特征。 2、国家制度的第一个特征是按照地域来划分居民,由于自然环境、生产工具和生存空间的开放性不同,古希腊国家制度的地域性完全是切断血缘关系而冲破氏族的藩篱的结果,而古代中国国家制度的地域性则是血缘关系通过宗法制度得以延伸的结果。这样,虽然不论是古希腊还是古中国,作为政府制度的核心——政治权力,都冲破了地域的限制,但古代中国的权力结构是继续沿着宗族内部的路径而跨越地域空间的,而古希腊的权力结构则是在宗族外部的路径上跨越地域空间的,即先跨越宗族再跨越地域空间。正是这两条不同的跨越路径,决定了国家制度的第二个特征——“权力的公共性”在中西古代的差别:古希腊政府制度的“公共权力”逐步发展为公民权,而古代中国政府制度的“公共权力”本质上为血统性的“个人”行使。前者演变为“主权在民”的路径,后者则演变为“主权在君”的路径。 3、中国古代由于土地与血缘的不可分性,使土地分封制无法实行下去并推动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而西方古代土地与血缘的分离性促使契约关系的产生,并使土地分封制发展为土地私有制。本文认为,正是这种差别,使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沿着争夺的路径演变出“大国之君,不如小国之君”的局面,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兼并的方式来扩大势力,增强争夺土地的力量,最后重新走向大统一;而西方古代社会土地制度沿着契约的路径演变出“附庸的附庸不是国王的附庸”的“分藩而治”的政府制度局面。不过,中西古代政府制度的起源既有从原始社会延伸的一面,但也有体现社会改革方案选择的另一面。不同的社会改革方案,具有促使政府制度是满足统治需要或是满足社会需要路径发展的巨大作用。 4、对中西政府制度演变的主观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本文的重要内容。中西古人对政府制度的认知和思维路径,与他们各自所处的政府制度的客观路径是一致的。不同的认知和思维路径,反过来制约着中西政府制度路径的演变。(1)在政府起源和权力的认知方面,中国古人认为政府起源于立了“受命于天”的君主,“君权神授”要求“君权独制”,对君权的制约主要依靠君主的修养,辅之以必要的外在约束。而西方古人认为,政府起源于人们为了摆脱混乱的“自然状态”而通过“相互约定”建立的,约定的前提是人人具有参政能力和人人都享有权力,权力的“公共性”决定权力的制约必须以权力的相互制衡为主。(2)在政府制度主客体的角色地位的认知方面,中国古人认为君主是“天之子”,是至高无上的,官吏只是为服务君主的需要而设置的“事君之臣”,民众只是“君父”的子民,必须仰仗君父之爱而安乐。而西方古人认为,各级统治者只是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官吏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而产生的“公职人员”,民众是有权参与城邦事务的公民。(3)在政府制度设计的思维方面,中国古代的制度设计思维是把个体置于依附关系的网络中,并相信通过教育和引导,每个人都会在这个网络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并遵守网络中的关系规则,规则的核心是家庭关系规则的放大,一切冲突都可以在人伦“情理”中得到妥善的解决。在这个网络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大小决定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高低和财产的多寡。而在西方,制度的设计思维是把个体看成是独立的个体,个体在制度中的地位是由个体的能力和财产决定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契约以及法的形式来处理和约束,人间不存在总是善良的“天使”,哪怕是政府及其官员本身,所以任何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在约束人的行为的同时,也保护每个人的财产。财产权对每个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获得政治权力的前提是拥有个人财产。 5、任何制度转型过程都是通过改革或革命来实现的。这个过程充满着新旧的斗争,旧制度的主客观路径对制度转型的约束,表现为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思维约束、对进行制度改革的社会动员的约束以及对改革和革命的社会成本的约束。本文通过对中西近代制度转型的比较研究,揭示中西两种不同制度转型的特点。(1)西方近代制度转型以英法革命为标志,但西方人争取制度转型的斗争是从中世纪就开始的。古典时代的民主遗风和民主观念的影响贯穿于整个中世纪,但文艺复兴使古代政治文明得到更为全面的恢复。英法革命能够在西方确立君主立宪制制度与民主共和制制度,与中世纪市民阶级的一点一滴的斗争和文艺复兴运动是分不开的。西方近代的制度转型是相对中世纪的专制制度而言的,相对于西方政府制度的整个演变历史来说,这种制度转型是恢复和发展古代政府制度的起源路径。(2)中国近现代的制度转型与西方近代的制度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是对古代政府制度起源路径即单主制(专制主义)路径的打破,改革者、革命家试图建立的新制度,不仅在中国政府制度演变史上缺乏任何积淀和思想基础,而且,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路径对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创新理念、制度设计、革命方案等都具有强劲的约束力。中国制度转型的结果是创造性地移植民主制度,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是古代民主制度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就此而言,中国制度性超越的难度远高于西欧各国,也因此决定中国的制度性超越的任务远还没有完成,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 你可以任选其一方面,进行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