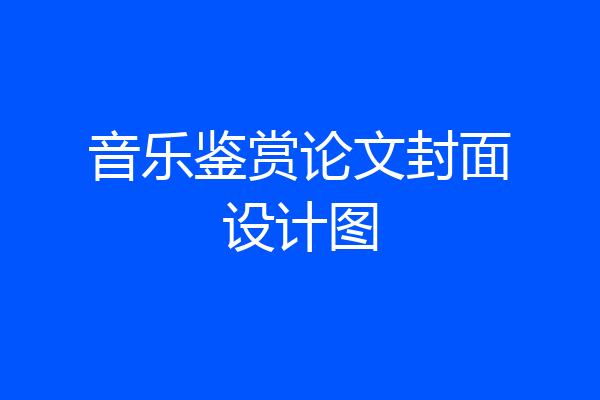CQY1887685
CQY1887685
这个音乐是有背景故事的。天亮了》和背后的故事 事发生在1999年10月3日10时20分左右,在贵州麻岭风景区,200多名游客在马岭河峡谷谷底唯一的缆车乘坐点,等待乘坐缆车去山顶吃中饭。11时10分,一阵难以想象的拥挤后,面积仅有五六平方米的缆车车厢,竟满载了35名乘客,又一次缓慢上升,10多分钟后到山顶平台停了下来。工作人员走过来打开了缆车的小门,准备让车厢里的人走出来。就在这一瞬间,缆车不可思议地慢慢往下滑去。缆车缓慢滑行了30米后,便箭一般地向山下坠去,一声巨响后重重地撞在110米下的水地地面上,断裂的缆绳在山间四处飞舞! 在缆车坠落的那一刹那间,车厢内来自南宁市的潘天麒、贺艳文夫妇,不约而同地使劲将年仅两岁半的儿子高高举起。结果,这个名叫潘子灏的孩子只是嘴唇受了点轻伤,而他的双亲却永远离开了人世! 这个生命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歌手韩红,她以这个令人震撼的事件并以小孩的口吻,《天亮了》这首感人至深的歌曲,并经过多方联系,领养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小孩。 每次听韩红的天亮了,心里总有一种酸痛,总能感受到一个孩子撕心裂肺的呐喊,人世间对我们付出最多的是我们的父母,他们无怨无悔的为我们付出,并不奢求我们的回报,父母的爱能给我们一种温暖,一种力量所以韩红创作了这首歌曲。 在生和死的瞬间,父母想到的并不是自己, 他们用双手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儿子,这就是父母之爱。 1999年10月3日的一场灾难 让当时只有2岁半的潘子灏变成了孤儿。 看过今年3·15晚会的人们可能都还记得 晚会最开始的那首歌———《天亮了》, 这是歌手韩红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 可是谁知道这动人的歌声背后, 还隐藏着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生命的故事 1999年10月3日,在贵州麻岭风景区, 正在运行的缆车突然坠毁,36名乘客中有14位不幸遇难。 而就在悲剧发生时,一对年轻的夫妇, 用双手托起了自己两岁半的儿子。 结果,儿子得救了,这一对父母却失去了生命。 这个生命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歌手韩红, 经过多方联系,她领养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小孩, 下面我们要讲述的就是 发生在韩红和这个小孩之间的故事。 韩红连续两次在3·15晚会上演唱了《天亮了》这首歌, 打动了亿万电视观众。而在创作这首歌之前, 打动韩红、激发她创作灵感的又是什么呢? 韩红动情地说: "我就觉得是他爸爸和妈妈。因为我从小没爸爸, 我5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然后母亲又不在身边, 所以父母的这种爱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但是有哪个孩子不愿意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呢? 我就觉得在缆车下滑即将坠地的那一瞬间, 子灏的爸爸潘天奇和他的妈妈贺燕雯 两个人把孩子举起来了, 我心里觉得这是一个用伟大两个字 都无法去恰当体现的一个壮举。 这个壮举也许是出于父亲、母亲的一种本能, 也许是出于他们对孩子的一种爱,也许很多, 总之我看到这的时候,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感受恐惧 如何将心中的震撼化为实实在在的作品, 是韩红面对的难题,为了完成歌曲的创作, 韩红只好去体验坐缆车的感受。 韩红告诉记者,春节期间, 她到成都青城山坐了一趟缆车, 自己亲身感受了那种上上下下、在在正常运转的缆车上, 韩红体验到了恐惧与无助, 而发生事故的贵州麻岭风景区, 缆车竟然是违章设计施工的, 甚至只能载客十多名的缆车挤进了36人, 当缆车几乎是垂直上升时,悲剧就更加难以避免了。 潘子灏的生还,是他父母的双手托起的一个奇迹。 当韩红见到当时只有2岁半的潘子灏时, 一段新的故事开始了。 韩红向记者讲述了她和子灏见面时的情景, 她说:"我一进门就看见了他,他就在一个角落里面。 我一叫他,他居然自己走过来抱着我, 于是我们俩在一起哭了好一阵, 就是让我自己尽情地去哭, 好像孩子跟我有很多话要说,然后我们两个人一直在哭, 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好像我对他也有很多话要说。 这个情景当时被家人拍录下来了, 但是今天我也不想给电视观众看, 因为我觉得那是属于我心里、 深藏在我心里最深最深的一种最真诚的东西。" 未婚女的母爱 尽管韩红愿意为潘子灏付出一个未婚女性所能给予的母爱, 但是,留在潘子灏幼小的心灵中的创伤并没有愈合。 韩红告诉记者,子灏他喜欢去当地的, 好像是一个百货大楼的游乐场去玩, 在小木船上,韩红发现每当她摇木船超过三下时, 然后小子灏就要下来,说那是缆车,他害怕。 可见这一件事情对一个幼小的心灵会有多么大的压力。 韩红说她一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特别恨那些对生命完全没有任何尊重可言的人。 再过几天,就是潘子灏的四岁生日, 得知小子灏扁桃体又发炎了, 韩红赶紧往广西南宁挂长途电话,在电话中, 韩红不停地问小子灏打针痛不痛, 小子灏告诉韩红自己虽然感觉痛,但却没有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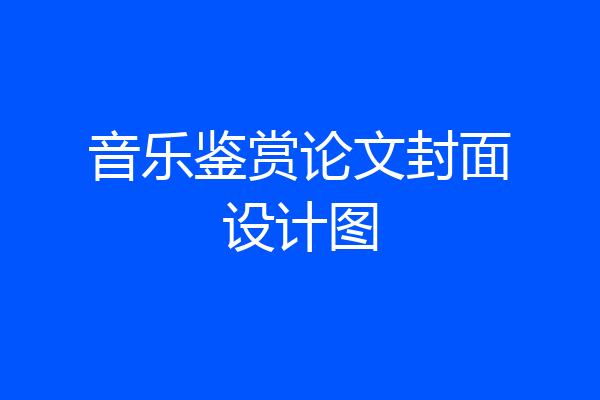
一直都觉得音乐这东西很深奥、很有内涵、很专业,像我这样的人是没办法理解的,我也很喜欢音乐,不过只是喜欢听听唱唱流行歌曲和摇滚歌曲,对于那种专业的音乐,还有肖邦、贝多芬什么的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感叹,我一直觉得自己听不懂所谓的音乐,也许有一定程度的心理意识,反正我就是一直都有这种想法,而且也从来没有去试过听那种音乐的感受。 这里简单提一下我对音乐的看法,可能我的理解比较肤浅。对于音乐所表现的世界,可以有诗意,画境,和内心的独白。例如肖邦的《肖邦生F大调夜曲》和交响组曲《天方夜谭》,《伏尔塔瓦湖》就分别表现了这一点。我最喜欢的还是能够表现对苦难人生的抗争,奏响时代的强音的贝多芬的《命运》了。因为他很振奋人心,听过之后感到激情澎湃,人生苦短,不能被眼前的困难打倒。 至于音乐还能表现什么,可能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音乐可以表达一切。音乐是独特的,任何语言或画面都不能将它完整的描述。音乐是直接的,多数时候欣赏经典的音乐只需放开心灵去直接感受,而不需要思考什么。音乐是抽象的,但我们欣赏的时候不必刻意追究它的什么细节,只需本能的去感受。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进音乐的门问自己就行了。有的时候自己真的体会到了,并不带有喜爱音乐以外的想法,问心无愧。也许就是音乐想要表达的世界,即使和作曲者的想法不一样。自己真的热爱那才是最关键的。我觉得跟着大流走,别人说什么自己就认为是什么这种想法并不可取。虽然大流很多都是对的,但热爱音乐并不需要大流的认同,因为音乐是人的杰作,也属于较为抽象的艺术,在理解和看法上不同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音乐没有这一特点那也就没有这样的魅力了。 熟悉贝多芬还是他的那句话。他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绝不能让它毁灭我!”我对这句话比他的《命运》要熟悉。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命运》这部作品创作于1805——1808年,与他完成《第三(英雄)交响曲》的时间相隔4年。在这4年中,他不但在创作活动中取得很大成就,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思想也逐渐成熟。当时正是贝多芬创作的黄金时期,也是他遭遇不幸的时期。于是,他与命运英勇搏斗,以惊人的毅力和意志,写出气魄恢弘,极为感人的《命运交响曲》。 在整个《命运交响曲》作品中,情绪激昂、气魄宏大,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作品结构严谨,手法简练,形象生动,各乐章之间具有十分清晰的内在联系。第一章节,开头就是那激昂的音乐澎湃而出,让人心灵为之一颤,就像那滚滚的历史巨轮的滚动,就像生命被死神扼住喉咙一般!就像那十二级的风暴袭来!就算我是听过几次的,但是每一听到,还是禁不住为之震动! 那“当当当当”的敲门声仿佛敲在我的心门。我的眼前好象出现了一个狰狞的死神,在肆无忌惮的狂笑,粗大的手掌缓缓地掐住了我的喉咙,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一点也没有反抗的能力。总体上,第一章节激昂有力,具有勇往直前的气势,表达了贝多芬充满愤慨和向封建势力挑战的坚强意志。接着,圆号吹出了由命运动机变化而来的号角音调,引出充满温柔、抒情、优美的第二主题。 而第二乐章,音乐有舒缓的地方。让人在振颤中舒缓下来。在那激昂的音乐中缓了一口气。仿佛是生命已到最后,人的气息只有那么一口似的。那是小提琴悲哀的鸣叫。我似乎放弃了与死神的对抗,无奈的接受了事实。人,最终还是对抗不了命运的安排。我甘心放弃挣扎,对命运的捉弄无可奈何。但是,它仍然抒发了贝多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却是命运动机再次闯入,威风凛凛的命运再次占了上风。转调的非常频繁增加了原有的不稳定性,使音乐显得更加丰富。但在这一乐章的庞大结尾处,音乐的气势不可阻挡,进一步显示出人民战胜黑暗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 到了第三,四乐章,生命的顽强体现出来。黑暗必将过去,曙光就在眼前,振奋人心的象征着人民群众在黑暗势力下的斗争信心和乐观情绪。我不能向命运低头!我不能屈服于命运!我要战斗,战胜命运!我要战斗,我不是命运的奴隶!我就是我!我能忍受挫折,我能抵抗疾病,我能站立,我能与你抗争。到了这里命运已被我战胜了!这时候命运的威吓声,已是苟延残喘,再也阻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潮流了。 于是,辉煌、明亮的音乐再次响起,以排山倒海的气势,表现出人民经过斗争终于获得胜利的无比的欢乐。这场与命运的决战,终于以光明的彻底胜利而告终!音乐的末梢,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好象自己真的刚参加完这场斗争一样。 这首交响曲让我体会到,面对困难,应该决不屈服,勇敢的挑战不幸的命运,最终战胜命运,取得成功! 我对贝多芬有看法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早在20多年前,我还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年,刚刚开始跟着几个学声乐的女同学后面恩恩叽叽附荣风雅时,就对贝多芬的什么命运什么英雄交响曲颇有看法;虽然我还不知道五线谱是什么东西,只是感觉象河里的蝌蚪,但我仍然保留对他的看法。 多少年过去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某些传媒社会道德的不断沦落,我那颗对名人特别是对重量级名人有看法的心脏又开始激烈跳动起来。我很后悔早出生了十几年,要是俺也搞成个零零后出生的,就现在这个娱乐和道德环境,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如鱿鱼得咸水,那还不活蹦乱跳死。 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现在谁出名,后面总会有几个跟在名人屁股后面挑食吃的贤人。无论这个名人是唱歌的还是跳舞的,是演小品的还是拿大顶的,只要此名人正当红,就啃腚有人冒充不同政见者站出来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什么此名人在作品里降低政治标准啦,什么那个名人收徒弟有封建思想啦,什么这个导演牙不整齐,那个小品演员普通话没有达到国家一级水平等等。我真的不明白,只要这个导演拍的电影大众喜欢,为什么一定要求内容必须加入文革那样口号才算是符合政治需要呢?难道符合群众的东西不是第一政治需要吗?说到底那些向名人下手的人本身不一定不爱看某导演的电影,或许在诱骗文学女青年时,还喜欢拿某导演的电影说事呢。 人怕出名猪怕壮,自古都是这个道理。要说世界的文明史也有几千年了,物质生活和科学技术也都达到一定高峰;可为什么有些东西不能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变的更加文明呢,看来还是他母亲的金钱闹的!评价普通人不能引起轰动,骂普通人也存在现实的风险;遇到个不温柔的,不一定谁能骂过谁,即使警察不逮你,你要骂人家,看不把你的嘴撕歪。但是骂名人没有什么风险,即使有风险也是和收益成正比的。你不去骂名人,别人不知道你是谁;你这么貌似正义的在名人屁股后面一脱裤子,大家在关注名人同时,顺便一转脸----嘿嘿,这还有个好玩的东西呢,这不你也就跟着出名了。接着就会有生产洁而阴的厂家找你做广告,估计治痔疮的也要请你当代言。等广告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厕所墙上传播的到处都是的时,你也就比名人都名人了,无论是你走到天涯还是水底,只要下雨天的夜晚不戴墨镜,一定有群众把你认出来,当你潇洒的把自己那几个字龙飞罢后,一定有粉丝激动的说:有志之士就是不一样啊! 说清楚,是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