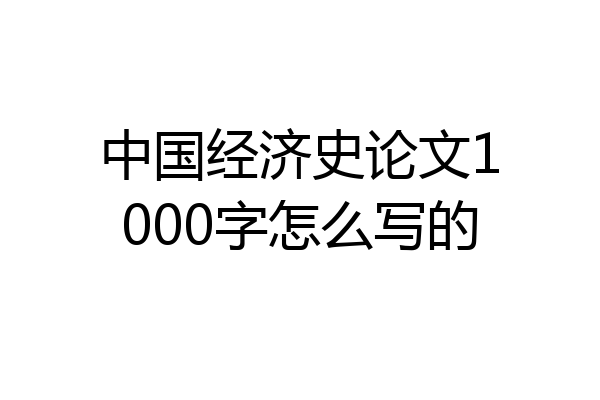18789199527
18789199527
是论文吗?建议最好自己写 传统社会的中国经济及对其发展历程的思考 董方炜 40901008 经济学基地一班 中国在十九世纪前的传统社会中,经济实力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量财富聚集在中国,在几千年的变革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史,面对这样一部丰富的历史巨篇,我们不禁好奇,这其中缠绵着怎样的悲喜纠结,掩藏着多少对错善恶,蕴含着多少文化和精神,又是怎样让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被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国门,投向了经济大变革的浪潮。 经济史是研究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这个社会过程所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的一门学科。其科学性在于考察问题的客观性,在历史文献和大量数据材料中找寻其最能反应社会现实的基础论据,并用一定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演进。其重点在于考察经济运行的机制和绩效,并考虑机制绩效的质与量。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史时,必须要考虑的另一点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出现的哲学或宗教中的精英与大师的思想著述会在该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奠基和指引性的作用,就像雅斯贝尔斯所说“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所出现的大师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确定了西方发展模式,孔、墨、孟奠定了中国发展模式。 考察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史,我们从大到小,从浅如深,从传统经济制度的形成说起,到具体发展成就和财政制度经济思想结束,并着重探讨为何中国并未走向资本主义之路。 在技术条件低下的古代社会,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着国家的经济规模结构及性质,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差异,存在着不平衡性,并预示着不同的经济形态发展方向。例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在攫取经济时代,人们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这是一种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现成天然的物质资料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远古社会的进步非常缓慢,因为这种现成物资的提供限制了远古人类智力的发展。而当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启迪了原始人的智慧,开创了原始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后,人类的社会的迅速发展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人类社会进入了改造自然,通过自身劳动增值产品的生产经济时代,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智力大发展,经济大进步,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并开启了人类罪恶本性的伟大时代。 夏商周时代是由氏族部落向封建领主经济的国度,是奠定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时代。早期人类社会形成了及生产和消费为一体的社会细胞——氏族,随着氏族组织的繁衍于扩大,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部落与部落联盟,并逐渐向王权社会过渡,并最终形成了层层分封的宝塔式结构。中国早期封建社会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井田制上的领主制经济。不管是由于社会传统的巨大惯性还是由于文化堆积力,人类文明的最初时代所奠定的一些思维模式和体制形式都对后世产生了引导性的影响,使后世发展从未摆脱前朝前代所带来的渗入骨髓的根本性的纠缠,并决定了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源于原始社会部落酋长管理生产活动传统习俗的“工商食官”制度,即各级宗族首领控制垄断经营,不允许四人从事工商业的制度,对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这种传统的延递,使人们开始延续重农思维,并不断排斥工商的重要作用,使工商业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春秋时期,封建领主制经济由于其自身内在的矛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而日渐趋于瓦解和崩溃,相应的土地改革产生的土地私有制,引发了剥削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终于在战国秦汉时期,确定了以小农的小规模经营,以精耕细作和劳动力大量投入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在以后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这种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和健全,从秦汉至明清,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曲折变化,兴衰交替,呈现出“两个马鞍形”的发展态势。 中国传统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农业的发展水平及其成就制约着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农业是“人类一切经济发展的开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是以个体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色的劳动力高度密集性的集约农业,其单位面积产量和耕地复种指数都很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利用土地保持地力方面达到了但是世界的最高水平。古代中国一直被认为是经验知识积累量大,经验科学非常发达的社会,而在农业上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多粪肥田”保持了地力,使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仍然能够利用那本来就为数不多田地养活十三亿的人口。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一直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经济所提供的剩余不仅满足了传统社会中非农业部门的消费需要,而且还是专制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繁荣的农业经济史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小农家庭是赋税徭役的承担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历代专职郑度都十分重视农业经济,形成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重农思想和政策体系,维持着精耕细作集约化农业的平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一种经济资源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过随着地权变动机制和地权转移的频繁,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地呈现出不断向各类地主集中地趋势,地主占有土地,目的是投资于土地,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来获取地租,形成租佃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租佃制度也不断调整和完善,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束缚逐渐松弛。中国有很多无产者,即是贫农,贫农租赁地主富农土地,并定时交租,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个特色,这种封建制度下的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工厂中的无产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有官营手工业,城镇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三种生产组织和经营形式并存发展。官营手工业在我国传统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汉武帝时起,中国实行了“盐铁官营”政策,这一政策影响了一个历朝历代的政策制定,对中国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限制作用。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满足皇室和专制国家的需求和生产,二是为了市场生产垄断商品,目的在于追求垄断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垄断地位和为皇室生产不计成本决定了其具有精湛的技艺和低下的收益这两个特点。城镇民营手工业是指由城镇中的一些个体小手工业者和豪民贵族经营的手工业,它是一种脱离农业或农民家庭而独立存在的手工业结构,民营手工业者主要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中国古代脱离农民家庭独立出来的民营手工业大多是以手工作坊的形式已出现的中小手工业者,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只是极少量得存在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次要的手工业部门。由于民营手工业要为专制国家承担各种差役,劳动力得不到保证,缺乏稳定的城乡市场,同时,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有效机制欠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城镇手工业在官营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夹缝中艰难挣扎,发展极其缓慢。 现在我们再从整体上看一下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大不同的经济结构。个体小农经济是我国典型的自然经济,统治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把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满足了家庭基本需求,使之与市场的关系降到了最低限度。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性质的,具有明显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上下同构,相互离散,却又十分稳定。而商品经济则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虽然中国的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完善,但由于其特有的对自然经济依附的特性和缺乏自由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同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虽然存在冲突,但更多的是一种相互补益,共生共存的关系,其最终也未能独立出来。 中国古代财政管理机构不断健全,其曲折的演变过程中,财政管理的权益有相对集中向多极化发展,纵向配置有地方分全乡中央与地方均权发展,财政管理体制在整个国家建制中的地位日见重要。 随着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经济研究经济,在儒学思想出于支配地位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思想以“富、均、庶、义”为基本标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地位一直被人们争论,中国古代也发展出了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放任主义两种思想,但最终确定下来的却是国家不断参与宏观管理,考虑各经济问题时,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立场和利益出发。但几千年来,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处于停止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和变化,不断教条化。 中国历经千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近代史上却不断遭遇耻辱,落后就要挨打,但几千年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何不能自我实现向近代经济的转型,没有走向富强呢? 由于古代中国经济的自营性,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中国传统经济的效率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欧领主制经济,但其有效性又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和摧残。中国的传统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传统商业,但这种商业只是一种补充,并且也扩大了地主和国家的剥削范围和数量,更多的起到维护传统经济秩序的作用。商人、地主、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形成的强大中央集权制度在商品经济危害其自身发展时便伸出了恶魔之手,重农抑商,同时官营资本也在挤占城市手工业的市场,占用了劳动力。 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这种“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而中国在发展中只是中刑法和行政法,轻民法商法,货币制度也不甚完善,长期处于欠缺流动性的情况下。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商业的专门化不只是出现了以经营为目的的手工业等,而是出现了以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以谋取利润者,由于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重农抑商,有存在“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有田方有福”的思想,大批商人购置田产,转而投资土地,成为地主。 所以,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但并未走向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研究中国经济史,从其中找到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不但可以指导我们怎样去发展经济,而且还可以提醒我们,稳定的制度虽然可以给国家带来稳定和长久,但内部表面的和谐不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得到了实现。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虽然保障了封建王朝的延续,但相对于外部世界,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已严重落后,而大部分人民在政府王朝愚民洗脑政策下,不能意识到这些,而专制政府也是为了维护王权和自身利益,不思改革,目空一切,最终被西方用武力打开国门,被迫变革。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政府不应该只是为了保持内部和谐,而应该在应该和必须的时候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真正体现人民利益,发展经济和完善政治体制,以达到国富民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长久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尊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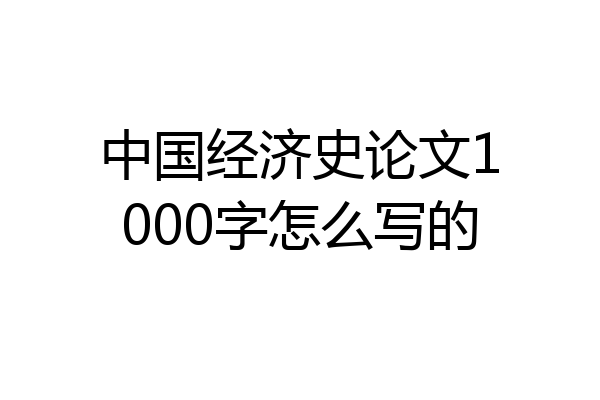
首先,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尚未超出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其次,大量商品不是供不应求而是供大于求。物价上涨是在前几年物价长期负增长或零增长的基础上涨价,是一种恢复性上涨,是我们几年来治理通货紧缩要达到的目的。第三,能源或原材料等基础行业除了电力、钢铁等供给暂时比较紧张外,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全面供给紧张,目前在建的基础行业供给能力很快便足以缓解暂时供给压力。第四,资产“价格泡沫”也仅在局部地区的房地产有一定的体现,在政府一系列措施调控后,形势已开始好转。全国房地产价格上涨只约为5%,股市则已低迷两年半。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