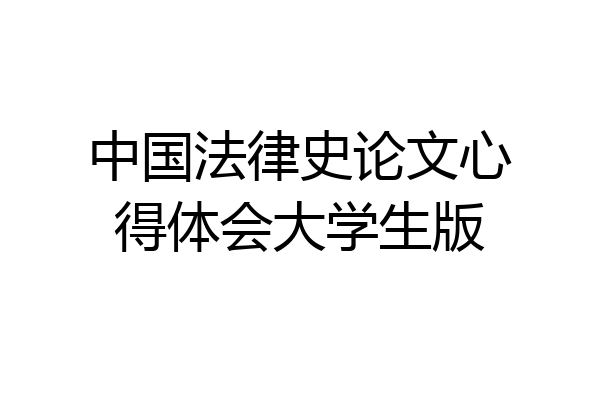fishyulu
fishyulu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它阐明了法学各个分科历史发展的源流关系,因而法学分科的内容更加丰富。并且中国法制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专门史,因而较之一般的历史学尤为深邃。因此决定了研究中国法制史不仅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还需具备法学的功底。回顾多年来法史研究走过的路程,我们不难看到,影响法史开拓研究、古为今用的症结,多是与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法制、法律文化及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有关。因此,正确对待传统法律文化,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是推动法律史学走向科学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首先、法制史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法制史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单化的。我们要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法制史时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再总体的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才有可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其次、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法制历史是复杂的,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法律调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样的。把阶级社会法制的功能唯一归结为阶级专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功能,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 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不能因此把阶级社会的法制史说成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 最后、法制史学的任务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华法文化是悠久的,内容是丰富的。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其中不乏跨越时空的民族性因素,需要从正面加以肯定、阐发,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内涵。而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是法制史学生命力之所在。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再一枝独秀,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这是可喜的,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是需要发展的,而理论分析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质和其规律性。西方的理论,也值得学习,但要弄懂弄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理论要与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但不“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此变革,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发展中国法制史学,使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仍是法制史科研队伍应负的历史使命,为了推进法史学的研究水平,需要积极开拓法制史学的研究领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进取心,在此过程中我们要保持谦虚谨慎态度,自强不息。古人说:“一谦而四益”。面对博大 精深的法制史,确实需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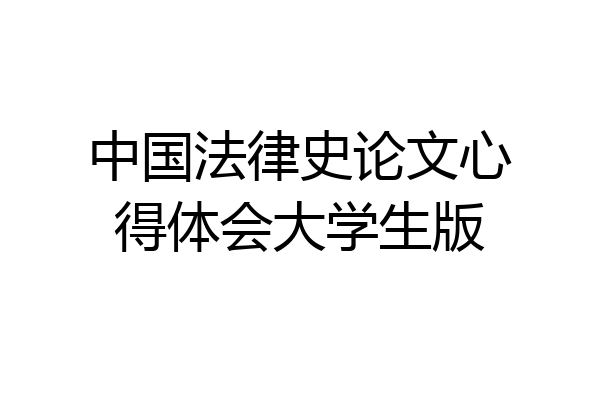
通过学习中国法制史,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精神。西周的法律制度的特点是礼法一元化,礼就是法,法律的精神就是儒家的,尽管此时儒家并未真正出现。而至春秋战国,由于法家思想更符合现实,因此法家实际上取得了立法主导思想的地位,法律的精神主要在这一时段主要是法家。中国古代的法律儒家化肇始于汉代,汉武帝之前的法律是法家化的法律以及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法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官方地位,并通过春秋决狱,将儒家思想引入了司法领域。而其后的引经注律更是以儒家经典注释律文,使法律儒家化。从魏晋至唐,是儒家思想进入法典的时期,这个时期通过立法行为,儒家思想进入了法典,具体表现有曹魏新律的八议制度,西晋的“准五服以制罪”,南北朝的官当、重罪十条以及存留养亲制度的形成,这种礼法和一在唐律中正式形成,形成了“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宋以后至清末是中国法制的进一步深化,此时儒家精神在中国法律中已经定型,法律的演进也就限于形式上的演化,直至清末近代化才开始引发新的变化,打破原有“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引入民主宪政理念,逐步去除了法律中的儒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