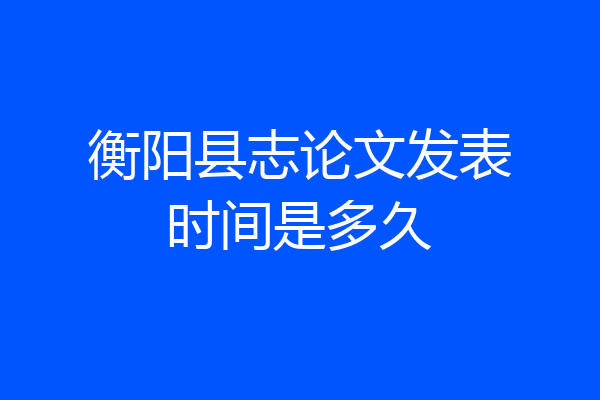einsteinwj
einsteinwj
公元前202年 (衡阳)置酃县,县治附近居民善酿美酒,被后世称谓酃酒。(2003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深埋地下2100年之久的西汉凤鸟金锺美酒出土面世,专家认为,此酒就是产于湖南衡阳的贡品酃酒。)公元280年 司马炎建立西晋,举行开国大典,荐酃酒于太庙。约公元282年 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著《吴都赋》,书中描写衡阳酃酒非常盛名,如:“飞轻觞而酌酃醁”。约公元290年 西晋大文学家张载为酃酒写《酃酒赋》,这是我国历史上为名酒作赋的最早文献资料。公元318—334年 南岳魏夫人饮王子乔琼苏绿酒,即衡州酃酒泡制的养生酒。(相传魏夫人饮此酒后飞天成仙。)公元369年 符坚灭燕国,降前凉,下代国,进西域,四方戎夷,望风而降,很快就“天下郡县十得其八”,基本统一了长江以北的中国领土,国力大盛。符坚每次出兵前都要狂饮酃酒,并说:“此乃酃湖之酒,真勇士方能饮之。”公元4世纪 罗含撰《湘中记》,书中介绍产自衡阳的酃酒为美酒。公元4世纪 庾仲雍撰《湘州记》,书中写道:“湘州临丞县(即衡阳)有酃湖,取水为酒,名曰酃酒。”公元432—445年 南朝范晔撰《后汉书》,该书卷三十二记载:“(衡阳)有酃湖周迥三里,取湖水为酒,酒极甘美。”公元450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入侵南朝时,俘获了南朝将领蒯应,后又将之释放。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立即派人送上等酃酒去北魏犒军。于是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和。公元6世纪 北魏郦道元的著名地理名著《水经注》卷三十七准确地记载了酃酒的产地和酃酒之美:“酃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居民彼人资以给,酿酒甚美,谓之酃酒。”约公元630年 唐太宗盛赞酃酒之美:“酃醁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公元646—648年 唐代房玄龄等21人修《晋书》,书中记载了酃酒自晋代就开始为贡品的历史:“武帝荐酃酒为太庙” 。公元1060年 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同宋祁等人撰《新唐书》,书中记载了产自衡阳的酃酒是美酒。约公元1063年 刘学士来衡州任知府,欧阳修在《送刘学士知衡州》诗中特地赞美了衡州的酃酒之醇美:“湘酎自古醇,酃水闻名久。”公元10世纪 北宋未年,宋徽宗予张皇后、张驸马(二张均系衡阳籍)家酿酃酒赐名,曰酃醁。公元11—12世纪初 北宋将贡品酃酒作为宫中诞育的犒赐,《武林旧事》之卷八载:“宫中凡阁分有娠……于内藏库取酃醁沈香酒五十三石二斗八升。”公元17世纪 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仍将酃酒列为贡酒,称谓“衡酒”。公元1686—1743年 清朝廷编修《大清一统志》,该志书中记载:“酃湖在衡阳县东,水可酿酒,名曰酃酒。”公元1763年 清泉(衡阳)知县江恂主修《清泉县志》,卷二·地理志·风俗记载:“邑本汉之酃县,俗工造酒,盖酃酒之遗也,然味醇而值贱,饮者多不拘时,侨于旅而倦于游。”公元1805年 马倚元主修《衡阳县志》,县志记载酃酒历史悠久:“酃酒者,彰灼史传,取重仪狄,凡三千年。”公元1872年 清大臣曾国荃歧山进香,获仁瑞寺养生秘方——“酃酒百子汤”, 治愈不育之症。公元1889年 衡阳岐山仁瑞寺主持田静法师以酃酒神曲水治愈慈禧太后疑难之症。公元1935年 民国政府创办《中国实业杂志》,该刊为经济类刊物,刊登有关中国经济方面的论述和中外特优实业调查。衡阳酃酒书上有名:“湖南酒产以衡阳产者为最著,自来有酃湖美酒,古称酃酒。晋代用以祀太庙,清初作为贡品,其质冽,其味醇,为湖南省其他各县酒产所不及。”公元2001—2007年 湖南省酃酒酒业有限公司整理古代酃酒史料、工艺技术、收集酒器、酿造工具等600余件,建立酃酒文化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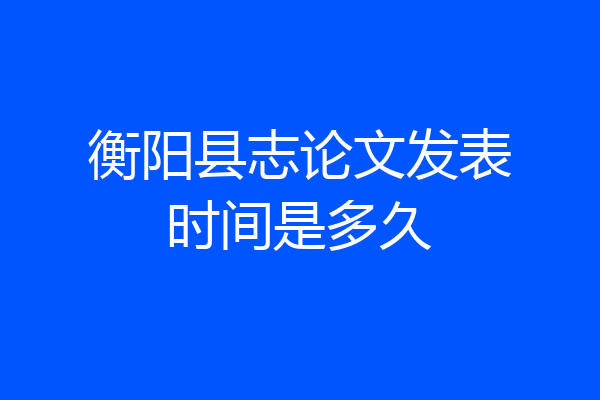
第二节 影响衡阳城市文化变迁的内外因素中国城市文化的近代化路径不是单线条式的长驱直入的,这是由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的特点决定的。因此,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产生与形成便呈现出多角度交叉发展的趋势。城市文化近代变迁的主要向度,一是西方文化的中国传播对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带动。二是传统城市文化的近代转型。三是随着城乡联系的逐渐加强,具有近代因素的某些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的靠拢,在城市文化的大容器里经过化合、锤铸而成为近代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当然还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也会对城市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为了便于分析,将影响衡阳城市文化近代变迁的主要原因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内发性因素这些因素既是衡阳近代城市文化变迁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衡阳城市文化变迁的原因。他们相互之间还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为经济结构的近代变迁。古代衡阳城市主要担负政治、军事功能,城内的主要经济形式是简单的商业贸易,为满足城内官员、士绅生活起居所需的基本资料,城内其他居民不多,采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住在外城的居民因生活资料而发生的交换行为大多发生在城外或者城墙的外围地段。到了近代,工商业经济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增强,城内居民日渐增多,城狭人促,对商业贸易的依赖加强。近代衡阳城市的经济模式逐渐从时间节奏缓慢的农业社会模式渐变到节奏快、竞争激烈的商业模式,人们获取生存的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这就为城市文化的近代变迁埋下了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因为商业贸易逐渐成为城内的经济形式,因为商业而带来了各个行业的演变,衍生出近代的机构、设施。行业文化兴盛,报纸杂志等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加速了文化的流转与更新,近代新式教育带来了突破传统的新观念,因为商业竞争而受到影响的市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变化,娱乐活动内容更加丰富,所有这些既是城市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也是变迁的内容。各个方面的变迁最后在城市逐渐融合铸造成新的文化。第三,由于商业的兴盛,各行业从业人员很多,加上城市本身的居民,导致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市民阶层,适应市民阶层的闲暇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最终发育成城市文化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市民文化,或者叫市井文化。这些文化的整合、变迁、创新的过程构成了衡阳近代城市文化变迁的全过程,丰富了衡阳近代城市文化的内涵。外在因素“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演进的产物。自有历史以来,城市的特征,均因特殊的需要而改变。如军事性的防御,行政制度,科技进步,生产和交通方式的改变等都影响到城市的特征”,进而影响到城市文化的特征。影响衡阳作为湘南经济中心地位的主要因素是陆路交通的发达。随着民国时期铁路和公路的发达,衡阳与本省其他各市、外省等联系大为加强,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其他各市之间的内部联系也日渐增强。民国期间长株铁路和潭宝公路修通时,江西、邵阳的贸易不经过衡阳而改道湘潭,致使衡阳市场出现衰落。而粤汉铁路、湘桂公路的通车既加大了衡阳与沿线城市的联系,无疑也加强了沿线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反而是对衡阳城市功能的削弱。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湘南政治和经济中心,衡阳的聚集和辐射作用被削弱。这也是近代中国逐渐城市化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近代直到目前的城市化的进程,使中国近代以前的中心点城市辐射四周腹地的单一放射状结构变为星星式的网状结构,辐射影响的方式更加复杂。必将加强城市之间点对点的直接联系而削弱上一级城市与下一级城市的行政关系甚至最终打破区域的限制。城市对省级行政区域的离心化和独立化趋势与省级地域对中央离心化和独立化趋势一样不可忽视。其次,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也对衡阳的城市空间结构产生影响。近代广州作为南方经济贸易中心的衰落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的兴起以及省内北部的岳州、长沙相继开埠,湘潭、长沙的崛起对湘南的冲击和削弱,衡阳的经济从向南发展转变为与北方紧密联系起来。大量的物资通过湘江北上,抵达长沙、岳阳、汉口直至长江中下游。在这个过程中,北方的风尚习俗、长江中游城市武汉、岳阳开埠,西方文化的逐渐渗透对衡阳的城市文化变迁产生重大影响并在衡阳的文化、建筑、宗教伦理、市民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上表现出来。 其次,历史上衡阳辖区的不断分合对衡阳城市文化发展亦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乾隆二十一年,析衡阳为衡阳县和清泉县,但两县治同城,衡阳城市呈现双核心发展的结构。到民国时期又将两县合为一县,并于1942年升为省辖,客观上提高了衡阳的地位,聚集了更多的行政和社会经济资源,对于境内文化的繁荣和辐射都有重要的影响。第三,抗日战争时期的人口流动对社会阶层和民俗的融合影响深刻。社会风俗习惯和社会心态是社会文化中的表层,也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它的形成与一定的人群在较长时间内相对定居密切相关,因为它缺少交流,缺乏新的文化因子,故而有较大的封闭性与文化惰性。战争引起的难民流动对衡阳社会风俗习惯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他们的到来给衡阳人民展示出陌生的区域文化,不同的区域文化在这里交汇,孕育出新的文化因子,给当地的城市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与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