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q30208
qq30208
高行健的探索剧不仅创造了当代戏剧的新形式,而且突破了传统戏剧单一、封闭的戏剧思维,创造了一种开放、多维的戏剧思维,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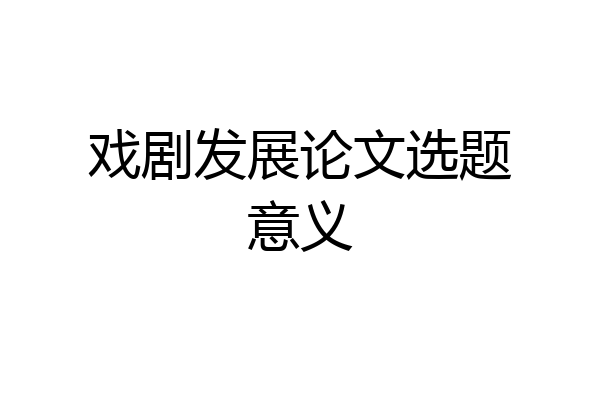
2005年5月15—17日,中国戏曲学院主办了“京剧的历史、 现状与未来暨京剧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京剧研究领域内引起众多专家学者们非常强烈的反响。因为这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研讨会,其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意在提供一个纯粹的研究平台,聚合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探讨与京剧相关的学术问题,同时更试图通过这个大型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正式提出“京剧学”这个学科称谓;它意味着中国戏曲学院面对海内外京剧研究界的所有同行公开且正式推出“京剧学”学科建构计划,这将是戏曲学院面向未来的规模庞大的学术发展计划的重要开端。一次学术研讨会承担了那么多的功能,这是学术研究领域并不多见的学术现象;这也是京剧界从专家学者到表演艺术家和剧团管理者都对这次研讨会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原因。 学科称谓的来源以及分类法千差万别,就某个大学科内的分支而言,分类最常见的方法大致是两种,或以研究对象区分,如汉语有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之分,中国文学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分,它们分别研究中国语言文学范畴内不同时段的内容;或以研究方法和特色区分,如经济学领域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等,它们所研究的对象可以基本一致,由于方法与学术取向上的差异,就明显地形成多个分支。作为一个学科的“京剧学”假如能够成立,它的分类学依据显然属于前者。毋庸赘言,它将会是归属在戏剧学(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设置称为“戏剧戏曲学”)门类下的一个分支,与戏剧的基础理论研究、外国戏剧研究相并立,也可以与戏剧文学、戏剧舞台美术、戏曲音乐等六类相交错,并且与戏剧学领域其他剧种的专门研究相区别。从这个角度考虑,京剧学的学科定位,在理论上是非常清晰的。 如果京剧学作为戏剧学门类里的一个分支学科有可能成立,那么,以京剧在中国戏剧领域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在20世纪以来中国戏剧现实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极有可能成为戏剧这一学术领域内的一门显学。而京剧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出现,还会进而带动中国戏剧的其他剧种的专门研究,刺激昆曲、秦腔、川剧、粤剧和越剧等等有影响的剧种的专门研究,而一旦京剧研究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分支学科的学术地位得到普遍承认,各地方剧种的研究,也就很容易随之构成学术上相对独立的分野。 正因为京剧在中国戏剧乃至于中国文化整体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提出“京剧学”这样一个学科分支,推动这一学科的建设计划就成为非常严肃的学术研究事件。 如果从学科称谓上看,正在建构中的京剧学可以称之为一个“新”学科。新学科不断涌现是晚近学术研究领域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现象,无论是1980年代中期大量的所谓“交叉学科”,还是最近各地专以地方文化现象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地域性学科,倡言者均不乏其人。然而,学科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个学科是否确实形成,并不能以是否已经有人正式提出这个学科称谓为衡量的标志,即使倡言者为之做出了具体的学科内涵与外沿的界定,也还不能满足学科成立所需的充分条件。学科成立的真正要件,在于它必须得到业内外人士自然的承认,因此,一个学科何时成熟,一个大学科内的分支学科何时从它所属的学科中相对独立出来,并非人为可以设定。更重要的是一个学科之形成,需要有相当数量为学界公认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及可以持续开展的研究项目与课题为支撑,逐渐形成一个以这一学科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群体,而返观1980年代红极一时的不少所谓“新学科”和“交叉学科”,由于并不具备上述条件,即使拥有倡言者振臂一呼时的学科建设遐想,终究只能耸人听闻于一时,所谓“新学科”也就徒具其名并无其实。 京剧学的现状与这类“新学科”不能混为一谈。京剧诞生两百多年来,有关京剧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即使以它之成为现代学术研究对象的晚近数十年计,自齐如山以下迄今,专门的研究成果也难以计数。在当下中国戏剧研究范畴内,京剧研究的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剧种的专门研究,其研究的触角也已经深入到京剧的文学、音乐、表演、舞台美术等方面。而且,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戏曲学院这所以京剧研究与教学为主要特色的高等院校组建以来,早就已经有相当一批资深学者长期从事京剧领域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专门研究者群体;而除了这个人员相对集中的群体以外,多年来,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中国其他城市,包括台湾地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欧美和澳洲各国,在文化部所属的各专门艺术研究机构还是在高等学校,从事京剧专门研究的都不乏其人,而每年都有多位以京剧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生,更说明京剧研究的学术内涵与价值,早就已经在海内外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同。京剧史、论等多方面的研究,在中国戏剧研究这个重要学术领域内的影响以及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但京剧研究之得到学术界关注和引发海内外众多学者兴趣的原因还不限于此。除了京剧艺术本身的研究价值以外,一方面由于京剧最集中地代表了中国戏剧20世纪发展的路径与成就,同时也由于京剧在中国现当代社会进程中曾经起到过非同一般的重要影响,京剧研究领域的学术空间,更因为这些超越剧种本身甚至超越纯粹艺术层面的意义而得以大大拓展。 因此,“京剧学”这个学术称谓的提出,并非灵机一动的突发奇想,也不是欲以白手起家的毅力平地起高楼式地开创某个学科,只是以新的学科建设的自觉,借大学这一特殊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专门机构之力,致力于更好地整合、完善与提升京剧研究这个已然存在的学术领域。它并不求石破天惊的效果,更接近于一种新的学术策略。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就不难明白何以中国戏曲学院提出建构京剧学这个学科时,并不急于在理论与概念上为它做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像京剧学这样的学科,确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固然是重要的,然而,正因为无论是过去是当下,京剧研究都已然拥有相当的成就和规模,它的存在早就已经是不争的现实,因此,对于学科建设而言,更重要的和更为迫切的任务,不是学究式地思考“什么是京剧学”或“京剧学究竟应该研究什么”这类早就已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而应该更多地着眼于为相关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希望立足于现有厚实的研究基础,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由一代又一代研究者和新的研究成果自然地充盈其内容,促使这一分支学科清晰而健康地立足于学术之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京剧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正在努力倡导和推动这一学科发展的中国戏曲学院将完全无所作为地静候着京剧学自己走向独立和成熟。事实上,提出有关京剧学学科建设的这次研讨会之所以在京剧研究领域引起强烈反响,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学科称谓有多么令人激动,而更多地是由于学者们通过这一举措,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戏曲学院决定将京剧学作为学院学术发展的主导方向这种学术上的自觉意识。因为学科建构的自觉意识,将有助于让京剧研究朝更具系统性与完整性的方向发展,而像京剧这一内涵十分丰富、涉及面非常广泛的研究对象,如果不能考虑到研究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研究成果很容易成为一盘散沙。举例而言,中国戏剧有包括京剧在内的三百多个剧种,至少有一百多个剧种历史地形成了自身较完备与独立的音乐声腔系统、剧目系统、表演技法系统,但是长期以来,不同剧种对这三个相辅相成的系统的研究往往各有偏重,包括在资料的积累方面,也存在非常之明显的差异,比如,1950年代初各地曾经搜集整理了数以几万计的京剧和各地方戏的演出剧目,但是在各剧种音乐方面的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就远不如剧目那样受重视,而表演艺术方面的资料积累,则更是严重缺乏。显而易见,无论是哪个方面的研究和资料积累的缺失,都足以影响到今人与后人对于研究对象完整准确的认识与把握。即使以表演艺术方面而言,不同行当乃至于不同流派的研究,更会因许多偶然因素的作用呈现极不平衡的状态,部分行当和流派可能受到较多的关注,而同样重要的行当或流派,却有可能遭到不应有的忽视,甚至完全缺乏研究,致使剧种研究限于一端。学术研究当然需要给所有研究人员充分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如果同时考虑到研究的完整与系统性,就需要有影响的、有学术自觉的学术机构,通过有组织的、更客观的全面研究防止种种偏颇的出现。 通过某种学术自觉以组织与整合京剧学研究是一个方面,通过大学这种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组织推动学科的核心课题的深入研究,则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虽然京剧研究的成果颇丰,在京剧学的学科建构方面,依然任重道远。除了对京剧内部不同方面的研究的还不均衡,还有相当多新的研究领域值得去努力开拓,如学者们曾经提及的京剧文化、京剧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自有其重要价值。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京剧史论研究领域尚有很多关键性的学术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较完满的、足以为京剧界内外所公认、并且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解决。从史的角度看,极左思潮的影响余温尚存,对京剧历史与现实的评价往往因此丧失应有的客观性,对历史和现实有意无意的误解甚至曲解比比皆是;从论的角度看,苏俄化的西方戏剧理论框架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对京剧的认知模式与评价尺度,京剧自身的特色与魅力往往因此被遮蔽。有关京剧研究的历史资料,除了张次溪的《清代燕都梨园资料汇编》以外,自民国以来至今的大量基本史料,都还没有得到完整的搜集与整理。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固然重要,但是,只有位居学科核心的上述主干课题研究方面的明显突破,才足以充分体现一个学科之进步与发展水平,而要想在这些方面取得满意的成就,就特别需要一个有学术自觉的机构、团队以及学科带头人倾力以赴,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赢得学术界乃至世人对于学科之成立和成熟的自然承认。 在学术研究领域,没有什么比一个学科的草创更困难,但也没有什么比它更具挑战性。作为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我深知在京剧学学科建构这一学术设想的实施过程中,应该承担哪些重任。如何凝聚现有的研究力量,组建和培养新的研究队伍,通过数年的集体努力,尽可能弥补现有的较大和较明显的学术缺失,使这一学科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并且在史、论和资料建设这三个学科核心的研究方向有所突破,藉此明显提升学科研究水平,都将成为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最优先考虑的目标。完成这些重要工作之后,“京剧学”将不再只是一个称谓和设想,它作为一个单独学科的存在,将成为不言而喻的现实。对此,我深信不疑并将为此持续努力。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 戏剧起源 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 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 (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 (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 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 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 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 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 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 (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 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 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