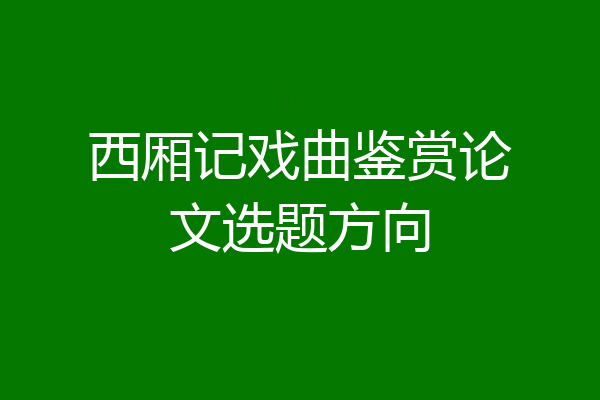s1247191
s1247191
《西厢记》是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部杰作,它诞生于盛产戏曲的元代,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精湛优美的艺术性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喜爱。作品里描写的崔张爱情故事简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而作品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它那璀灿优美的语言艺术,更令历代各阶层人土,包括自视甚高的历代文人墨客都为之扼腕赞叹不已。正是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现,作者王实甫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这位来自社会平民阶层的人士与当时另一位戏曲大师关汉卿齐名,其作品全面地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又吸收了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并将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文采璀灿的元曲词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所谓“文采派”的最杰出的代表。明朝初年著名戏曲评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称《西厢记》:“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本文拟就《西厢记》里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语言艺术,试为论述二三,管窥之见,浅陋在所难免。一、《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丰富性大凡读过《西厢记》的人都觉得这部剧作的语言文字很美,让人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走进一座迷人的语言艺术宝库,觉得异彩纷呈,目不暇给,如珠似玉,叹为观止。这部剧作包涵着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语言,而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所以,研究《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到它语言艺术的丰富性。剧作中有雄浑豪放的曲辞: “[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却便似弯箭乍离弦。”①(第一本第一折)这里把九曲黄河写得何等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剧作中也有绮丽流畅的小词:“[中吕][粉蝶儿]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绎台高,金荷小,银镇犹灿。比及将暖帐轻弹,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偷看。”(第三本第二折)这里洋溢着美好幽深的诗一殷的气氛。但剧中写惠明和尚的唱词却是另一种慷慨激昂的“金刚怒目”式,请看剧本第二本《楔子》:[正官][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仟》,风了僧伽帽,袒下我这偏衫。杀人心逗起英雄胆,两只手将乌龙尾钢椽昝。[收尾]恁与我助威风擂几声鼓,仗佛力呐一声喊。绣旗下遥见英雄俺,我教那半万贼兵唬破胆。这是高亢激越,掷地有声的英雄誓词。剧本中也不乏幽默解颐的话辞,请看《拷红》一折(第四本第二折)中一段唱:[鬼三台]夜坐时停了针绣,共姐姐闲穷究,说张生哥哥病久,咱两个背著夫人向书房问候。(夫人云)问候呵,他说甚么?(红云)他说来,道‘老夫人事已休,将恩变为仇,著小生半途喜变作忧’。他道‘红娘你且先行,教小姐权时落后’。(夫人云)他是个女孩儿家,著她落后怎么?(红唱) [秃厮儿]我则道神针法灸,谁承望燕侣莺俦。他两个经今月余则是一处宿,何须你一一问缘由?这一段的曲白是十分精彩的,尤其是红娘十分俏皮的“供词”,逼真地表现了红娘的绝顶聪明和老夫人的无奈,具有很好的喜剧效果。上面所举数例可使我们对《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丰富性略见一斑。《西厢记》在对环境气氛的描写和对人物性格性情的刻划方面则使我们对其语言艺术的丰富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剧作对环境气氛的描写是为衬托人物活动服务的,剧本为一部崔张爱情诗剧,剧作者描摹环境,突出诗情画意,结合人物活动,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堪称生花妙笔。剧中展开情节冲突的环境为僧舍普救寺,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将普救寺理想化地写成一个“幽雅清爽”,饶有诗意的胜境,请看:“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在这里,经常佛殿上阴森肃穆的气氛,罗列森严的罗汉菩萨、烧香的婆子俗客,以及念经的和尚,一概略而木写,而只写了相近青霄的琉璃殿、幽静的僧房以及青色的苔、红色的落花,使男女主人公在这样充满诗意的环境中展开一段千古称颂的风流佳话。下面再看第三本第二折写莺莺的闺房是“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 扉摇响双环。绛台高,金荷小,银钉犹灿”。这里通过描绘莺莺的闺房,创造了一种幽深闲静,香气弥漫的美好氛围,这与茸茸举止娴静、深沉含蓄而又感情丰富的性格是相吻合的。即使在剧中个别情节有悲苦性质的场面里,作者的描写依然笼罩着诗般的气氛。比如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其语言是借助古典诗词描写离愁别绪的特有表现手法来加以渲染的,是以那种诗意的浅浅哀愁和无奈的色调来表现主人公离别时的悲苦的。在刻划人物性格感情方面,作者善于驾驭语言的天才得到古今读者又一首肯。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剧中有关描写人物的语言,便会感到人物的至情至性(或典型性格)无不一一凸现,令人有其声如其口出以至呼之欲出的感觉。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戏剧不同于小说或其他文艺形式,后者常常采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但戏剧则必须通过剧中各种人物不同的声口说话,以性格化的语言来刻划人物,《西厢记》在这方面堪称典范。请看第二本第一折,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欲掳获莺莺做压寨夫人,众人慌作一团计无所出。莺莺则提出著名的“五便三计”:第一计献身于贼,第二计献尸于贼,老夫人皆认为不可,于是有第三计:“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例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老夫人认为此计较可,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陷于贼中。此时,好一个张生,在众目注视下出场了:“(末鼓掌上云)我有退兵之策,何不问我!”这一句“何不问我!”有力地表现了张秀才的才智胆识,使人感到这位痴情的书生并不是无能的懦夫,而是临危不惧的勇士。由此,张生在众僧人和莺莺、红娘的心中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应当说,在《西厢记》中,这种即景生情而又贴合人物个性的语言是很多的。请再看第三本《楔子》的开头——莺莺: “自那夜听琴后,闻说张生有病,我如今著红娘去书院里,看他说甚么?”(唤红娘)红娘:“姐姐唤我,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莺莺:“这般身子不快啊,你怎么不来看我?”红娘:“你想张……”莺莺:“张甚么?”红娘:“我张著姐姐哩。”这数句对白不外是 莺莺打发红娘去探望张生,但人物语言声口,见性见情。 莺莺身子不快、实有心病,她却先责怪红娘不来看望自己,红娘对小姐的心病了如指掌,因此快人快语,语刚出口,又觉得过于直率,怕小姐难以下台,一句话只说了半句就顿住:“你想张……” 莺莺对“张”字当然敏感,立即追问,红娘急切间改口:“我张(望)著姐姐哩。”足见红娘聪明狡黠,善于应对。这段对白固然表现了 莺莺红娘间亲密的主仆关系。但莺莺说的话自是莺莺身份,话语闪烁不定,不易捉摸。红娘虽是下人,却机警有谋,惹人喜爱。《西厢记》中这样精彩的性格化的语言对白是不胜枚举的。通过语言对白刻划人物性格,是《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一个特点。《西厢记》语言的丰富性还表现在作品对民间俗语的吸收运用。当然,这也是为刻划各种人物不同性格服务的。纵观全剧,剧作者对文化修养高的人物如张生、莺莺多用文雅的语言,而对于文化修养较低,性格粗豪或爽朗泼辣的人物,如惠明和尚、红娘则多用口语俗语。请看第二本《楔子》惠明和尚出场所唱:[滚绣球]非是我贪,不是我敢,知他怎生唤做打参,大踏步直杀出虎窟龙潭。……[耍孩儿]我从来驳驳劣劣,世不曾忑忑忐忐,打熬成不厌天生敢。我从来斩钉截铁常居一,不似怎惹草拈花没掂三。……上述曲子中有口语: “打参”、 “驳驳劣劣”、 “忑忑忐忐”、 “天生敢”、“没拈三”,成语则有“虎窟龙潭”、“斩钉截铁”、“惹草拈花”等,通过这些口语成语的运用,刻划了惠明和尚天不怕地不怕的粗豪性格。又请看剧作第四本第二折《拷红》有些曲子:“[越调][斗鹌鹑]则着你夜去明来,倒有个天长地久;不争你握雨携云,常使我提心在口。则合带月披星,谁着你停眠整宿?老夫人心数多,性情馅,使不着我巧语花言,将没做有。”上述曲子中出现好些成语,如:“天长地久”、“提心在口”、“带月披星”、“巧语花言”;还有当时的民间口语俗语,如:“心数多”、“性情 ”、“将没做有”等,是从红娘的口中道出的。这些很好地表现了红娘热情泼辣,聪明机敏的性格。这些成语口语俗语在曲辞中的穿插运用,既生动传神地刻划了人物性格,又使曲子通俗易懂并且琅琅上口,使全剧达到华美与通俗的和谐统一。《西厢记》作者善于学习并成功地运用民间俗谚口语,是使这部剧作语言丰富多彩脍炙人口的其中一个因素二、《西厢记》语言艺术的文采性古典戏曲发展到元代,可以说是迈上了一个高峰,唐诗宋词元曲,世人皆言,说明元曲与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代表一个朝代的珍品,这与其语言艺术的成就是分不开的。元杂剧分为本色派、文采派两派。本色派以朴素无华,自然流畅为语言特色;文采派则以词句华丽、文采璀灿为特点,并十分注意修饰词语,有很好的修辞技巧。关汉卿是本色派的语言大师,王实甫则为文采派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西厢记》堪称文采派的典范。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其文辞之华丽、故事之曲折、文笔之细腻、人物之传神均属一流。“文辞华丽”是《西厢记》语言艺术的特色,这种语言特色是形成剧本“花间美人”风格的重[赚煞]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人情牵。“临去秋波那一转”乃曲中之眼,美而传神。第三本第二折,又通过红娘之口正面写了驾营:[醉春风]则见他钗蝉玉横斜,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t普天乐]晚妆残,乌云彩掸,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鬟。将简贴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折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这折唱词以秀美的艺术语言刻出莺莺外表懒散娴静,内心却对张生病情消息的焦虑和等待以及见到简帖后的喜悦心情。可见剧本写人与状物一样,其语言同样不乏华美秀丽的特色,保持着“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这在写剧中其他人物,如张生、红娘、老夫人、惠明和尚等时也随处可见。倘若没有语言上这种五彩缤纷的娟丽姿采,“花间美人”就要黯然失色。下面再请看《西厢记》中的几组名句(诗),我们对“花间美人”的灿然文采就更能领略了。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第二本第一折)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第四本第三折)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第三本第二折)以上这些绝妙好词,在《西厢记》里面俯拾皆是,真是美不胜收。这里无庸再一一例举。正是这些“词句警人,余香满口”的艺术化语言,使《西厢记》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气氛,成为一部百代称誉的诗剧。说到诗与词,若数词句华美、文采璀灿莫过唐诗宋词。《西厢记》剧作者的成功之处是吸收了唐诗宋词的精美语言,使剧作语言更富于文采性。如第一本第一折张生的唱词:“[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便是化用唐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又如第二本第一折营茸的唱词:“[混江龙]……隔花阴人远天涯近。”则是化用宋女词人朱淑真词《生查子》句:“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又如第一本第四折张生唱词:“[鸳鸯煞]有心争似无心好,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里化用宋苏东坡词《蝶恋花》中句:“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还可以举出更多这样的例子。显然,剧作者对唐诗宋词的喜爱,使他不仅乐于在剧作中采用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且乐于化用这些诗词当中的经典名句,使之贴合剧中的人物,感情及环境,从而使这部剧作亦增添了五彩缤纷的璀灿文采。《西厢记》的文采性在语词优美、娟丽动人方面确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这部剧作的文采性,也表现在其包含有丰富的修辞技巧,因而剧作的语言修饰达到美轮美奂的境界。据《中国戏曲通史》(张庚、郭汉城主编)统计,全剧运用的修辞手法达34种之多。这里只举出一种修辞格——“复迭格”中迭字词的运用,如剧中第四本第四折“[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这里“绿依依”、“静悄悄”、“疏刺刺”、“昏惨惨”等迭字词的运用对加强语言的表现力、增强环境的渲染起了很大的作用。再看剧中第一本第三折,作者是如何传神地运用迭字词来表现张生的动作与心情的:[越调] [斗鹌鹑]……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悄悄其其,潜潜等等。[紫花儿序]等待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悄悄冥冥”等迭字词,形象生动,恰到好处地写出张生对莺莺的爱慕及主人公初恋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剧中类似这种精妙的迭字词还有许多,这类迭字词的巧妙运用使作品写影写情述事皆臻妙境。其他的还有三十余种的修辞技巧就不一一例举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②正是这些有丰富修辞技巧的曲词,才使人感到《西厢记》这部剧作语言的精美。从这一角度来看,《西厢记》语言的文采性是作者精雕细刻的结果。必须指出的是,《西厢记》文采璀灿的语言特色,绝不是形式主义的堆砌词藻,雕琢造作,使人晦涩费解。全剧语言华美秀丽而流畅自然,达到“清水出英蓉,天然去雕饰”③的境界,这是同时代以及其他著名戏曲作者所不能企及的。还必须指出, 《西厢记》是有着严格韵律限制的戏曲作品,要在一定的规矩内作出切合人物环境戏情又合乎韵律的精美曲辞,绝非易事,比如第一本第三折中张生唱:“[么篇]我忽听、一声、猛惊,元来是扑刺刺宿鸟飞腾,颠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第二本第四折中莺莺所唱: “……本宫、始终、不同。又不是《清夜闻钟》,又不是《黄鹤醉翁》,又不是《泣麟》、《悲凤》”。六字中三押韵,极不易制作,剧作者填写得既合韵律,又拟声写情,精美绝妙,确非大手笔不可。明朝何良俊所写的《四友斋丛说》认为“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词之雄”,然哉斯言。三、结语《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的一部杰作,它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妙的艺术风格使这部作品七百年来一直雄踞“一流”的宝座。作品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语言艺术,可以这样说,运用什么样的语言,作品就具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无与伦比的,它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吸取了这些古典诗词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经过提炼加工,博取众长,从而形成自身华美秀丽的语言艺术特色。所以《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①见《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西厢记》第7—8页,王实甫撰,张燕瑾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下文引《西厢记》均见此书。②[宋]朱烹《观书有感》诗句,见(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7页。③[唐]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灾培良宰》诗句,《全唐诗》170卷,第17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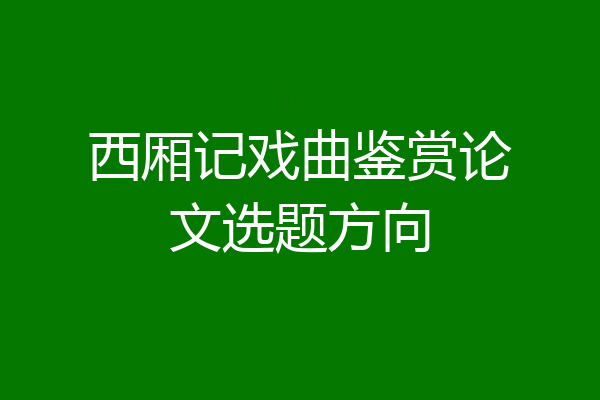
文体:元曲(元杂剧) 背景及赏析: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背景材料 一、《西厢记》作品年代概况: 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最早成于元代成宗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最晚成于元代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如按最晚的时间算,2007年是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诞生700年。(王季思、黄天骥《四大名剧》岳麓出版社) 二、王实甫生平概况: 《西厢记》作者王实甫为北京人,“名德信,大都人”。(钟嗣成《录鬼簿》)王实甫准确出生年月已不可考,但略晚于关汉卿的观点得到史学界承认。 三、《西厢记》的演变: 《西厢记》的文学源头为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形成最早为唐德宗贞元末年(约公元802年至804年),距今大约1200年。《莺莺传》并不是唐传奇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作品。有“今世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指崔张故事)以为美谈”之说。《莺莺传》中的基本矛盾是张生与莺莺的矛盾,是爱情与负心的矛盾,结局是悲剧性的。 金代(公元1189年至1208年),出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史称“董西厢”。在“董西厢”中,人物基本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张生与莺莺共同追求爱情幸福而与封建家长之间的矛盾,成为爱情与礼教的矛盾,结局是喜剧性的,“董西厢”用崔、张二人共同追求幸福爱情的动人故事,取代了《莺莺传》“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 到了元代,《西厢记》终于定型,主题逐渐从一个“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发展成“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爱情理想宣言,形式上也从说唱文学过渡到元杂剧。 王实甫的《西厢记》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个性化;艺术上更加精美成熟,;结构严谨完整,情节起伏跌宕不落窠臼;心理描写与人物性格、戏剧情节紧密相关;语言华美、富有个性化。王实甫以赞扬的笔调,细腻的笔触,充分描写了莺莺和张生作为初恋的少男少女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而不再认为这是一种罪过,也不再考虑是否会误国误身。简而言之,杂剧中的莺莺,不再是妖孽、不再是尤物,而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寻求爱情幸福的纯情少女。作者对爱情给予了的高度肯定,对人的正常的权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王实甫的《西厢记》打破了传统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格局,学习南戏的体制,首创性地以五本二十折(或作二十一折)的宏大篇幅,来给以足够的表现;又打破全戏由一角唱到底的体制,让张生、莺莺、红娘甚至配角惠明都唱,一出之中也灵活转换唱的角色,用丰富变化的手段来表现丰富变化的内容。 现在通行的《西厢记》刊本以暖红室复刻凌梦初本为底本,并以王骥德、金圣叹、毛西河、刘龙田、何璧、张深之诸本以及《雍熙乐府》参校。校点时,参用了《集评校注西厢记》(王季思校注,张人和集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和《西厢记新注》(张燕瑾、弥松颐校注)的研究成果。 四、《西厢记》的历史评价: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贾仲明《凌波仙》)。 “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明:王世贞《曲藻》)。 “读《西厢记》,必焚香读之;必对花读之;必与美人并坐读之;必与道人对坐读之”(金圣叹)。 “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明朱权《太和正音谱》)。 “古戏必以《西厢》称首”(明王骥德《曲律·杂论三十九》)。 “《西厢》无所不工,《西厢》之妙,以神以韵”(明王骥德《新注古本西厢记附评语》)。 “令前无作者,后掩来哲,遂擅千古绝调”(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序》)。 “吾于古曲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能之”(清初李渔《闲情偶寄》)。 《西厢记》评本数量之多和评论的名家之多,皆遥遥领先于其它戏曲、文学名著,不仅在中国文艺史上而且在世界文艺史上也是罕有伦比的。 《西厢记》在明清两代有著名的徐士范、李卓吾、徐文长、王凤洲、沈璟、汤显祖、王骥德、陈继儒、徐奋鹏、凌豫初、闵遇五、金圣叹、毛西河、周昂等十数家评本,荟萃明清一流文艺理论家,并多有理论建树,尤其如金批《西厢》,乃代表中国评点文学的高峰著作之一,与金批《水浒》同为后世之楷模,直接启示了毛声山《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本、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本、《聊斋志异》诸种评点本和《红楼梦》脂砚斋评点本及哈斯宝译评本、三家评本等一系列评论和理论名著的产生,对明清两代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影响巨大而深远。 《西厢记》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也渐得各国研究家的正确评价。如俄国柯尔施主编、瓦西里耶夫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说:“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 日本河竹登志夫的《戏剧概论》将《西厢记》和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印度迦梨陀娑《沙恭达罗》并列为世界古典三大名剧,则从更广阔的世界戏剧史的高度,给《西厢记》以精当的评价。 五、《西厢记》的社会影响: 《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周锡山《西厢记》新论)2001年12月吉林出版社出版)。 《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史上最重要的爱情剧目之一,是“四大爱情戏之首”(另三部是《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艺术上的异常精美成熟,而且还在于它体现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内涵。郭沫若说:“《西厢记》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的而且普遍的生命。”(《郭沫若全集》15卷) 在中国戏曲史上,有些戏曲名著,并不一定是文学名著,而《西厢记》既是戏曲名著,又是文学名著。“如果有人问,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剧作是哪几部?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应是《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王季思《四大名剧》,岳麓书社1992年第1版) 《西厢记》是元代戏剧中的最高成就,是中国第一部才子佳人的作品,是中国第一部舞台喜剧。 元代,关汉卿和王实甫被誉为元代的双子星座,若以单个作家论,关汉卿最富开创性,有奠基意义,贡献卓著;若是以单部作品论,《西厢记》是元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被金圣叹称为“第六才子书”,金批本大约完成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它与金批《水浒》(称为“第五才子书”)一样,在清一代颇负盛名,妇孺皆耳熟能详,成为《西厢记》诸版本中流传最广,翻印最多的一种。 金批《西厢记》,把它等同于《离骚》《史记》《杜诗》等儒家经典,把它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去评价,这在当时,没有一定的胆识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西厢记》中的张生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知识分子”;崔莺莺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怀春少女”;尤其红娘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登上文学殿堂的“草根”。在中国文学的人物形象中,有两个人是家喻户晓,一个是“孙悟空”,另一个就是《西厢记》中的“红娘”。 《西厢记》的社会影响巨大,它的艺术生命力和舞台生命力特别强。无论是古老剧种、新兴剧种、大剧种、小剧种皆有本戏或折戏被搬上舞台。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承中,有“先西厢,后牡丹,再红楼”之说。“《西厢记》描写的知音互赏式的爱情模式为中国和世界文艺发展史所作出的巨大的首创性的杰出贡献,并引领《牡丹亭》《红楼梦》等取得领先性的杰出艺术成就”。《牡丹亭》是《西厢记》出现三百年之后才出现的,而《红楼梦》则更晚。《红楼梦》中借鉴了大量《西厢记》的描写手法,故有“第二西厢”之说,为此,《西厢记》和《红楼梦》则被誉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无与伦比的“双璧之作”(赵景深《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其文学艺术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无人出其左右。 “其实《西厢记》不仅仅是一部元杂剧,它可以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从这里进去,唐传奇、唐诗、宋词、元杂剧,一气贯穿。元杂剧中取材于唐传奇的当然还有,但是崔莺莺的故事太迷人了,从这个故事中获取资源的创作活动持续了好几百年。更何况《西厢记》文辞之高华优美,几乎登峰造极。”(江晓原:迷恋《西厢记》) 六、《西厢记》历史上在海外的影响: 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是目前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中国戏 曲名著。自1872年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被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以来,至今已有120多年。目前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已有英、法 、德、意、拉丁、俄、日、朝、越等文种的译本。在日本,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译成日文竟有8 种版本。 《西厢记》是最早在西方国家公映的中国影片。1927年由黎民伟的民新公司根据王实甫元杂剧改编出品拍摄,由侯曜执导的古装无声片《西厢记》是目前留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古装电影。1928年夏天,该片在巴黎公映。 1940年上海国华影业公司再次把《西厢记》搬上电影银幕,由当时的著名电影演员周旋扮演崔莺莺。 《西厢记》赏析 【作品简介】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大都(今北京市)人。他一生写作了14种剧本,《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是他的代表作。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 历史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 【故事起源】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 【故事梗概】 前朝崔相国死了,夫人郑氏携小女崔莺莺,送丈夫灵柩回乡,途中因故受阻,暂住河中府普救寺。这崔莺莺年方十九岁,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所不能。她父亲在世时,就已将她许配给郑氏的侄儿郑尚书之长子郑恒。 小姐与红娘到殿外玩耍,碰巧遇到书生张珙。张珙本是西洛人,是礼部尚书之子,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他只身一人赴京城赶考,路过此地,忽然想起他的八拜之交杜确就在蒲关,于是住了下来。听状元店里的小二哥说,这里有座普救寺,是则天皇后香火院,景致很美,三教九流,过者无不瞻仰。 这张生见到莺莺容貌俊俏,赞叹道:“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为能多见上几面,便与侍中方丈借宿,他便住进西厢房。 一日,崔老夫人为亡夫做道场,这崔老夫妻人治家很严,道场内外没有一个男子出入,张生硬着头皮溜进去。这时斋供道场都完备好了,该夫人和小姐进香了,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张生想:“小姐是一女子,尚有报父母之心;小生湖海飘零数年,自父母下世之后,并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报。” 张生从和尚那知道莺莺小姐每夜都到花园内烧香。夜深人静,月朗风清,僧众都睡着了,张生来到后花园内,偷看小姐烧香。随即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也随即和了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张生夜夜苦读,感动了小姐崔莺莺,她对张生即生爱慕之情。 叛将孙飞虎听说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便率领五千人马,将普救寺层层围住,限老夫人三日之内交出莺莺做他的“压寨夫人”,大家束手无策。这崔莺莺倒是位刚烈女子,她宁可死了,也不愿被那贼人抢了去。危急之中夫人声言:“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就将小姐许配给他。”张生的八拜之交杜确,乃武状元,任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镇守蒲关。张生先用缓兵之计,稳住孙飞虎,然后写了一封书信给杜确,让他派兵前来,打退孙飞虎。惠明和尚下山去送信,三日后,杜确的救兵到了,打退孙飞虎。 崔老夫人在酬谢席上以莺莺以许配郑恒为由,让张生与崔莺莺结拜为兄妹,并厚赠金帛,让张生另择佳偶,这使张生和莺莺都很痛苦。看到这些,丫寰红娘安排他们相会。夜晚张生弹琴向莺莺表白自己的相思之苦,莺莺也向张生倾吐爱慕之情。 自那日听琴之后,多日不见莺莺,张生害了相思病,趁红娘探病之机,托她捎信给莺莺,莺莺回信约张生月下相会。夜晚,小姐莺莺在后花园弹琴,张生听到琴声,攀上墙头一看,是莺莺在弹琴。急欲与小姐相见,便翻墙而入,莺莺见他翻墙而入,反怪他行为下流,发警再不见他,致使张生病情愈发严重。莺莺借探病为名,到张生房中与他幽会。 老夫人看莺莺这些日子神情晃惚,言语不清,行为古怪,便怀疑他与张生有越轨行为。于是叫来红娘逼问,红娘无奈,只得如实说来。红娘向老夫人替小姐和张生求情,并说这不是张生、小姐和红娘的罪过,而是老夫人的过错,老夫人不该言而不信,让张生与小姐兄妹相称。 老夫人无奈,告诉张生如果想娶莺莺小姐,必须进京赶考取得功名方可。莺莺小姐在十里长亭摆下筵席为张生送行,她再三叮嘱张生休要“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长亭送别后,张生行至草桥店,梦中与莺莺相会,醒来不胜惆怅。 张生考得状元,写信向莺莺报喜。这时郑恒又一次来到普救寺,捏造谎言说张生已被卫尚书招为东床佳婿。于是崔夫人再次将小姐许给郑恒,并决定择吉日完婚。恰巧成亲之日,张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归来,征西大元帅杜确也来祝贺。真相大白,郑恒羞愧难言,含恨自尽,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 【历史沿革】 唐代以后,这个爱情故事的结局,令许多人感到遗憾和不满,斥责张生为“薄情年少如飞絮”。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将结局改变,宋代以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和汉族同化,封建礼法观念在普通人民中间逐渐淡化,金代出现了董良(一说为董琅)所写的诸宫词《西厢记》,诸宫词是当时的一种说唱艺术,类似现代的评弹,用琵琶和筝伴奏,边说边唱。这本《西厢记》将内容大为增加,加入许多人物和场景,最后结局改为张生和莺莺不顾老夫人之命,双双出走投奔白马将军,由其做主完婚。 元代时王实甫基本根据这部诸宫调将《西厢记》改编成多人演出的戏剧剧本,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融合了古典诗词,文学性大大提高,但将结尾改成老夫人妥协,答应其婚事,大团圆结局。这部剧本作者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关汉卿所作,也有人说是关作王续,或王作关续,但认为是王实甫所作的说法比较公认。 【版本历史】 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起凤馆刻本(李贽、王世贞评)、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香雪居刻本(王骥德、徐渭注,沈景评)、明万历间萧腾鸿刻本(陈继儒评)、明天启间乌程凌氏朱墨套印本(凌蒙初校注)、民国五年(1916)贵池刘氏《暖江室汇刻传剧第二种》重刻凌氏本、明崇祯十三年(1640)西陵天章阁刻本(李贽评)、明崇祯间汇锦堂刻本(汤显祖、李贽、徐渭评)、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开明书店排印汲古阁《六十种曲》本。 【所取成就】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相关评价】 《西厢记》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林黛玉的口,称赞它“曲词警人,余香满口”。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牡丹亭》、《红楼梦》都从它那里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 《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认识。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在王实甫之前,金代的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要说到王西厢的成就,就不能不提到董西厢。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名不详,“解元”是金元时代对读书人的敬称。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流传和演变】 《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写的传奇文 短篇小说 《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