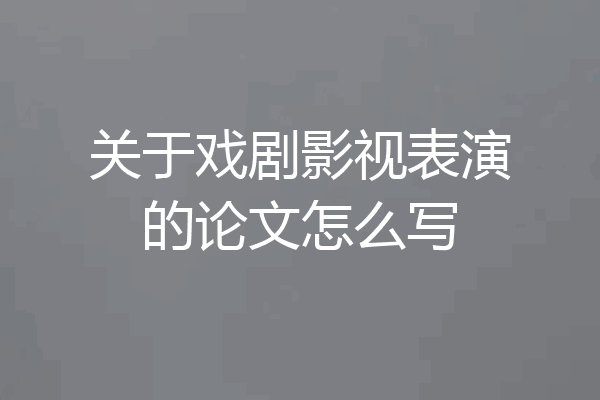哈鲁茶具
哈鲁茶具
四、 必要的修养 通过上面的讲解,相信大家会有这样一个认识:对一部影片的剧作分析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修养之上。 首先,你必须有相当的看片量。一个人如果加起来总共没看过几部影片,就无法展开一部影片与其它影片的比较并对这部影片做出正确的分析了。保证一定的看片量才能了解最新的和全面的电影创作动态和现象,也才能将一部影片放置在大的创作背景和环境下来考察。例如一篇分析《沙鸥》的文章这样说: “尽管《沙鸥》这部影片在今天的观众眼中看来各个方面都显得幼稚了,但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特殊位置是必须肯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的发端之作,是书写在银幕上的宣言。因此,当我们立足于今天对这部影片进行评论的时候,考证它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就比单纯分析它的创作技巧重要得多了。 “‘四人帮’粉碎以后的1979年到1980年,中国电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春潮。其中,《小花》、《小街》、《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等一批中年导演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然而在热热闹闹的创作中,中国的电影人却惊讶地发现,正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由于十年动乱的耽误,中国电影已经与世界电影拉开了距离。尽管这些中年导演从外国优秀影片中学习借鉴了很多对于当时的中国电影说来还很新鲜的表现手法,例如变焦镜头的运用、时空交错式的结构、画外音、高速镜头、通俗唱法的主题歌、旋转镜头、女跑男追……等等,但是渐渐地他们就感觉到盲目地从外国电影中拿来一些皮毛无法解决中国电影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一个是被观众普遍指责的‘不真实’,一个便是电影语言的落后。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影坛的两个年纪已不太年轻的新人——张暖忻、李陀夫妇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作者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呼吁国内同行向外国电影学习,加快中国的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步伐。尽管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对外国电影具体手法的罗列过于琐碎和表面化,缺少系统扎实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但作者的热情和直率还是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激起了中国影坛的轩然大波。这篇文章被后来的人们看作是第四代中国电影导演的宣言,而文章的作者就是《沙鸥》这部影片的编导者。”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把握《沙鸥》剧作特点的时候并没有就《沙鸥》论《沙鸥》,而是把这部影片放在了一个大的创作背景中考察,这就使文章作者得以沉浸在剧作手法的具体细节里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由此可见一个全面客观的剧作分析应该建立在对电影创作发展和现状的全面了解和全盘把握上,这就要求作者随时关注电影创作的现实和动向。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作好一部影片的剧作分析没有相应的剧作理论准备也是不行的。我们来看看上面引述过的分析《沙鸥》的文章中的一个段落: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制定过戏剧必须恪守的规律,他说:‘有人认为,情节之统一,出于只写一个人物,其实不然。因为一人的遭遇可能很多,甚或无数可计,其中有些无法统一;同样,一人的行为可能甚多,其中有些不能构成一件行为。’据此,他认定,只提写‘一个人’是不能保证情节完整性的,必须提‘一件事’。中国清代戏剧家李渔持有同样的观点:‘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又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可是《沙鸥》要打破的偏偏就是这条戒律。在影片中,沙鸥的行为虽然依旧是统一的——努力奋斗,夺取金牌,但是影片却没有拘囿于一个单一事件。也许,作者可以把时空和情节框定在最后一次出国比赛上,然后再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法则有层次地展开这个事件。但是这似乎不合《沙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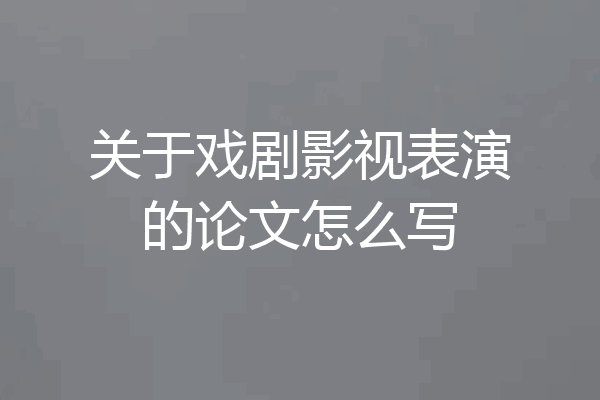
电视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一、视角转换之于电视文化研究的必要主张从多种视角来研究电视文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第一,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落后于迅猛发展的实践。我国电视文化的历史始于20 世纪中期,虽然晚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经济和科技两个高速运转的车轮的驱动下,不仅在传播内容、传播 形式、传播技术上,而且在传播理念与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对电视 文化的理论阐释却尚处于“盲人摸象”式的探索中,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理论 的滞后、理解的偏差又反过来使实践的发展走向误区。第二,电视文化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形态,既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又有商品 的物质性、消费性,既有强制性、操纵性,又有迎合性、对抗性,既有同质性,又有多元性 ,既有类型性,又有创造性;既有娱乐性功能,又有教化功能。电视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一种 跨学科的文化形态,涉及到的领域已远远不是传统的文化艺术所能涵盖的。第三,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以及文化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语境下, 它的商品属性使其由以往的艺术文化转变成一种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新现象、新特征由此 频频凸显。对这些新现象、新特征,尤其是其大众文化特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都使我们产 生一种“莫相知”的恐慌,而没能从理论高度予以阐释。第四,以往的从艺术单一视角对它所进行的理论研究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很多问题,例如 大量不具有审美意义粗制滥造的文本却有很高的收视率、文本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的是声像 光电的技术手段而非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等等,仅从艺术的角度难以解释。在这种复杂的状态下,既要正视电视文化迅猛发展的事实,承认电视文化所蕴涵的商业文 化、大众文化特性,以历史的理性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赋予文化转型的可能; 又要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的把握、理性的认识,恰当的评价,审理各种理解的 偏差,以期更有效地规范和引导这种新型的文化形态。二、电视文化研究的几种视角多重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对电视文化的多重认识,有助于在矫正操作的失误和寻找正确 的发展方向时获得理论上的高度与支持。社会文化视角:以往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忽略了这一文化活动的社 会过程全身。随着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演变,电视文化已走出象牙塔,融入广大民众真实生 动的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品格。作 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社会公共事业,社会学视角、人类文化学视角的关注,也 许能使我们穿越数量众多庞杂、质量良莠不齐的电视文本,抵达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剖析 。在这其中,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尤为重要,因为一切文化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 代码”。从马克思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说、文化研究学派、后现代主义,意识 形态批评无不是这些理论的重心。大众文化视角:电视文化所表现出的商业性、消费性、大众娱乐性、通俗性(甚至媚俗性) 、技术性、可复制性、程式化、无深度感正是大众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体现出与电视文 化与大众文化的一致性、同质性。因此,在对电视文化的研究中,借鉴西方某些学术思潮对 大众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虽不能祈望彻底解决中国电视文化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无益的。 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使我们认识到电子传播作为生产力给对电视文化生产带 来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技术进步对人造成的新的控制,认识到其意识形态 的操纵性、欺骗性的一面;后现代主义理论让我们对电视文化的世俗性、扁平性、游戏性、 狂欢化获得了一种哲学上的认识高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则令我们对电视文化、大众文化中的 全球化倾向、文化同质化倾向保持高度警惕;新历史主义提醒我们,以“戏说”为代表的电 视 文化可能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危险;文化研究学派以它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和跨学科的学术胆 识,启示我们以宏观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微观的文本研究相结合,在微观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 展开宏观的文化研究……这些理论奠定了以大众文化的视角来审理电视文化的理论基础。
浅谈话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话剧是舞台的艺术,是将宽广的现实生活抽象、浓缩到一个小小的舞台上。布景、灯光、道具等一切舞台元素的设计,都不是为了在舞台上复制真实的生活,而是创造一个经过了抽象和浓缩的生活场景。夸张和渲染,让舞台上的生活场景迥异于真实的生活,但将这夸张的场景设置在剧场这个特殊的建筑形式中,并用“第四堵墙”将观众隔离时,舞台上的场景就有了自己的逻辑,没有观众会因为舞台布景的夸张而批评话剧的“真实性”——总而言之,话剧的世界就是一个经过了抽象和浓缩的夸张的世界,演员的表演也势必要融入这个特殊的舞台世界中,与舞台上的情境融为一体。所以,不能照搬真实的生活,而必须表现一种抽象、浓缩之后的生活。 影视表演则是镜头的艺术,最终的成品是经过了摄影和剪辑的渲染的影视作品。影视创作者会通过景别切换、镜头运动等方式,放大剧中的关键信息,让观众随时能够看到必要的信息。影视的空间以实景为主,尽量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总而言之,相对于话剧来说,影视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演员的表演也务必要符合这个真实世界的逻辑。影视表演相对于话剧表演来说,它不需要那么夸张,更接近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和动作。 因为话剧表演具有抽象性和浓缩性,相比真实生活而言,它是夸张、简略的。每一出话剧在编剧阶段就进行了高度的压缩,创作者要仔细推敲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直到把所有的“废话”都剔除干净,以保证呈现给观众的每一刻都包含着必不可少的信息。演员的表演,正是用自己的肢体和语言将这些必不可少的信息表达清楚。所以在话剧表演中,不能含糊其辞、暧昧不清,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都要清清楚楚地呈现给观众,否则会损失剧本的连续性。所以话剧的表演无比要口齿清晰、铿锵有力,情绪低落或高涨的时候,要用比真实生活夸张的动作和语言将饱满的情绪传达出来,这就是话剧表演的分寸。 而影视表演的分寸则以平实为主,镜头会帮助演员呈现动作和表情的种种细节。比如一个吃饭的动作,在话剧表演中,必须夸张地运动脸部肌肉,而在影视表演中,导演会切入一个较小的景别,银幕前地观众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演员脸部肌肉的运动,大快朵颐或细嚼慢咽,只需跟现实生活一致即可。 话剧表演在舞台上进行,它的受众是坐在舞台下的、“第四堵墙”后面的观众。对于剧场中的观众而言,舞台始终是一个整体,想要让他们辨别出该看哪儿、不该看哪儿,则必须通过演员的表演去引导。 影视表演的受众是银幕前的观众,引导他们的目光的是摄影机的景别。演员不必担心自己的表演过于“温吞”,摄影师和剪辑师会通过技术手段让那些日常的动作具备高度的戏剧性。 话剧表演是连续的、一次性的,一旦错误没有修正的余地,所以每一个动作都要经过精心的设计,演员的站位、表情、台词都要事先进行多次排练,直到滚瓜烂熟。这也决定了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不能有一刻松懈,必须集中注意力,全身心地投入角色。 而影视的表演则是片段式的,表演的错误和不到位可以通过在此拍摄来弥补。它的最终目的是将这些“片段”组合成一个整体。所以影视表演在连续性上的要求不如话剧那么高,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演员如何衔接情绪。可能上一场是拍摄婚礼,下一条即是拍摄葬礼,演员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绪中来去自如,这也对演员的“入戏”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虽然有诸多操作上的区别,但话剧表演和影视表演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 首先,无论是话剧表演还是影视表演,都属于表演这一艺术范畴,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塑造一个完整、饱满的角色,以契合剧情的表意。在理解角色方面,话剧表演和影视表演没有区别,都要进行深入的研读和推敲,直到能够体会角色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体验到十分,演出十分,就是好角色;体验到三分,演到十分,就会假大空。 其次,剧作风格决定表演样式。无论是话剧作品,还是影视作品,都有悲剧、喜剧、正剧之分,在不同的剧种中,表演的风格都要做相应的调整。 我国的表演艺术教育以前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造的“斯氏”表演体系为主,斯氏的表演体系注重“体验”,注重由内向外开发角色,先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再把角色的内心世界外化为动作和台词,正如斯氏本人说的那样:“如果说历史世态剧的路线把我们引向外表的现实主义,那么,直觉和情感的路线却把我们引向内心的现实主义”。 我在扮演话剧《那一方灿烂星空》中王庆平一角时,就恪守了这一由内而外的表演原则,对王庆平的内心进行深入的理解,再外化为舞台上的表演。剧中,王庆平要面对大妈、将军、连长、士兵四个个性迥异的人物,我就仔细推敲了王庆平与这些角色关系的疏近,从理解人物关系着手,让我在不同的场次里做到更准确的表演。 影视表演也一样。在电视剧《特战先锋》中,我扮演地下党员“书生”一角。但这个角色不同于以往我们见到的大义凛然的革命工作者,他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总是收敛起自己的智慧,用“若愚”演绎“大智”。在仔细地推敲了角色的所思所想之后,我决定以“冷幽默”的形式去扮演这个角色,外表寡言冷语,内心机灵、忠诚,最终这个角色获得了观众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