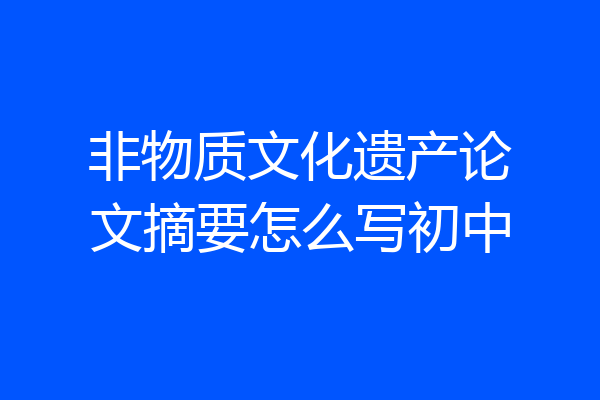nwanggt
nwanggt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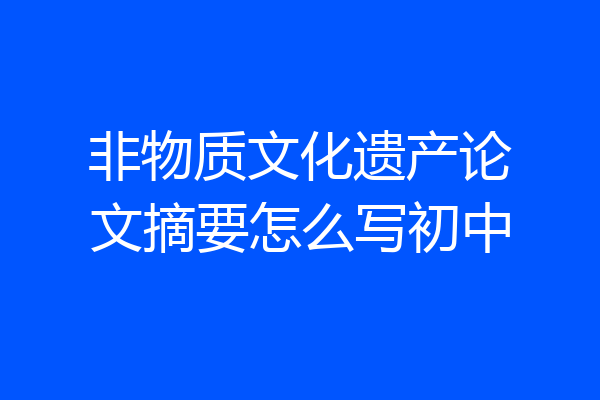
“我们搞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最怕听到的两个词就是打造和开发……”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先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生班开班式上的一句坦言。如乌先生所述,博大精深的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来源于不当开发的巨大威胁。这样的忧虑不仅来源于乌丙安先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老师和著名博物馆学专家苏东海先生也都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了十分相似的担忧。田青老师在其《传统与现代化》主题学术讲座中谈到:“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对传统的极度憎恶中开始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在对传统严酷破坏的基础上开始的。”苏东海先生更是在城市文化研讨会上明确指出:“城市的高速建设将会导致文化遗产的快速消失”。面对诸位先生前辈的担忧和感叹,作为一名文化遗产工作者,我们不得不十分谨慎的重新审视各种形式的“打造”、“开发”与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禁要问一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真的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一、不同角度的不同观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至今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的具有知识性、技艺性和技能性的文化事项。比如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节日、传统仪式和生产生活知识等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漫长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面对这笔巨大的文化财富站在不同的角度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 站在遗产工作者的角度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妥善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客观认识历史、开展文化创新、保护文化多样性、重建社会秩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有实物形态,使其较之有形的文物(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在识别、保护方面都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又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性,也使其在历史变革与时代冲击时比有形文物更加脆弱,比有形文物更容易消逝。正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上的这种困难性和其本身的这种脆弱性,对它的保护才显得更加的急需和紧迫。 站在旅游和经济工作者的角度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民留给今人和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当鼓励各方对非物质遗产的活用,从民俗表演到旅游开发,从工艺品销售到文化创意发展,多手段全方位的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民族艺术的同时也为开发人文旅游景观、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开发破坏和保护桎梏 前文的两种观点看似有较大的分歧,但细细想来却各有其合理之处。笔者认为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保护遗产与开发遗产同样都可以对遗产传承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基于不同的认识往往会引发不同的行动,对遗产、对社会、对国家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不论是遗产工作者还是经济工作者,面对祖先遗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我们心态正常、方法得当,不论是保护行动还是开发行动都会是对遗产有利的活动,但如果不能端正心态或使用不正常的方法则往往会给珍贵的文化遗产造成一些不良影响有些甚至是不可消除的。 1、开发破坏损害遗产 开发活用非物质遗产本无可厚非,但是在最近我们却总能听到因为开发活用不当给遗产造成不良影响的例子。从民乐改良增加交响乐指挥,到邦子演员穿上歌剧演出服,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开发者热情过高,又不了解遗产的文化内涵,在开发的过程中盲目的追大求全,导致经过“开发”的文化遗产已经失去了应有的韵味。民间小戏像京剧大戏,民族音乐像西方交响乐。本来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快速的向主流文化和西方文化趋同,而文化趋同的过程往往正是文化遗产消失的过程。从云南石林的天天“三月三”,到民俗村里的随意“拉郎配”,我们又发现一些开发者只看到了遗产之中的经济价值,对于文化遗产背后的文化价值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开发过后的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分离,文化遗产中蕴藏的风俗、信仰反而在文化遗产保护大潮中快速消失,如此一来经济开发也就成了经济糟蹋。 2、过度保护桎梏社会 经济开发可能给遗产造成开发性的破坏,这一点也许不难理解。但是仅仅按照遗产保护的工作规范对遗产进行保护就完全利于遗产发展吗?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尽然。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遗产,它需要由传承人代代相传,随着时代的变迁,传承人所生活的社会也不断发展,遗产也会发生变化。如果遗产工作者仅是教条、机械的对遗产进行保护,不注意随着社会发展改变保护手段,并且总是希望遗产处于一个历史的时间点,与遗产有关的一切都一承不变,那么这种保护就成为了一种过渡的保护。过渡的保护是不现实的,比如我们不能为了保护一个民族地区的民族习俗就让当地的女孩子不去上学,比如我们不能为了保护船工号子就让河流上的航运交通停止使用机械动力而恢复拉纤。像这样的过渡保护往往会桎梏经济甚至是社会的发展,并且也往往不会被社会所接受。 三、合理利用与传承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事项,它也要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论是开发还是保护,只要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也总会变得不切合实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同时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紧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和滥用。”“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这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在这个大方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也似乎并非不可调和。适度的保护与合理的开发会相辅相成的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但在适度保护与合理开发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要点值得注意: 1、 不能将开发置于保护的对立面上 要走出保护与开发“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怪圈,保护可以是为了开发而保护,开发也可以是为了保护而开发。不能盲目的将开发置于保护的对立面上,单纯为了保护而禁止开发或为了开发而拒绝保护。开发者要有效利用保护者的工作成果,依照文化传统进行传承性的开发,而保护者则应当针对开发者的工作给出有效建议,以便开发工作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 2、 可以利用遗产开发当代文化产品但要与遗产加以区分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来源于民间,来源于生活并非为表演和旅游而设计,在需要进行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时就难免会对遗产的部分内容进行变更,比如为了增强视觉效果在民间戏剧中加入声光电元素,为了增强音响效果在民间音乐中加入新式乐器的伴奏,为了提高制作效率在民间手工艺制作过程中加入现代工艺等等,经过这样的变更原本非为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需要的文化遗产,就成为了一种既具有全新形式,又带有遗产元素,适合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的当代文化创意产品。为了经济开发需要而利用传统文化遗产开发当代文化创意产品是应当给予支持的,因为它一方面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遗产的社会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当代文化创意产品应当在推广时与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区分,让当代创意产品的受众对于其改动内容有明确的认识,防止对于遗产的误解。 3、 要允许遗产的自然发展但不能人为干预其发展 如前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的遗产,需要由传承人代代相传,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传承人所生活的社会不断发展,遗产也会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比如在部分传统的苗族村落,火把节中的火把早已被工业文明的手电所取代;又比如在部分原来生产力落后民族地区,随着先进生产工具,人们已经在一些传统手工艺使用原来没有的电动工具。这些都是遗产的自然发展,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对此遗产工作者要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不能过度的干预。但是文化遗产的自然发展也要尊重自然归律,不能人为的“拔苗助长”加速其变化,防止“邦子演员穿上歌剧演出服”的闹剧重演,防止对于遗产的歪曲。 4、 通过科学记录的方式保护遗产的现状并努力保护遗产的活态传承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生产力不发达的民族地区和农村,当今在这些地方正发生着快速的社会变革。在社会变革中人们思考的往往不是如何保护文化遗产,而是如何摆脱落后文化的束缚。当他们有朝一日过上他们盼望的“幸福生活”时,他们会发现他们的传统文化已经消逝,一些与时代发展“不适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亡。面对这种情况遗产工作者不可能人为的阻碍社会变革,让遗产的传承人选择他们不愿接受的生活。我们应该做的是积极的通过多媒体的科学记录方式保护对于遗产记忆,通过收集与遗产有关的作品、工具保护遗产的现状,并通过改善传承人生活状态努力保护遗产的活态传承。尽可能真实的保持文化遗产的原貌,让后人更加真切的了解遗产的全貌,防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于遗产的滥用。 看到今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领域中保护与开发之间的辩驳,使我不禁想起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一面是具有悠久历史又现实岌岌可危的文物建筑,另一面是生活在近乎是危房的文物建筑中渴望改变生活又经济拮据的居民,面对这一对矛盾,因为我们的一些城市管理者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些文物建筑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一些曾经的文化名城正在变成与西方大都市面貌相仿的“水泥森林”。面对这一切,我想说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再也不能走文物保护、旧城保护的老路,要从开始就做好规划。特别是我们这些遗产工作者更是不能愧对这份历史的重托。 1949年解放军解放北平之前,曾向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求教,让他在北京城地图中划出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人民解放军会对把这些建筑视为雷池禁区一样绝不加以破坏,在战争中对这些建筑的所在区域宁可增强伤亡,也要用步枪、用手榴弹去打,决不使用炮击。58年后的今天,这个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而我们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正是要拿出58年前梁思成先生的气度为我们国家文化建设标出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雷池禁区。而我们的领导干部也应当拿出58年前人民解放军的风骨,宁可花费更大的成本,也绝不破坏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愧对历史,愧对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