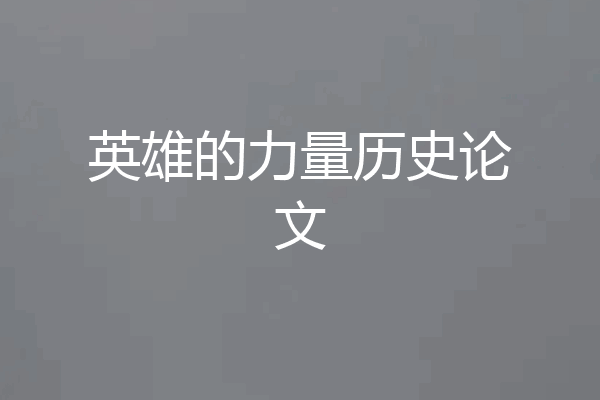hmhhzkd85
hmhhzkd85
论英雄材料:一, 何人是英雄? 谈到英雄,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马上想起曹操与刘备煮梅论英雄的故事。当年刘备臣属曹操。一日,曹操邀刘备赴宴,席间评论起天下英雄。刘备举出当世握有重兵,雄居一方的各位诸侯,称他们为英雄。但是都被曹操嗤之以鼻。曹操举出这些人各自的弱点,认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英雄,当世的英雄只有曹操本人,和面前的这位出身布衣,目前还寄人篱下的刘备。刘备一听大惊失色,酒杯落于地。这时天上正响一巨雷,刘备趁机掩饰说,因惧雷而落杯。曹操听了便轻视了刘备,后来终于让刘备寻机脱身,后来三分天下。 这曹操的眼光确实利害。天下众多有权有势的豪杰在他眼里不屑一顾。但偏偏看出这位刘备将来的成就无可限量。而且竟被他说中。他与刘备论英雄,就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刘备被捧为英雄,不但未喜,反而大惊落杯。因为他知道曹操妒才,必然会除掉他,才故意示弱。曹操还是被蒙骗过去,是曹操的疏忽呢?还是刘备命不该绝? 以这个故事开头,因为它带出了本文的主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是英雄?在对英雄们研究过以后,希望能够发现出规律:如何才能成为英雄。 古人说,美女爱英雄。其实,哪个不崇拜英雄?哪个不敬仰英雄?哪个不希望自己就是英雄。但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英雄呢? 自古以来,对英雄的定义没有统一说法。而时代变了,古人说的英雄同今天人说的英雄又有很多区别。比如,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个士兵炸毁了敌人几辆坦克,马上就成了英雄。一个清洁工扫地几十年,突然哪一天做了什么好事被发现,也成了英雄。在现代社会里,英雄的概念比较广阔。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从历史的角度谈古代那种英雄的概念。 本文要讨论的英雄是指曹操谈的那种有远大抱负的豪杰之士,“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那些能够一呼百应、叱吒风云、万民敬仰、天下归心、文能定国、武能安邦,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发挥英雄本色,建功立业的人才可以称为英雄。 二,何时出英雄? 既然要安邦定国,那么就要有邦让英雄来安,有国让英雄来定。如果是一个太平盛世,英雄也会磨去锐气。马卸鞍,刀入库,边疆烽烟不起,处处莺歌燕舞。和平会腐朽人的志气。所以,中国有句名言,叫“乱世出英雄”。也就是说,在乱世里才会出现英雄。 这是因为,在乱世里,或者因外力入侵,或者因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减弱,各地诸侯于是雄踞一方,而且互相之间争抢地盘,变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在乱世里,各级政府对土匪的征剿也无力进行,于是一些土匪豪强也纷纷召兵买马,拉山头,攻城掠地。这些人中也有发达而成群雄之一的。 在乱世中,百姓饱受战争的蹂躏,颠沛流离,背乡离井,因此希望伟人出世,能够平定天下,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人就是受民众崇拜敬仰的英雄。所以,乱世之中才更有机会出现英雄。 三, 盛世无英雄 如此一来,岂不是说大家都来盼望乱世,好有机会一试身手,显出英雄本色吗?非也。和平盛世虽然会腐蚀人,但总比乱世好。所以,为国为民着想,不能希望乱世,更不能去破坏和平,制造动乱。为满足自己成名的欲望,而妖言乱世,蛊惑民众者,乃是人民的公敌。所以,想成为英雄的人不可因急功近利而误入歧途。要知道,定力也是检验英雄的一个标准。 这里就又要用到中国的一句古话了,叫“英雄待时而动”。在盛世之中,英雄就必须遏制自己的成名欲望。他们应该一方面增加自己的实力,以备未来之需;另一方面要热爱和享受生活的乐趣;如果没有机会施展身手,正应该为天下太平而庆贺。不能为一己之私而害天下。 所以,时机不对,就不要出头。没有机会,就不要盲动。保持实力,待时而动是英雄们必须学会的一门功夫。古人曾以龙来喻英雄:“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京戏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唱词:“有朝一日风雷动,平步青云上九重。”这就是英雄待时时的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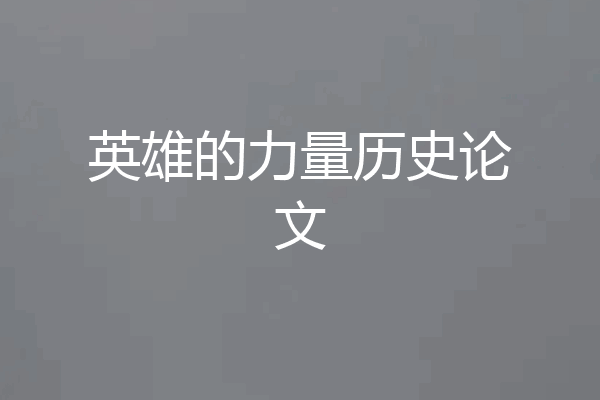
“英雄崇拜情结”及其悲剧 谁是英雄?不同的时代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果我们抖去历史的尘封,翻开一部厚重的中华民族史,认真地作一次追本溯源的巡礼,这对于理解我们的主题将是很有益处的。 通常讲中华民族史,大都习惯于从人文初祖炎、黄以降的“五帝时代”开始,那也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发议论吧。 “五帝时代”被称之为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时代”,因为在这时,我们的祖先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与大自然和周边其他民族的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巨人般的英雄。今天的人们肯定要问,这一时代的英雄都是些什么样的英雄?那时侯的人们对他们面前的英雄怀着什么样的感情?这显然是些并非尽人皆知却又十分有趣的问题。对此,我们还是让古人来回答这个问题更好,古人说: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 这段珍贵的史料为我们保留了什么有关的信息呢?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 我们民族的“英雄崇拜情结”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末期。 二、 这时的英雄,都是与本氏族成员同血缘的人物,“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即外族的英雄一律被排除其外。 三、 这时的英雄,都是些对本氏族有突出贡献的人,他们不是发明家,就是劳动能手,不是战斗英雄,就是治水专家,等等。 总之,“英雄时代”的英雄与后世那些令人望而生畏,莫敢仰视的英雄们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这些处在“天下为公”这种特殊社会环境中的英雄人物,按照氏族社会的惯例,无一例外都必须来自民众,必须经过氏族成员的考验和民主推举,必须尊重民众的选择,成为英雄之后,还必须回到民众中去,事事走在民众的前面,并且不断地作出更为突出的业绩,否则就会在民众的“选贤举能”中被无情地淘汰,也就是说,英雄的命运掌握在民众的手中。 “五帝时代”最后一位氏族领袖,治水的英雄大禹就是这样一个最突出的人物0。当华夏民族面临黄河这条桀骜不驯的巨龙疯狂肆虐而命运岌岌可危时,大禹——这位由民众推举出来的氏族领袖,毅然率领全体氏族成员,劈波斩浪,因势利导,与滔滔的洪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坚苦卓绝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大禹这位民众的领袖时时站在民众之中,走在治水队伍的最前列,“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跋,颈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为了社会的公益和民众的福祉,他确实称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不过,悲剧的帷幕从此也就徐徐拉开了。 治水的成功,使大禹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大英雄。民众向他欢呼,四夷向他膜拜,以此来表达对他的爱戴和景仰之情,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有谁知道,就在人们陶醉于对英雄的欢呼和膜拜的狂热气氛之际,英雄的形象便被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夸张了,严重的扭曲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场威胁我们民族生存的大洪水似乎仅仅是靠大禹个人超人的智慧和力量才被击退的,那些跟在他后面的成千上万的治水民众似乎可以缩小为可有可无的陪衬。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会很自然地问,同样是治水,鲧带领着成千上万的民众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呢?可见民众确是可有可无的陪衬,而真正的英雄才是一个民族亟需的救世主!于是英雄的神话产生了:“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在神话中,治水的成功被说成是大禹具有指挥应龙的超自然的神力;与此同时,治水的广大民众却被治水的神话一笔抹杀,淹没在历史的黑暗中。借助于神话,从此大禹便从民众之中脱离出来,逐渐成为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万民仰视的民族之神! 我们要问,是谁制造了英雄的神话?最初,肯定地说是民众。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英雄的神话呢?因为他们需要英雄的神话。当氏族社会的民众还不可能认识到英雄那超人的意志和力量本该是自己的属性时,他们就必然渴望一个能够体现自己意志和力量的英雄横空出世,跪拜在他的面前,以便换取他们所最需要的安全感,这是“英雄崇拜情结”产生的最主要的社会根源。 那么,此时的英雄又是怎样对待民众崇拜的呢? 据先秦古书《吕氏春秋·当务篇》记载说:“禹有淫湎之意。”结合其它的史料,我们觉得《吕氏春秋》的话是可信的。治水的成功,民众的崇拜,权力的集中,地位的上升,很容易使大禹飘飘然,忘乎所以,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最终导致与民众的彻底分离,成为居于民众之上的至高主宰。这点,首先表现在他对手中权力的运用上,治水成功后的大禹在处理事情上就不那么民主了,据另一本先秦古书《国语·鲁语上》记载:“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在当时,这实在是空前反常的惊人之举!要知道在氏族社会中,按其习惯法,对违反氏族社会行为规范的最严厉的惩罚也不过是流放而已,但现在大禹竟然利用手中的权力,未经氏族全体成员的同意,轻易地杀掉了一个部落的酋长。可见,英雄崇拜的结果,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权力的滥用,防风氏仅是“英雄崇拜情结”的第一个牺牲品罢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要知道,权力的滥用必然导致权力的独占倾向,因为越是尝到滥用权力甜头的人物就越急切地希望独占权力。在氏族社会末期,氏族显贵出现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民众赋予他们的权力永远据为己有,大禹又何尝不是这样!否则又怎能有历史上“夏传子,家天下”的沧桑巨变呢?总之,大禹死后,社会的最高权力落到了大禹的儿子启的手中。他靠什么作到这一点的呢?当然不是靠氏族传统的“选贤举能”的的“禅让制”。而是靠着家族显赫的地位和赤裸裸的暴力抢夺! 问题是广大民众居然容了这种严重“违法”的行为!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中华民族当时正处于由“天下为公”的“野蛮时代”向“天下为私”的“文明时代”作结构性整体转型的关键时刻,新与旧,公与私,野蛮与文明,民主与专制的激烈冲突此起彼伏,并错综复杂的纠结在一起,而这种前所未有的冲突又必然在广大民众内心深处造成难以抑制的焦虑、忧患和骚动不安,于是,“英雄崇拜情结”就开始作怪了,此时,无所适从的民众再次渴望一个大禹式的英雄能够耸立在他们的前面,把他们尽快带出眼前黑暗的混沌中。他们一相情愿地以为,既然大禹曾经拯救过他们,那么,大禹的儿子肯定也会具有如此神通广大的法力,就这样,在历史的最关键时刻,广大民众站到了大禹的儿子启这边来。 然而,广大民众这次却为自己这一虚幻的“英雄崇拜情结”付出了万劫不复的惨痛代价!人类的走过的路无情地告诉我们:每当民众将自己的命运寄托给某个救世主式的英雄时,他们得到的并非是他们所渴望的拯救和解放,而是奴役和枷锁!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阶级社会的第一个英雄——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铁的事实证明,他不过是个“淫溢康乐”?,动辄就向民众吼叫道“予则孥戮汝”?的无耻君王。顺天应人搞“革命”的汤、武又如何?他们也无非把奴隶主的千年大厦砌得更牢固。事情怎么会闹到这样的地步?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主要的则应该是,阶级社会的英雄与氏族社会的英雄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不是发明家,不是劳动能手,不是战斗英雄,更不是治水专家,等等,而是些私欲膨胀,野心勃勃的政治、军事强人,自从这些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社会生活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始的公有变而为私有;民主变而为专制,社会公仆变而为专制帝王,社会主人变而为被奴役的奴隶。一句话,一切皆变,遗憾的是只有民众的“英雄崇拜情结”非但没变,反而越发的浓烈! 原因何在?这里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当这些阶级社会的英雄登上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之后,我们民族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在“兴”、“亡”这两极之间进行周期性的恶性震荡了,于是乎,无权的广大民众便一次次在劫难逃地陷入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灾难深渊中去!试想那些手无寸权的纭纭众生,当此漫漫长夜,能不翘首以盼救世的英雄降临人间吗?中国有句尽人皆知的老话,叫作“乱世出英雄”,这句话再直白不过地折射出中国人灵魂深处的“英雄崇拜情节”了。所以,每逢神州大地沧海横流之际,倍受血与火煎熬的人们都会心急如焚地互相追问:救世的英雄何时横空出世? 春秋战国时代,我们民族第一次陆沉于五百余年的大动乱之中,面对着“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妻离散,莫保其命”?的空前大劫难,此时此刻,包括我们民族的精英如老子、孔子以及其他先秦诸子在内的所有人,不都在不约而同地呼唤着救世英雄的出世吗? 老子故作深邃地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孔子喟然长叹地说::“甚也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孟子坚定不移地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荀子则焦急期待地说:只有一个“庶人隐窜,莫敢仰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的“绝对圣王”才能收拾眼前这个支离破碎的旧乾坤。 而他的高足弟子韩非更十分肯定地说:这个“绝对圣王”不是什么别人,而是一个深知“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的独裁君王。 在这里,只有庄子发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呐喊。 可是在一片甚嚣尘上的英雄崇拜声浪中,他的呐喊又有谁愿意倾听呢?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尚且如此,又何况广大无知无识的民众了。 为了让这个“绝对圣王”降临人间,战国时代的民众忍受着战争的蹂躏、死亡的威胁、饥饿的折磨、赋役的重压,一代代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这个即将降临的“绝对圣王”铺垫一条铁血之路。 人们呼唤的英雄终于降临人间了,他不是别人,此人就是横扫六合,一清海内的铁腕君王秦始皇。他给望眼欲穿的民众究竟带来了什么?据他说,他给民众带来了和平与福祉,带来了“黎庶无徭,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的理想生活。可转眼之间,这位以功超“五帝”自诩的大英雄却原形毕露,他“虏使其民”,去修陵墓,开驰道,造宫殿,筑长城,征匈奴,打南越,巡游天下,求仙长生……,然而他就是忘记了民众该怎么活着!原因十分简单,他认为“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原来如此!为此,他可以把秦帝国变成人间地狱,可以把民众推到绝境,可以把民众逼得揭竿而起,可以把社会抛到新一轮的大劫难中。 对于民众来说,夏启、秦始皇之流的英雄太让他们失望了。但这并没有泯灭他们寻找真正英雄的强烈愿望,他们总以为只要找到一个真正的英雄,他们就会获得彻底解放。于是他们去找刘邦,去找刘秀,去找唐宗宋祖……;本族的英雄让人失望,他们也顾不得“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的祖训”了,就跑去找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这类外族的英雄。 但这些英雄何曾把民众放在眼里,因为是你们求我啊!英雄的江山哪里来的?他们心里明知是用千百万民众的尸骨换来的。但为了把江山变为私产,为了不去回报民众惨痛的牺牲,为了给自己头顶带上神圣的光环,为了让民众更加驯顺的匍匐在地,任其驱使,于是这些英雄编制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神话,(请注意,氏族社会的英雄神话出自民众,而阶级社会的政治神话却是英雄们自己伪造的。)这些政治神话无论多么光怪陆离,却都离不开一个主题:他们是“受命于天”的龙种,他们是救世主,他们是历史大舞台的主角,而民众永远是舞台下的看客! 中国的悲剧就在这里。由于民众被专制政治无情地剥夺了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权力,久而久之也就丧失了表演的能力,熄灭了表演的欲望。别无它策,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交给几个在政治大舞台上来去匆匆的大小角色去摆布。这点也就注定了中国的看客们对上演的节目的特殊选择:他们不喜欢看生活戏,因为生活够平凡、够悲苦的了;他们也不喜欢看域外戏,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过得虽然不好,但比别人可强多了。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英雄戏”,看起来最过瘾,最来情绪!一旦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没有了值得叫人喝彩、叫人激动、叫人为他而豁出命来的“大英雄”角色,中国的看客们就会感到百无聊赖,感到世界失去了希望和重心,这时,他们无不认为必须再捧红一个“英雄”,让他雄赳赳,气昂昂地杀上这个大舞台,占据舞台的中央,自己却宁愿跟着跑龙套,把抛头颅,撒鲜血夺来的江山拱手献给几个与自己出身同样微贱的政治、军事强人,为的是让自己喜闻乐见的“英雄戏”继续演下去。一个西方人说“没有英雄的国家固然不幸,然而需要英雄的国家更不幸。”?遗憾的是中国人很难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他们始终需要英雄,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英雄”,特别在陷入绝境时更是? 绱恕?nbsp; 难道我们民族中就没有头脑清醒者吗?有。除了战国时代的思想大师庄子之外,反暴政的农民领袖陈胜不是曾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最强音吗?西晋时代的思想家、诗人阮籍不是也曾指着司马氏这群窃国大盗,愤然地骂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吗?到了蒙古人统治的元朝,知识分子在这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异族统治者的铁蹄下,陡然由昔日的社会精英堕入到连妓女都不如的“臭老九”的恶境。不过,这种恶境反倒锻炼了他们所缺乏的反思能力,促使他们冲破了“英雄崇拜情结”的羁绊,看透了英雄的本相。元人张鸣善在他的《[双调]水仙子·讥时》小令中,用一种揶揄的语调对历史上的英雄嘲讽到: “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角猫渭水飞熊。” 可惜的是,以上的真知卓见尚属偶然的思想闪光。能够真正从理论上破除“英雄崇拜情结”的人物,当属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他写了一本《明夷待访录》的奇书,此书被专制统治者视为势在必禁的异端邪说,所以如此,就是由于黄宗羲身当神州陆沉、蛮夷滑夏的亡国巨变,痛定思痛,使其思想境界终于超越了传统的忠君爱国的狭小天下,将其目光准确地投向数千年来不断产生“乱世 雄”的君主极权政治制度上来。在深沉的反思中,他勇敢地喊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那么这些以“内圣外王”自许的专制君主之“大害”何在?黄宗羲进而鞭辟入里地指出,这些家伙: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可悲的是,历史上少数志士仁人振聋发聩的大声疾呼并未唤醒我们民族那麻木的整体意识,因此他们的思想闪光也难以点燃我们民族的启蒙之火,更谈不上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涤荡旧思想的启蒙运动了。因为我们民族类似于“英雄崇拜情结”的文化积淀实在太深厚了,何况还有一层难以击碎的封建专制主义外壳牢牢地禁锢着它,所以,只好等待强大的世界大潮去冲决它。 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人类的解放只能靠民众自己的力量。过去有人说“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英雄和英雄崇拜》),而我们则要大声说:不,“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 引文
有能力的统治者能够振兴历史,而能力不足的统治者则会阻碍历史的发展。。。。算的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