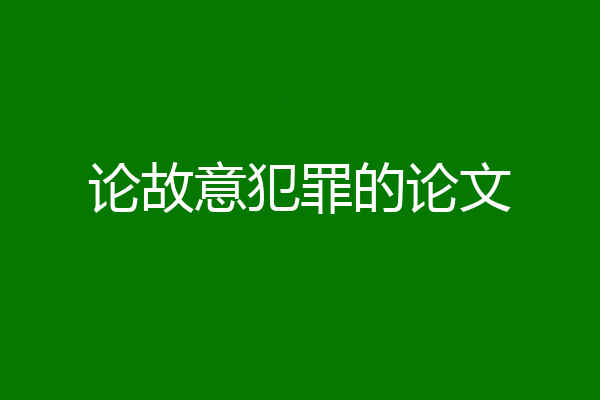nicoleyan
nicoleyan
论犯罪未遂 作为犯罪形态的核心,犯罪未遂一直是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司法实务认定的一个难点。在恢复法制20年间,产生了“构成要件(齐备)说”、“主观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等有代表性的学说。一、犯罪未遂的现论与实践概述“构成要件(齐备)说”以是否全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是否得逞的标准,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实具体犯罪构成的实行行为,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犯罪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犯罪未遂的“未得逞”就是不齐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它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含义:从客观的方面看,“未得逞”是犯罪完成状态下犯罪构成应具备的要件未能齐备;从主观方面看,是犯罪分子希望完成犯罪和齐备犯罪构成全部客观要件即达到既遂状态的犯罪意图未能全部展开和实现。此说从语言分析角度讲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一些学者批评道:行为不齐备犯罪构成要件即不构成犯罪,也就谈不上犯罪未遂。其实,犯罪未遂的特征与未遂的犯罪构成不是一个概念,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完成形态以及未完成形态的犯罪的犯罪构成,都是犯罪的客体、客观、主体和主观这四个方面基本要件的有机统一体。未遂的构成要件本身并不缺乏任何要件,但缺少了某要素。有的学者还用公式作了一个更细致的说明,指出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的基本构成要件并无不同,只是前者在客观方面的行为、结果和因果关系等的发展程度和实现程度上不同。“犯罪目的(实现)说”以犯罪目的的是否达到作为犯罪得逞与否的标志,认为“犯罪未得逞”的含义就是指犯罪目的没有达到。其中又有修正的目的说,主张以行为人追求的、受法律制约的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得逞与否的标志,发生的为既遂,未发生的为未遂。“犯罪结果(发生)说”以犯罪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是否得逞即既遂未遂区别的标志,认为“犯罪未得逞”,就是犯罪行为没有产生法律规定的犯罪结果。“构成要件(齐备)说”被认为较合理地阐明了犯罪未遂的特征,几乎被各院校教材所采用,从而成为理论界通说。但随着犯罪未遂原理在分则具体犯罪运用研究的深入,这一学说受到新的质疑,从而产生了“构成要件充分展开说”和“实行行为达到目的说”。前者以构成要件是否充分展开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认为在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使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充分展开的,是犯罪未遂。后者以实行行为是否达到该行为的直接目的为标准区分既遂与未遂,认为在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后未能达到行为的直接目的的,是犯罪未遂。以上五种观点中的后四种,在理论界均有一定影响,但未能撼动第一种观点的主导地位。然而,今人奇怪的是,理论界对具体犯罪的未遂形态的分析,并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第一种观点,而实务界对具体犯罪的未遂形态的认定,由于实用主交的功种主义的影响,更是五花八门。由于制度、机制、法官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加之学术生产线出来的东西良莠不齐,我们不能奢望学理解释在短期内取得其在德国、日本那样的地位,但司法公正的呼唤、立法与司法已经提供的空间,都要求学术的自省、自律和自我发展。因此,梳理既有观点,分析其间得失,如有可能,再作出必要的推进,也是研究犯罪未遂问题应当进行的工作。二、对现有观点的梳理尽管学界对犯罪未遂问题的探讨一直未曾停止,但实际上通说的整体地位并未动摇,因为争论只是在局部进行。(一)关于犯罪未遂的概念关于犯罪未遂形态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以法国刑法典为模式的未遂概念。即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或障碍,而使犯罪未达到既遂形态的情况。这种主张把因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法定结果发生而未达既遂的情况作为犯罪中止形态,以区别于犯罪未遂。二是以德国刑法典为模式的未遂概念。即犯罪未遂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行犯罪而未达既遂形态的情况。这种主张把犯罪中止形态也包括在犯罪未遂形态中,认为只要犯罪行为已经实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致使犯罪未达到既遂形态的,都是犯罪未遂。只是根据导致犯罪未达到既遂的原因,将犯罪未遂分为两类:行为人因意志以外原因或障碍而未达到既遂的,是障碍未遂;行为人因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而未达到既遂的,是中止未遂。我国现行刑法与旧刑法均以同样的文字,采用法国模式对犯罪未遂作了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一般认为,这是立法对犯罪概念所作的规定,称之为刑法中的犯罪未遂概念。不过学者们更乐意采用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表述作为理论中的犯罪未遂概念。对此并无大的分歧,不过我认为:第一,刑法对犯罪未遂的规定,只是突出了犯罪未遂的主要特征,以形式逻辑的概念标准衡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至少,它缺少被定义项,外延也不周延;第二,由于犯罪形态尤其是犯罪的不完全形态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过失行为无“着手实行”可言,并且过失行为与间接故意行为一样,尚无分则规定的危害结果发生,则不构成犯罪,自无犯罪形态可言,因此,在犯罪未遂概念中应界定“直接故意犯罪”这一外延范围,才能使概念周延。(二)关于犯罪未遂的性质 犯罪未遂究竟是犯罪的一个阶段还是犯罪的一种状态?这是犯罪未遂的性质问题,对此,各国的规定和认识均有不同。由于受《苏俄刑法典》和前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我国八十年代的教科书几乎都将其作为犯罪阶段来研究,从九十年代开始则全部改称“犯罪形态”,至今为止,这一定论已无人再持异议。(三)关于犯罪未遂的分类犯罪未遂的分类,又称犯罪未遂的表现形式,或者说类理、种类,即以一定标准,把犯罪未遂分为若干类型。我国理论界通行的划分标准有两种,一是以危害行为是否实行终了为标准,将犯罪未遂分为实行终了的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未遂。这种标准看似简单明了,但其自身建立的标准是什么,却引出了不同认识。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即有绝对的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前者主张,行为是否实行终了,应以行为人自己的认识为判断标准;客观说认为,行为是否实行终了,是一个客观实际,故应以行为是否足以或已经危害社会为判断标准,后来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一般人对犯罪行为发展程度的客观认识为判断标准。这一概括,我认为有失准确,因为:第一,它不符合客观说主张者原义:第二,人的认识都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并不因认识主体的多寡而改变其主观色彩。也就是说,认识是否客观,不取决于它是个人的认识还是一般人的认识。客观说还有“法律规定说”,主张犯罪分子已经实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行为的是实行终了,否则为未实行终了。折衷说主张,行为是否实行终了,应按照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艰苦既要考虑行为发展的客观情况,又要顾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此说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当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行为发展的客观情况不一致时,究竟考虑和顾及哪一端?修正的主观说在坚持主观说的基础上,对主观说提出了限制性条件,即“犯罪构成行为要件范围内的主观说”。其含义是“在法定犯罪构成要件所限定的客观行为范围内,行为是否终了,应依犯罪分子是否自认为将实现犯罪意图所必要的全部行为都实行完毕为标准。”折衷说昙说一现,未见产生什么影响;绝对主观说的提出者仍坚持原来的观点,并有一定影响。主观说从本质上讲是合理的,因为实行行为全文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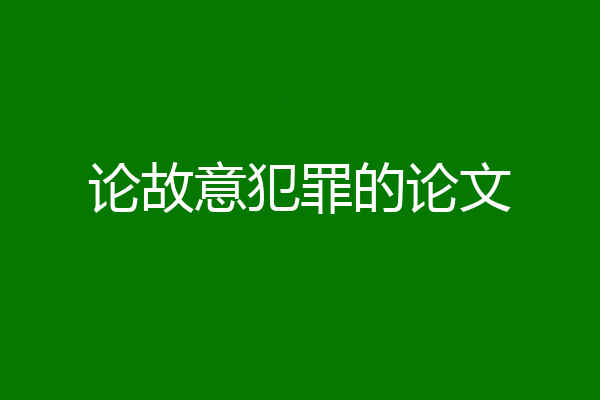
间接故意犯罪形态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实际上这是 个纯理论性的问题,如何于实务中解决这个问题,现有刑法规定并未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当我们已知某种故意犯罪成立,那么这种犯罪主观上是否具备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形态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但,当涉及具体的犯罪时,许多学者却经常忽略了这 点,通常以为这种犯罪是故意犯罪,但只能由间接故意构成。正如笔者在研究刑法第407 条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主观特征时所遇见的问题,大多数学者几乎都持这种观点。由此引发笔者对间接故意的兴趣和思考,究竟问题的症结何在?试申言之。 首先、间接故意内涵的界定 间接故意犯罪类型是否为刑法故意犯罪的规定所含括,刑法第14条明确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 规定揭示了犯罪故意应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部分构成。换言之,行为人能够认知其行为具有社会非难性,同时希望或者放任其行为发生的心态,则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故意。由此可见,刑法规定本身并未将犯罪故意厘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划分完全是 种理论层面上的研究。但探究间接故意的价值取向对犯罪故意理论具有积极的作用勿庸置疑。 间接故意和直接故意的分野源于刑法第14条对行为人意志因素的表述,即'希望或者放任'的心理态度。希望行为危害结果发生为直接故意;放任行为危害结果发生为间接故意。理论界关于间接故意概念的介述基本上援此为据,虽争鸣不甚激烈,但仍然存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其 ,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注;参见高铭暄著;<刑法总则要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127页。)其二,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注;参见王作富著;<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其三, 犯罪的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其行为可能引起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有意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质言之,预见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加以放任,就是间接故意。(注;参见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第167页。) 关于间接故意的涵义,不仅学界的见解不尽相同,各国的刑事立法也不 致。仅有少数国家刑法中明确规定了间接故意的内容,如俄罗斯、台湾地区等;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未作规定,但其中 些国家的刑法能够反映间接故意的内容,如<奥地利刑法>第5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有意实现法定构成之事实且明知其可能实现而予以认许者,为故意。'<澳门刑法>第13条第3 款规定;'明知行为后果可能使符合 罪状之事实发生,而行为人行为时系统受该事实之发生者,亦为故意。'<罗马尼亚刑法>第19条规定的间接故意是;'预见到行为的结果,虽不追求其发生,却接受了该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显然,这些规定并未对行为人的认识程度加以限制。英美法系的学者以为,故意既指希望结果发生的直接或目的之心理状态,也指间接故意。只要证明被告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是'事实上的必然'会造成这些结果,不管是否系故意的,均可成立或推定为'间接'故意。(注;不管是预见到事实上的必然性,还是预见到'极大的可能性',都仅仅是推定故意的证据,只有事实上的必然性,才足以作出这种推定。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大陆法系学者的故意界说多采用容认主义,(注;容认主义,又称为容认说,主张不以仅认识犯罪事实为己足,且亦不以意欲(希望)结果之发生为必要,而系以容认犯罪事实之发生为己足之学说。洪福增;<论故意>,载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1—2期。)普遍以为,凡在目的上实现犯罪事实之发生者,为直接故意;凡容认实现必然的伴随目的行为而发生之恶害者,为准直接故意;凡预见伴随目的之行为可能发生的结果,而予以容认者,为间接故意。(注;参见洪福增著;<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1982年版,第142页。)前苏联学者指出;行为人认识到产生结果的必然性, 则不属于有意识地放任。(注;法律没有把意识到后果的必然性列入故意的某个方式,刑法理论界和刑法实践对认识到后果的必然性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分析犯罪人心理状态的差异会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某人已经意识到了必然会发生某种结果,但他无视这 点,继续实施自己的行为,他在心理上更希望产生这种结果,而不是有意识地放任。根据这种情况,应当把认识到产生结果的必然性看作是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