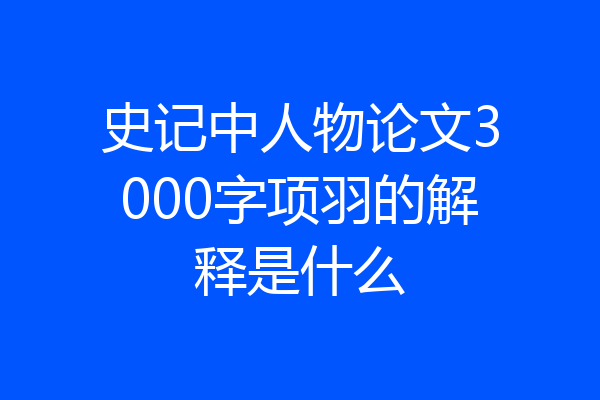颊俏6319
颊俏6319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史记-项羽本纪》。这是《史记》中对于项羽的基本情况的介绍。大意是,项籍是下相人,字羽。项羽开始起事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项羽的叔父是项梁,项梁的父亲是项燕,就是被秦将王翦所杀害的那位楚国大将。项氏世世代代做楚国的大将,被封在项地,所以姓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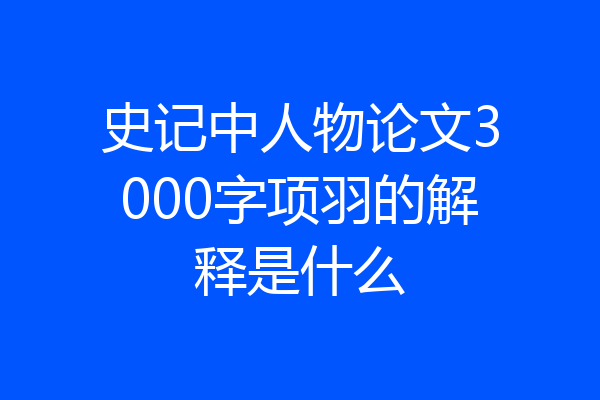
“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手起笔落处,端正凝重,力透人胸臆,直指人脊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不是几个字的精致组合,不是几个词的巧妙润色。是一种精髓的凝练,是一种气魄的承载,是一种所向无惧的人生姿态。那种凛然风骨,浩然正气,充斥天地之间,直令鬼神徒然变色。“当作”之所“亦为”,一个女子啊!纤弱无骨之手,娇柔无力之躯,演绎之柔美,绕指缠心,凄切入骨,细腻感人无以复加。透过她一贯的文笔风格,在她以“婉约派之宗”而著称文坛的光环映彻下。笔端劲力突起,笔锋刚劲显现时,这份刚韧之坚,气势之大,敢问世间须眉几人可以匹敌?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女词人追思那个叫项羽的楚霸枭雄,追随项羽的精神和气节,痛恨宋朝当权者苟且偷安的时政。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仅一河之遥,却是生死之界,仅一念之间,却是存亡之抉。项羽,为了无愧于英雄名节,无愧七尺男儿之身,无愧江东父老所托,以死相报。“不肯”!不是“不能”、不是“不想”、不是“不愿”、不是“不去”。一个“不肯”笔来神韵,强过鬼斧神工,高过天地造化。一种“士可杀不可屈辱”、“死不惧而辱不受”的英雄豪气,漫染纸面,力透纸背。令人叫绝称奇而无复任何言语! 绝句,不是只因其艺术的功力,不是只因文字的机巧,当浩然正气贯于心胸与文学才华浑然一处时,下笔之处,天地惊鬼神泣之力,是缘于她的精神凝聚,气节支撑。 现代文学作品中,有人曾这样的点评项羽,“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为什么身死东城,为天下人笑?他的失败原因‘妇人之仁,匹夫之勇’两句话包括尽了。当其败北之时,如果渡过乌江,卷土重来,尚不知鹿死谁手。而项羽向天长叹:‘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我而王,我何面见之?纵不言,籍独无愧于心?’英雄一世却没能战胜自己的自尊心!放弃了一线生机。” 从作者的切入角度和某个层面上说,我不反对这样的评说,但那只是就其切入角度的层面而言。纵观历史长河之内,英雄无数风流无尽,项羽的慷慨赴死报江东父兄,从容舍身慰男儿之身,如此气节,在他英雄之躯訇然倒地之时,腾空而起,凌云直上,流传千里,摧人至今。宁可无愧而死,不肯惭愧而生,这是项羽之生命换来的抉择之笔,书写着一种忠贞:忠贞于英雄之名,忠贞于大丈夫之气。联想到“霸王之别姬”可见其人文渲染和人格的魅力所至,造就出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慷慨气节、悲壮正气。 李清照本女儿之身。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一个坎坷漂泊的女子,一个沧桑憔悴的女子。笔墨所抒人杰之“杰”,高出众人几层之上;鬼雄之“雄”,豪踞鬼神遍及之处。一个“思”字,标示她的思想所向、志向所指,何等的无畏生死之气。此一绝句在她温香萦绕、弱吟娇叹的文字中,异笔突运,异军突起,这是她另一种的底蕴显露,是她别一种的气质光彩,是亡国之悲忿、爱国之强烈、命运之不屈的铮铮风骨和铿锵见证。 星光灿烂的古典文学长河,群星璀璨无比,这是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一路走过之处,给后人留下的斑斓印记。无法计数的才子佳人以其流光溢彩的才华,在文学史上取得了浓墨重笔书写自己名字的资格。但无论青天白日之下,还是明月当空之时,打开诗词集锦,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绝句,其浩然正气,傲然风骨,总会使人肃然起敬,凝神起思,思而情! 何谓做人风骨,何谓做人气节,从李清照这位以婉约凄美而娇峙文坛的女子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最为精准的答案吧! 提到项羽的精神,不能不去思考下楚人精神,纵观秦帝国灭亡的历史,楚国后裔们当是最大的胜利者,在整个抗秦力量中楚人身影也是令人敬佩的。不屈服,心怀信念,以及对秦国的痛恨。翻看历史,作为盟国,在秦征战其他诸侯国时,楚国没有丝毫疑心,信守承诺,楚最是无辜,最后遗恨而亡,败得糊涂啊。所以当秦军队攻入郢都时,许多楚人纷纷自杀殉国,在生还的楚人中有这样一句经典的传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悲痛的时候立下了惊天泣地的雄心壮志,而且这一传言也通过项羽之手得以验证。也许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精髓吧。
项羽是一位盖世英雄,在秦汉之际的政治舞台上仅仅活动了八个年头,兵败自杀时年仅三十二岁。司马迁考察项羽短暂而非凡的人生,深为项羽的英雄色彩和悲剧性格所感动,全神贯注地刻画了项羽的形象。
《史记·项羽本纪》以“勇”字贯穿始末,“勇”是项羽的基本特点。以灭秦为界,将项羽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描写。前期写他以一己之勇带动天下人之勇,推翻暴秦的统治;后期写他以一己之勇征服天下之勇,结束自己的统治。作品将刻画项羽巨人般的英雄形象和揭示项羽悲剧性格的教训有机地结合起来,项羽的形象不仅极为鲜明生动,而且还意蕴深厚,令人仰慕叹惋,发人无穷深思。
清代吴见思《史记论文》说:“八千人渡江而西,忽化而为二万,六七万,数十万,忽化而为八百余人,百余人,二十八骑,至无一人还。其兴也,如江涌;其亡也,如雪消。令人三叹。”这些数字的变化,说明项羽的神勇在前后两个时期的价值区别。前一个“忽化”说明项羽的神勇不断升值,风云际会,蓬勃兴起;后一个“忽化”说明项羽的神勇不断贬值,众叛亲离,倏然灭亡。
《鸿门宴》中樊哙指责项羽是“亡秦之续耳”,指出了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史记》中两次引用贾谊的《过秦论》,其上篇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作结,中篇指出“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当反秦斗争结束之后,项羽分封诸侯之时,实际上就是“守天下”的开始。项羽缺乏一统天下的政治眼光,不懂“逆取而顺守”的道理,一味迷信于自己的神勇善战,满足于做一个西楚霸王,分封未毕,旋即征讨。文末的论赞明确反对“以力征经营天下”,可见《项羽本纪》的主题与《秦始皇本纪》颇有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项羽形象中表现出了反暴英雄令人崇敬和同情的一面。
《项羽本纪》写作上独具匠心,代表了《史记》传记文学的最高艺术成就。
首先是选材精当,详略分明。第三节文字最为精彩。《项羽本纪》基于对历史本身的深刻认识,选材十分精当,能够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项羽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经历大事颇多,战阵就有七十多次。全面铺开,则显得庞杂。司马迁确认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大事件在项羽一生中极为关键,于是截取这三个重要的横断面,采用多种艺术手法,再现项羽威猛刚强、激昂慷慨、视死如归的壮烈形象,项羽的品格、气质、才识、胆略、武艺等,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他史实穿插其间,补充前因后果,丰富了项羽的完整形象。
其次是在矛盾冲突中展示项羽的英雄本色。钜鹿之战是起义军与秦朝主力军之间的战略大决战,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义军与秦军之间的殊死斗争是主要矛盾,秦朝君臣之间,率军将领与用事权臣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楚军君臣之间,主帅与其他将领之间也存在尖锐的矛盾。作为反秦的战略家,必须具有目无强秦的伟大气魄和正确无误的战略部署。项羽诛杀宋义,排除阻碍反秦斗争的羁绊,解决内部矛盾;随而派遣当阳君、蒲将军率军二万渡河救赵,安定钜鹿城中义军的军心。然后破釜沉舟,大举进军,采用反包围,消灭钜鹿城下的王离军,解除钜鹿之围,随后围歼秦军,迫使章邯投降,秦军随之土崩瓦解。
“鸿门宴”是反秦斗争结束而楚汉之争即将开始时项羽、刘邦两大集团之间的一次交锋,楚汉之争上升为主要矛盾。鸿门宴是楚汉之争的序幕。曹无伤告密,项伯说和并庇护刘邦,分别是刘邦、项羽两大集团的内部矛盾,都是次要矛盾。曹无伤告密激化了主要矛盾,而项伯说和并庇护刘邦,加之樊哙闯帐,怒责项羽,则缓和了主要矛盾。鸿门宴上的刀光剑影,意味着项羽集团的内部矛盾冲淡了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鸿门宴的矛盾冲突与转化,展示出项羽重感情、少城府、憨厚宽容的性格,同时暴露出项羽缺乏政治远见和优柔寡断的一面。项羽斩会稽守之头,斩上将军宋义之头,破釜沉舟救钜鹿,何等刚决果断!但面对并肩作战的刘邦,他却当断不断,不忍下手。宴前当击不击,宴中可杀不杀,宴后宜追不追,而刘邦及其随从刚柔相济,全身而退。鸿门宴通过双方斗智斗勇,刻画出项羽和刘邦性格的差异、见识的高低,从而揭示出汉兴楚败的必然趋势。
垓下之围的矛盾冲突表现为项羽陷于“两难”境地之中的生死抉择。类似的情形刘邦曾多次遭遇,却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项羽也有突围逃生、卷土重来的机会,但他突围而不逃生,只是要显示“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突围又复聚,“乃欲东渡乌江”,尚未彻底放弃卷土重来的希望。当乌江亭长劝他急渡的时候,他反而决意不渡。无面目复见江东父老,独愧于心,一个“愧”字使他彻底放弃了逃生的欲念。生得惭愧,死得痛快,“两难”的抉择在项羽做来并不困难,即使在最后的时刻,项羽还谈笑风生般地将项上人头赠送故人,显得何等豪迈!如果说钜鹿之战是一曲勇壮的凯歌,那么,垓下之围则是一首壮烈的挽歌。写奏凯的场面容易显示力量,而写失败的结局则容易流于衰飒。垓下之围写得豪气干云,悲壮而不哀戚,殊无衰飒之感。
再次是虚实相间,烘托对比,具有浓厚的小说因素。司马迁对钜鹿之战的战略部署和实施采取正面描写,而对具体的杀敌场面采用侧面描写。在正面描写中,字里行间洋溢着项羽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反秦灭秦的战略决心,完满地表现项羽杰出的指挥才能。对于项羽战斗的雄姿和楚军将士奋勇杀敌的情形,则采用侧面烘托。从诸侯军队在壁垒上观战的角度,描摹其“无不人人惴恐”的特殊感受,烘托楚军一以当十的勇猛气势;从诸侯将领入辕门见项羽的角度,描摹其“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的特殊行为,烘托项羽所向无敌的勇圣威风。
钜鹿之战的战场描写侧重于“虚”,鸿门宴的宴会描写则侧重于“实”。诸如宴会坐次排列,范增举_示意、授计舞剑、撞破玉斗,樊哙持盾闯帐、啖肉饮酒、义责项羽,项羽默然不应,项庄、项伯舞剑,刘邦逃席,张良留谢等,描写细腻传神,情景生动逼真,具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性。双方人物中,项羽与刘邦、范增与张良、项庄与樊哙、项伯与曹无伤,两两相对,相映成趣,更增戏剧色彩。
垓下之围的描述更是虚实相间。悲歌别姬描写具体,却纯属虚构。以项羽的文化修为“足以记名姓而已”,如何写得出《垓下歌》?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之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项羽面临失败并不气馁,陶醉于拔山盖世的勇力,不承认自己的无能和过失,将失败的原因推向客观时运,歌诗内容完全符合项羽的心理。盖世英雄最终竟无能保护爱姬,从而为项羽的英雄形象刻上浓重的悲剧印记,他的可爱和可悲都在于此。突围搏战是正面实写,既写出了先声夺人、疾如狂飚的战斗风格,也写出了分散聚合、莫不如意的指挥艺术。项羽认为这是一场得意的“快战”,其实是一场最无意义的恶战,它仅仅证明了“天之亡我,非战之罪”。这一实写紧密照应《垓下歌》。项羽缺乏统一和安定天下的政治远见,却分裂天下,称霸诸侯,违背历史的潮流。最后以区区二十八骑为赌注,为自己的失败挽回面子,可谓至死不悟。阴陵田父绐陷大泽,乌江亭长舣船相待,这两个细节并非闲笔。一方面说明项羽有人恨也有人爱,项羽对于人心向背茫然不知;另一方面项羽由此引发“愧于心”的感慨,愧于心即是“知耻”,而知耻是“勇”的前提。迷失道路时寻找逃生之路,而面临逃生之路却决意自杀,晚唐胡曾《咏史诗·乌江》云:“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正所谓“耻辱者,勇之决也”。在天下反秦最需要的时候,他义不容辞地站到历史的前沿,驰骋于铁血纷飞的战场,扫荡暴秦大军;在意识到愧对江东父老的时候,毅然地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这是英雄的本色,也是项羽形象的悲剧意蕴之所在。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颊俏6319
颊俏6319
 颊俏6319
颊俏6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