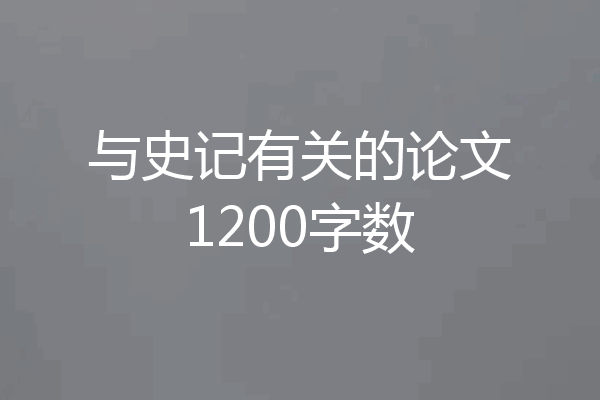yanziwew
yanziwew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出狱后担任中书令,是皇帝的近臣。友人任安给他写信,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想到自己的经历和遭遇,感到很为难,没有回信。待任安触犯刑律下狱,被判处死刑,司马迁写了这封回信。直面自己的遭遇和经历,说明自己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是要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是的,为了自己的理想,司马迁没有选择去死,而是忍着众人的嘲笑和误解,接受屈辱的宫刑换取活命,赢得修史的时间,这才有流传至今的《史记》。 一个人的慷慨赴死,一时的意气可能更为干脆,但是司马迁对于自己的生、自己的死造成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假如不受宫刑之辱,按罪服法,自己像一个蝼蚁般自生自灭,名节得不到承认,仍不免受到众人的嘲笑。更重要的是,还有自己和父辈的心愿未了,史书还没有完稿。两代人的未竟事业,终究还是要留下遗憾。 是忍着屈辱生,还是义无反顾死,司马迁是经过一番挣扎的,他把一个人的受辱,分成依次递进的几等,而宫刑处在最下等。但是,强和弱是形势所决定,勇敢和怯懦也是势位所造成。历史上一些有着曲折遭遇的名人,更证明了这一点。选择生并不代表自己怯懦,选择死并不表明自己勇敢。 司马迁选择了“生”,身心忍受着极大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他的寂寞,不可与人诉说,特别是对于不能理解的人,更无废话的必要。他唯有用事实说话,终于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着屈辱生存的心愿已了,而他的友人任安也走到了生死边缘。所以才有这一封对友人推心置腹的书信,坦诚心扉的字里行间,彰显了司马迁的伟大人格。 司马迁的信,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 他从历史上得出结论。古人干一番事业,都有一定的艰苦付出,这才有流传到今天的一段很著名的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们的人生和作为,没有一个在平安、顺畅环境中的水到渠成,都要在逆境中发愤,坎坷是磨练一个人意志的试剑石。 一个人的大智慧,是能屈能伸,不逞匹夫之勇。想走的更远,要先退一步,什么也不要说,用行动、用成绩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和无怨无悔。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舍生取义”的迂回策略,泰山的死,鸿毛的轻,只是在情势所迫中的一念之间。司马迁的坚韧是能够选择之后,坚持的义无反顾。 此信是司马迁的绝笔,以后的历史再也见不到他的文字。他的卒年成了一个谜,受任安案的连累,受此封直抒胸臆的绝笔信影响也未可知,毕竟他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和朝廷。 值得欣慰的是,写此信的时候,《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已经完稿。司马迁可以无撼赴死,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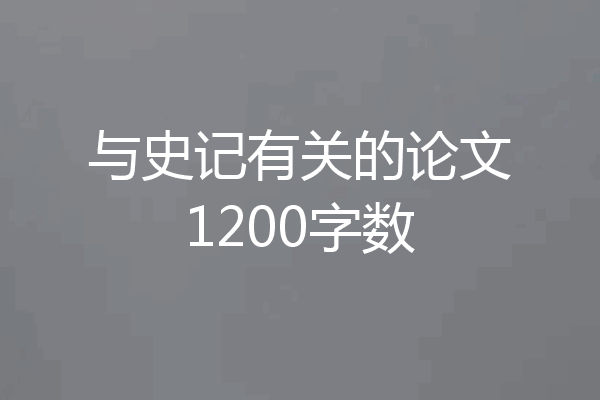
《史记》读后感 喜欢在边缘与缝隙中窥看历史。 喜欢把历史读成小说,也就把《史记》读成小说。《史记》写男子也写女子,写男子不吝笔墨,写女子一笔带过;写女子多淫荡,也多真性情。《史记》于我历历在目的也便是这些女子。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褒姒任性不知轻重;然天下不负幽王,而王自负。曾看过无名氏《烽火戏诸侯》,画中褒姒就像观音低眉,正如佛经云:“仪容婉媚,庄严和雅,端正可喜,观者无厌。”或许这是后世对褒姒的一种阐释,政治也好,淫荡也罢,全归于禅意。 《史记》不写妲己形貌,看过只是很简单地知道纣王沉迷于她的美色,听信过她的话。但许仲琳《封神演义》谓其:“乌云叠鬓,杏脸桃腮,浅淡春山,娇柔柳腰,真似海棠醉日,梨花带雨,不亚九天仙女下瑶池,月里嫦娥离玉阙。”真真尤物!妲己成为经典也都使世人心思。 女子如水,君子当如器。可中国对女子历来缺乏宽容与平和,不但男子对女子,女子对女子也不过如此。那些烟视媚行的尤物常常引起他们本能的嫉妒,嫉妒而生亲近之意,一旦不可企及,便本能地恐惧,又生贬抑之心。妲己成为了狐,女子们也并未像最初的狐一样受到尊敬与膜拜,倒是为“红颜祸水”之说制造了那么一点点可疑的佐证。便痛恨那些古代风气,于女子而言,全是轻蔑与禁欲的压抑。 记得蔡姬故事:“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望伐。”也背诵过“齐侯以诸候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至此,不由大笑桓公也有此狼狈滑稽。其实,淫荡却无邪,才是女子本色,只会让人觉得是美的,而淫荡无邪的绰约处子,更是女子中的极致。我爱的就是蔡姬轻狂如处子,天然情性。蔡姬故事,《史记》未详写,也正因这简略,则惊鸿一瞥,随意怀想之间尽是明媚与凄艳。 骊姬二字极佳,骊可为好马,也可为猛龙,骊姬之骊为骊戎之骊,也并不妨碍我将她与好马与猛龙连起来想。先秦女子之名,可同鸟兽虫草,有时候是这些名字在刻画它们各自的主人,以兽为名的女子,只观其名,似乎就是有了兽类的野性以及这种野性天赋的属于自然之子的骄傲与高贵。而且骊姬为人险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若以旁观者的眼睛来看,不失为另一种美;自然,这样的女子,于当下流行文学的小说作者倒是好材料。 讨厌卫子夫,大概是先听了“金屋藏娇”,如此,卫子夫成了凭借美貌趁机而入的第三者。到底我在为阿娇不平。卫子夫是个大花瓶!或者是宁静演的那个卫子夫实在让我失望。可卫子夫的下场也不好,有些狼狈,《史记》女子们也大抵如此,得善终者少。而她们也不过亲自充当了是古代中国女子的谶言罢了。 女子降生本是福气,女子的敏锐,朴拙,凌厉,温和,才艺,美貌,诸般种种,是女子的福气,也应是人间的福气,但为何这诸般种种却是一具埋葬在灵魂深土下的腐尸,无论曾经有多么绚烂光华,却已朽烂着并长存着,常常在她们沉睡时游离成恶梦,妆扮成她们醒来时猛然发现的躺在身边的骷髅。最是谁喂养了她们少女时代的情欲?其实那些本是一种极致之美,少女的情欲美好而惨烈,惨烈是因禁欲。那些情欲,让她们无法回首,回首之时,人世已深。这无端秀色,当真好没来由! 鲁元公主若不曾被爸爸刘邦几次踹下车,我也不会觉得她是可怜可爱的;而我所喜欢的那个卫子夫,却一定是个夏夜里将萤火虫关进骷髅壳里的少年女子;刘陵聪慧,有辩才,最终死陷囹圄,父亲刘安也留下了鸡犬升天的传说,却不知长生一梦醒,淮南草木又深了几许。 女子好像是突然就失去了最初的神性,不会再有女娲与伏羲的乱伦,从此神灵便是神灵,女子,则彻底沦落,青楼不是真风月,而世间于女子,却处处是艰辛风尘。而《游侠列传》里全是男子,女子无游侠,女子成为游侠是在以后的侠义小说里开始的。《史记》女子,也全无游侠气,到底她们是无此心,游侠本也是一种心境而已,聂荣为弟而死,那江湖终究也与她无关。 不喜欢赵太后,并不因为她已经是“媪”的缘故;就再说说薄太后与窦太后,我喜欢的都是她们还没有成为太后、即当初失意时,那时她们心怀失意与不满,才是人间的可爱女子。她们成为了太后或皇后,就不是当初的那种感觉了,仿佛有什么东西,一去不复返。究竟为何我也难以表清,感觉本身过于微妙,难以捕捉,迷离又神往…… 可惜古之女子无自由,骊姬得以横行后宫,却反为权谋所溺,又不是真自由了。或许自由意味着更高层次上的抉择,并且不为此抉择所累。除了自由本身,谁也没有权利来确认一个女性的价值。但愿能够看到一个活着的女子,她真的足够强大,这样的女子,又应该有怎样的心境?我怎么知道! 还是可惜了,太史没与王昭君活在同一个时代,还真想看太史会怎样写昭君。四大美女,以前喜欢西施,可能是因为她扮演了半个间谍的角色,后来才喜欢昭君,接着就一直最喜欢昭君了。汉帝痛悔,吾当快哉!当昭君的容光震惊了大殿上的所有人,单于使者们的谢恩与君王欲反悔而不得便是昭君的复仇之得逞。明妃去国,汉川亦为之失秀,失意之仇得偿后,又是怎样的虚空与苍凉?昭君自知。 曾怀疑过昭君的存在,这段故事太像传奇,像一部真实的悲剧。且将昭君看作一种情结,慰藉后之怀才不遇者。然昭君之前并无昭君,昭君去后,亦无昭君,世人从来各欲所欲,各哀其哀,又何必以昭君自许? 伍举入谏时,楚庄王左拥右抱的郑姬越女,郑姬越女,你们去国离乡,可会想着回去?夜深也忽梦少年事?这也足以让我凝神感伤。在边缘与缝隙对向历史,所见所闻是血淋淋的断面,有时觉得都是戏,戏里春风别旧梦,而戏外则叹息如此春风又一年。其实戏里戏外,知道了就记住不忘,何必当真执着?历史常常被刻意湮没,那些真实的、残酷的,也就成了化不开的象征与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