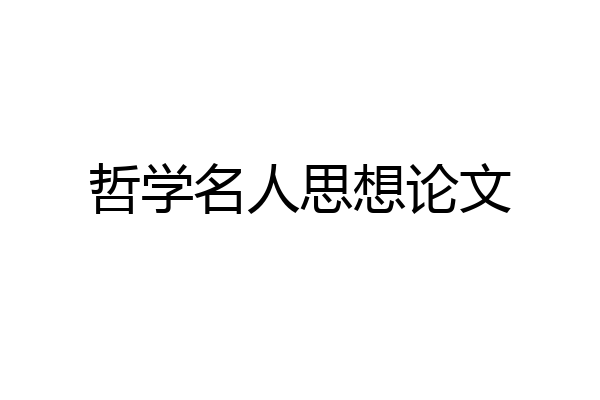floating
floating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导言 二、从意识到科学的发展过程 1.绝对即主体的概念 照我看来,——我的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只能由体系的陈述本身来予以证明——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实体性自身既包含着共相(或普遍)或知识自身的直接性,也包含着存在或作为知识之对象的那种直接性。——如果说,上帝是唯一实体①这个概念曾在它被宣布出来时使整个时代为之激怒,那么所以如此,一部分是因为人们本能地觉得在这样的概念里自我意识不是被保留下来而是完全毁灭了,但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人们相反地坚持思维就是思维,坚持普遍性本身就是这个单一性或这个无差别不运动的实体性②。而如果说有第三种见解,认为思维在其自身中就是与实体的存在合为一体的并且把直接性或直观视为思维,那还要看这种理智的直观是否不重新堕入毫无生气的单一性中以及是否它不重新以一种不现实的方式来陈述现实自身③。 ①指斯宾诺莎哲学。——拉松版编者 ②指康德和费希特哲学。——拉松版编者 ③指谢林哲学。——拉松版编者而且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唯其如此,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所以唯有这种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的真理,而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就其本身而言,则不是绝对的真理。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园圈,预悬它的终点为目的并以它的终点为起点,而且只当它实现了并达到了它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 上帝的生活和上帝的知识因而很可以说是一种自己爱自己的游戏;但这个理念如果内中缺乏否定物的严肃、痛苦、容忍和劳作,它就沦为一种虔诚,甚至于沦为一种无味的举动。 这种神性的生活就其自在而言确实是纯粹的自身同一性和统一性,它并没严肃地对待他物和异化,以及这种异化的克服问题。但是,这种自在乃是抽象的普遍性,而在抽象的普遍性里自在的那种自为而存在的本性就被忽视了,因而形式的自身运动也根本被忽视了。正因为形式被宣布为等于本质,所以如果以为只认识自在或本质就够了而可以忽略形式,以为有了绝对原则或绝对直观就不需要使本质实现或使形式展开,乃是一个大大的误解。正因为形式就象本质自己那样对本质是非常本质的东西,所以不应该把本质只理解和表述为本质,为直接的实体,或为上帝的纯粹自身直观,而同样应该把本质理解和表述为形式,具有着展开了的形式的全部丰富内容。只有这样,本质才真正被理解和表达为现实的东西。 真理是全体。但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关于绝对,我们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个结果,它只有到终点才真正成为它之所以为它;而它的本性恰恰就在这里,因为按照它的本性,它是现实、主体、或自我形成。不错,把绝对本质地理解为结果好象是矛盾的,但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就能把这矛盾的假相予以揭示。开端、原则或绝对,最初直接说出来时只是个共相。当我说“一切动物”时,这句话并不能就算是一部动物学,那么同样,我们都很明白,上帝、绝对、永恒等字也并不说出其中所含的东西,事实上这样的字只是把直观当作直接性的东西表述出来。比这样的字更多些的东西,即使仅只变为一句话,其中也包含着一个向他物的转化(这个转化而成的他物还必须重新被吸收回来),或一个中介。而这个中介却为人嫌恶,仿佛如果承认中介不仅限于表明它自己不是绝对的东西并且决不存在于绝对之中,而还具有更多的含义,那就等于放弃了绝对知识。 但事实上人们所以嫌恶中介,纯然是由于不了解中介和绝对知识本身的性质。因为中介不是别的,只是运动着的自身同一,换句话说,它是自身反映,自为存在着的自我的环节,纯粹的否定性,或就其纯粹的抽象而言,它是单纯的形成过程。这个中介、自我、一般的形成,由于具有简单性,就恰恰既是正在形成中的直接性又是直接的东西自身。——因此,如果中介或反映不被理解为绝对的积极环节而被排除于绝对真理之外,那就是对理性的一种误解。正是这个反映,使真理成为发展出来的结果,而同时却又将结果与其形成过程之间的对立予以扬弃;因为这个形成过程同样也是单一的,因而它与真理的形式(真理在结果中表现为单一的)没有区别,它勿宁就是这个返回于单一性的返回过程。诚然,胎儿自在地是人,但并非自为地是人;只有作为有教养的理性,它才是自为的人,而有教养的理性使自己成为自己自在地是的那个东西。这才是理性的现实。但这结果自身却是单纯的直接性,因为它是自觉的自由,它静止于自身,并且它不是把对立置于一边听其自生自灭,而是已与对立取得了和解。 上面所说的话还可以表示为:理性乃是有目的的行动。过去有人误解了自然也错认了思维,把自然高举于思维之上,特别是否认外在自然中含有目的性,因而使一般的目的形式处于很不名誉的地位。但是,亚里士多德曾规定自然为有目的的行动,同样我们认为,目的是直接的、静止的、不动的东西;不动的东西自身却能引起运动,所以它是主体。它引起运动的力量,抽象地说,就是自为存在或纯粹的否定性。结果之所以就是开端,只因为开端就是目的;或者换句话说,现实之所以就是关于此现实的概念,只因为直接性的东西,作为目的其本身就包含着“自身”(dasSelbst)或纯粹的现实。 实现了的目的或具体存在着的现实就是运动,就是展开了的形成过程;但恰恰这个运动就是“自身”,而它之所以与开端的那种直接性和单纯性是同一的,乃因它就是结果,就是返回于自身的东西;但返回于自身的东西恰恰就是“自身”,而“自身”就是自相关联的同一性和单纯性。 由于需要将绝对想象为主体,人们就使用这样的命题:上帝是永恒,上帝是世界的道德秩序,或上帝是爱等等。在这样的命题里,真理只直接被当作主体,而不是被表述为自身反映运动。在这样的命题里,人们从上帝这个词开始。但这个词就其本身来说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声音,一个空洞的名称。只有宾词说出究竟上帝是什么之后,这个声音或名称才有内容和意义;空虚的开端只在达到这个终点时,才是一个现实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不出,何以人们不仅限于谈永恒、世界的道德秩序等等,或者不象古人所做的那样仅限于谈本身即是意义的纯粹概念、存在、一等等,而还外加上毫无意义的声调?但通过这种名词,人们恰恰是想表示这里所建立的不是一般的存在或本质或共相,而是一种反映了其自身的东西,一种主体。但同时须知这个主体只是被揣测到的。揣测中的主体被当成一个固定的点,宾词通过一个运动被粘附在这个作为它们的支持物的点上;而这个运动是认识这个固定点的人的运动,根本不能视为是这个固定点自身的运动;但只有通过固定点自身的运动,内容才能被表述为主体。按照这个运动的发生经过来说,它不可能是固定点的运动;但既然假定了这个固定点,这个运动也就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外在的。因此,上述关于绝对即主体的那个揣测,不仅不是主体这个概念的现实,而且甚至于使现实成为不可能的,因为揣测把主体当作静止的点,但现实却是自身运动。 在上面的讨论所能得出的一些结论中,这一条是可以强调指出的: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体系才是现实的,才可以被陈述出来;而且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也是假的了;要反驳它因此也就很容易。反驳一个原则就是揭露它的缺陷,但它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仅只是共相或本原或开端。如果反驳得彻底,则这个反驳一定是从原则自身里发展出来的,而不是根据外来的反面主张或意见编造出来的。所以真正说来,对一个原则的反驳就是对该原则的发展以及对其缺陷的补足,如果这种反驳不因为它只注意了它自己的行动的否定方面没意识它的发展和结果的肯定方面从而错认了它自己的话。—— 真正地展开开端固然是对开端的一种肯定的行动,同时却也是对它的一种否定的行动,即否定它仅仅才是直接的或仅仅才是目的这个片面性。因此,人们也同样可以说展开或实现乃是对体系的根据(Grund)的一种反驳,但比较正确的观点是把开端的展开视为一种表示,它表明体系的根据或原则事实上仅只是体系的开端。 说真理只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或者说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这乃是绝对即精神这句话所要表达的观念。精神是最高贵的概念,是新时代及其宗教的概念。惟有精神的东西才是现实的;精神的东西是本质或自在而存在着的东西,——自身关系着的和规定了的东西,他在和自为存在——并且它是在这种规定性中或在它的他在性中仍然停留于其自身的东西;——或者说,它是自在而自为。——但它首先只对我们而言或自在地是这个自在而自为的存在,它是精神的实体。它必须为它自身而言也是自在而自为的存在,它必须是关于精神的东西的知识和关于作为精神的自身的知识,即是说,它必须是它自己的对象,但既是直接的又是扬弃过的、自身反映了的对象。当对象的精神内容是由对象自己所产生出来的时候,对象只对我们而言是自为的;但当它对它自身而言也是自为的时候,这个自己产生,即纯粹概念,就同时又是对象的客观因素,而对象在这种客观因素里取得它的具体存在,并且因此在它的具体存在里对它自身而言是自身反映了的对象。——经过这样发展而知道其自己是精神的这种精神,乃是科学。科学是精神的现实,是精神在其自己的因素里为自己所建造的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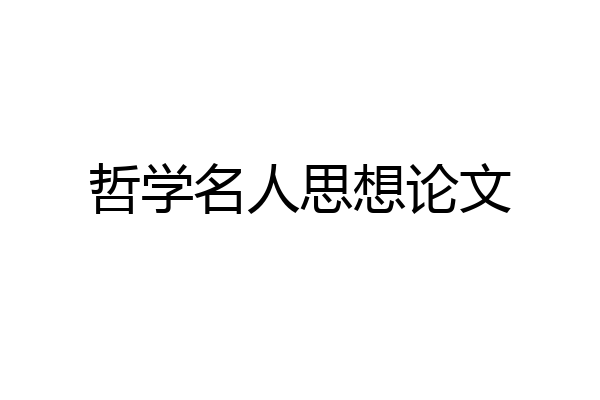
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在粗略读完《庄子》一书之后,颇有感触。依我自己尚肤浅的认识而总结出来的对《庄子》一书的评价,主要有四点: 1、作为百家争鸣时代产生的作品,《庄子》首要的特点就在于其内饱含道家深邃的思想。 众所周知,《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为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其外涉及政治、处世、养生、世界起源论和本质论、唯物辩证法等各个方面。它既是道家用以认识世界的工具,更是其劝人律己的道德手段。“道”最重要的,也是贯穿《庄子》一文始终的观点是“顺天”和“无为”。虽然各篇内容各异,思想浩繁,但我们多多少少都能体会到作者希冀的任天为之,不加外物束缚的自由境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境界何等雄浑! 然而,一些消极避世、过分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观点,显然是不足取的。 2、正因为庄子本人的思想超脱万物、穿越古今,必然要求文章中想象和虚构奇特磅礴,恣意汪洋。 写大物,有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有荫蔽千头牛的栎社树,有中央之帝混沌;写奇人,有乘云气游于四海之外的藐姑射山神人,有御风而行的列子,有用五十头牛做鱼饵的任公子;写怪事,有周梦蝶、魍魉问影、骷髅论道;写隐士,有狂人接舆、贤人肩吾、悟道者南郭子纂——总之,所绘之人、事、屋、物、景,皆使作者思想得以曲折地展现。COM 3、想象和思想通过特定的创作方法表现出来——“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卮言即出于心、自然流露之语言;重言为借尊者、名人之口,说出自己的观点看法;寓言是虚拟地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 其中,寓言是最有名的,通览全书,无一篇不涉及寓言故事的创作,而无一个语言故事不是独出心裁,着意为之。《庄子》的许多思想艰深抽象,而语言却化虚为实,将理论变得真切自然。重言也是随处可见,尤其是借孔子之口道出道家观点。这一点作者是矛盾的:道家避世自修的态度显然对儒墨等积极人世的行为表示不屑;而当时儒墨并盛,孔子为名人,为了使自己的主张为他人所接受,庄子又不得不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为曼衍”,层出不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这一点其实在诸子百家的许多著作中都存在。这里将其提出,庄子是想证明:自己的语言皆从内心自然涌出,言为心声,不能为外界功利目的而矫揉造作。 4、语言跌宕起伏,句式错综复杂,论辩性强。 庄子擅用尖新奇特之词,大段排比、反问、疑问的句式去论辩,读之或铿锵有力,或发想无端,或尖锐辛辣。当然,正是因为作者不直接表明态度,而是叙议结合地让读者去领悟其中的道理,加之作者思维跳跃较大,逻辑上往往会有疏漏,常常是开篇的寓言与后文衔接不上,最为突出的表现是《齐物论》和《寓言》。另外,篇末附及的一些寓言让人感觉过于重复拖沓,没有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