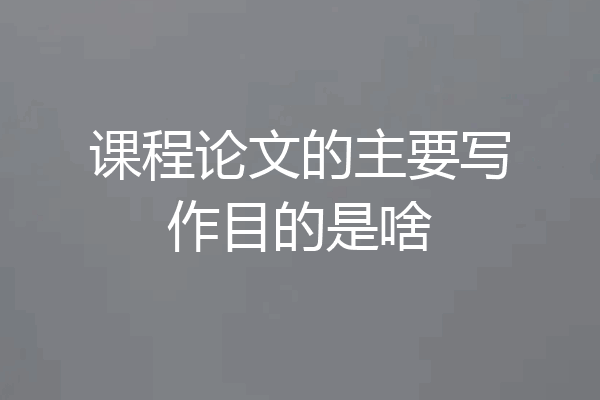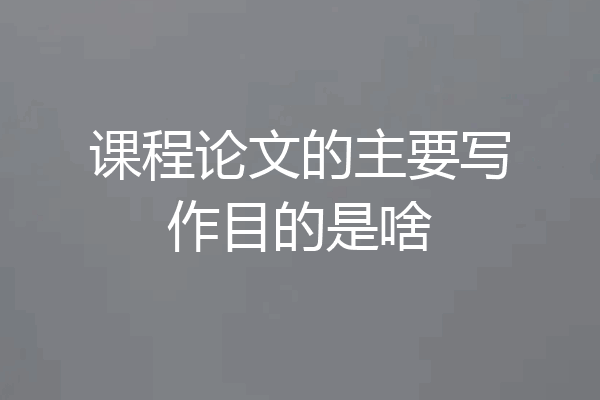xf13778459
xf13778459
自娱自乐的作者,作品首先为了自己看,先使求知欲得到满足,但话又说回来,既然是自己所写,书中的情节和思想都是已知的,虽然文思泉涌、下笔如神的章节再读也会惊叹,但看自己作品的神秘感和收获肯定少于阅读他人之作。如果具有一定的功力,文章确实上得了档次,那也值得一读,但若文笔拙劣,思想庸俗,自己都不忍卒读,那便连自娱的雅兴也没了。所谓“大师”的成长都需要一定过程,其基础便是“兴趣”。再说有感而发。卡夫卡说他肚里有团火,不释放出来就会堵得慌,浑身不舒服,而释放的渠道就是写作。所以,他写作的目的跳过了兴趣一阶,直接进入了情感层。这是可以想象的。情感的抒发有说话、哭笑、唱歌、跳舞、表演、运动等多方面,而写作是一种较为永恒的方式。作者用文字表达之时,就是一种情感宣泄,在那一瞬间是短暂的,但记录成文字编集成书之后却化为永恒,成为记录思想的历程。忧郁的卡夫卡施耐庵写《水浒》的最大目的不是文学爱好,而是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和愤怒,作者的一腔怒火无处发泄,于是草莽英雄纷纷啸聚山林,替天行道,大开杀戒,无拘无束,后世称之为“怒书”,书中鞭笞社会的笔墨比同期的《三国》强烈很多:张飞粗暴,但无非鞭督邮、叱董卓、罚士卒、杀敌将,仅此而已,李逵杀人,连带人家几十口尽皆杀死,施耐庵给他冠上“天杀星”的名号,可见水浒中的血腥暴力要比三国重得多。如同卡夫卡《城堡》《变形记》中对变异的世界冰冷地讽刺一样,读者无不感到作者强烈的表达欲望,快感呼之欲出。如果不是在情感和思想上有所表达诉说,这些作品就失去了意义,成为了空洞的文字堆砌。这就是写作的第二要素“思想”。因杀下凡的男人最后说流传后世。前两种目的看起来非常单纯,写作仅因为有兴趣和思想表达,想要流传后世似乎过于现实,又很难办到。其实并非如此。从孔子整理《诗经》开始,他就有将文学经典流传后世的想法,弟子们编辑夫子语录《论语》更是开创著作先河。曹丕谈及“立言”的重要性,说了为了流传后世。相较于纯粹的兴趣,这种思想有着较强的功利心,古龙、倪匡表示自己早期作品纯粹为了赚稿费,那时并不好看,可他们成名之后却能越写越好,从而成为大师,可见功利心并非就是坏事,想成名想赚钱的作者也可能走向成功之路。倪匡与古龙当代媒介发达,出版容易,所以写书越来越普及,这在古代真是难以想象。同时也造成了书海泛滥、良莠不齐,读者不知该读哪一本,只好顺应潮流,跟着众人的口味走,形成畅销引领潮流的趋势。畅销其实也是实力的表现,往往实用、时效、娱乐、颠覆性强的书籍最易进入榜单,但这不代表其余默默无闻的书就是糟糕的作品,反而很多文学作品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累积才能闪放光芒。经常有报道一些神童很小就出书了,狂称要超过《史记》、《红楼》、鲁迅、莎士比亚,引起不少非议。我认为,这种志向树立远大目标是不错的,能够激励自己进步,既然想在这个领域成功,何不向最优秀的伟人和作品看齐呢?即便没有达成所愿,这一路上的痴狂不也是艺术界值得提倡的精神吗?但前提是,必须真正去喜欢这些伟人和作品,不能人云亦云,只图浮华虚名。想成为大师非常困难,光有兴趣和思想还不够,仍需要天才的头脑,博学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强烈的情感,写出引发他人共鸣的作品才行。这就是最后一项——“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