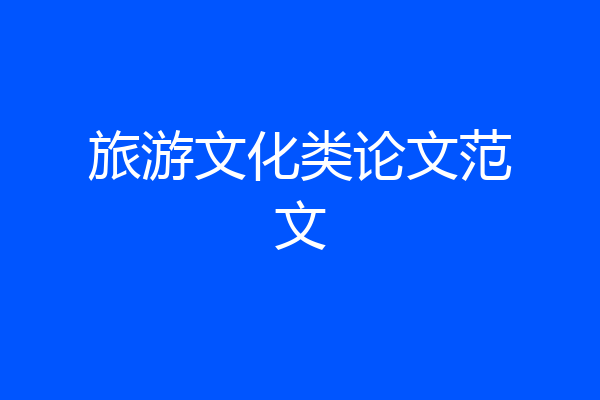一路西游
一路西游
伴着北京奥运的声声捷报,周六下午结束了甘肃新疆之旅,今天特来向久违了的博友们问好! 八天的行程,匆匆忙忙,有一些遗憾,但更多的是惊喜和感慨。回来后时间紧迫,工作任务也重,一路的风景描述和观感,恐怕没时间来进行了,先慢慢上些相片吧。 第一站--兰州 应该说,兰州只是旅游的一个中转站,风景名胜比其他地方相对要逊色一点,但其历史文化底蕴,却有很深的渊源。始建于公元前86年,叫金城,已近2100年的历史了,在隋文帝时开始就叫兰州了,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后来建制的几度变化,见证了中华大地历史的演变。 兰州是唯一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走在中山桥,即号称“天下第一桥”--黄河铁桥上,看着滚滚黄河水,由西向东奔流而去,难以想象20世纪初当年德国、美国工程师和华洋工匠,是如何不远万里,从德国运来建设材料,创造并结束了黄河上游千百年来没有永久性桥梁的壮举。后来,也是在这里的对河两岸,彭德怀率军和马步芳曾在此激战,解放了兰州 沿河两岸,风景秀美,其景色也不亚于我们的沿江风光带,怀着极大的兴趣,乘坐了羊皮筏子,在黄河上激情漂流了一躺,爽呀!羊皮筏子,是一个古老的交通工具了,由整个羊皮,吹气后,栓在一起,形成筏子,即“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 接下来,登上白塔山,观看兰州市全景;参观黄河母亲雕像 途中还路过了甘肃人民出版社,其主要刊物,大家都知道的---《读者》,其发行量已达1000万册,综合类杂志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仅次于《时代周刊》、《读者文摘》、《国家地理杂志》。 走马观花,兰州的印象不是太深,我们更期待下一站--嘉峪关 从兰州乘了一夜的火车,清晨起来,见到车窗外,南边是连绵的祁连山脉,终年未消的积雪,一直向西延伸,好象列车永远也无法跑到它的尽头;北边,放眼望去,人烟稀少,树木罕见,很是荒凉啊。到嘉峪关市下车,早餐后,就直奔嘉峪关而来。 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是保存程度最好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嘉峪关关城布局合理,建筑得法。关城有三重城郭,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重城并守之势。嘉峪关地势天成,攻防兼备,与附近的长城、城台、城壕、烽燧等设施构成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又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关城内现有的建筑主要有游击将军府、官井、关帝庙、戏台和文昌阁。每个城门口都有“士兵”把守,还不是有“军士巡逻”,校场内“练兵”的鼓声、厮杀呐喊不绝入耳,站在城楼上眺望,既可想象当年盛唐时期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也能感受当年“醉卧沙场”恢弘壮阔的边塞风光,又仿佛自己回到了古代,如号令千军万马的将军,点将演兵,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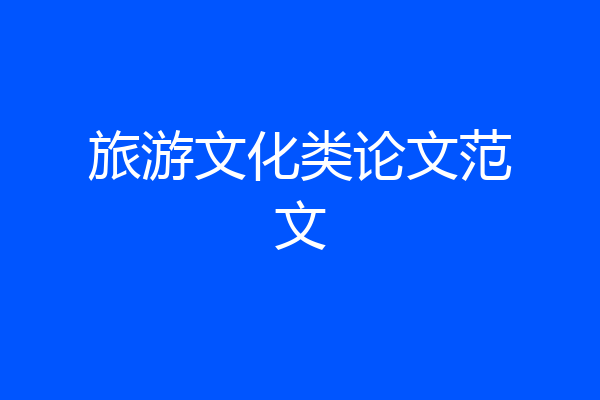
个人觉得从文化的延续、保护与传承下手比较好 旅游景点的开发总的来说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当然对现在的人来说 或许经济性更重要 但这是一个发展方向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 ,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 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7%。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但是,当我们怀抱全球化的语境联想,以此审视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游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原则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忧虑的是,民俗风情的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已经彻底仪式化了。当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抛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尽管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被想像成为天真蒙昧的代名词——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编织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兴旺,其背后所支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旅游由于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与价值的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民俗风情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是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想像之途径,随着民族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差距日益凸显,也已经成为地区间文化想像的文化符号。 实际上,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后现代时期文化的诸多特点,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象,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区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民俗文化,真实的生活物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建筑、戏剧化地想像为一套千篇一律的仪式,这本身就已经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平面化、瞬间化了。旅游部门一再强调,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体验异文化情调,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展现,旅游者将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体验一次充满异域情调的旅游探险,种种煽情的语言激起旅游者的无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游从策划、设计规划、投资建设、推向市场等等一系列步骤都表明,旅游部门向大众推出的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公园、博物馆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态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再生产与市场的逻辑,民俗文化在当下市场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主宰着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无论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让你感受一种所谓的真实体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而言,它与许多地方为了获得文化的交换价值蜂拥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复制。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实质却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威胁着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题公园试图以奢华浮靡的宏大排场来展示、汇集不同族群民俗文化的典型场景,这种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只不过就是对世界的仿真物,人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并不探求一个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实在,而只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体验现实的游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它是社会性与工具性的产物,主题公园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它是大众欲望、权力政治与大众媒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产物,消费主义的逻辑渗透到主题公园设计的每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