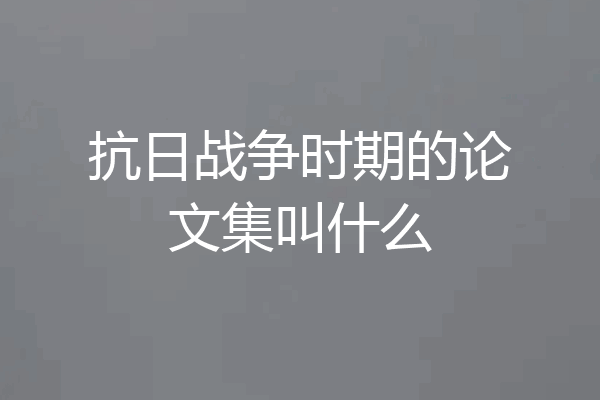学术KAI
学术KAI
在安国县上高小时,孙犁就开始阅读文学研究会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14岁那年,他来到保定西关育德中学读书,更爱上了新文学,尤其是鲁迅的文章。他也喜欢读茅盾、巴金、叶圣陶的作品和外国作家梅里美、普希金、契诃夫、高尔基的小说,这些作品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精练、含蓄、明快的艺术风格,都深刻影响了孙犁。而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文学作品,更使孙犁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因此,本想报考邮政学校的孙犁,选定了以“反映现实生活并推动现实牛活前进”的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此间,他还读了很多哲学、伦理、文化、社会学和生物学方面的书。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知识基础。 高中毕业后,他曾在河北省白洋淀边同口镇当了一年小学教员,“清晨黄昏,我有机会熟悉这一带的风上和人民的劳动、生活”。他作品中白洋淀儿女的形象及荷淀、苇塘的风光就是作家在此基础上的体验。 1937年,孙犁在冀中投身抗日洪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那“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那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的时代,给了他深厚的生活体验,加上他独到的分析观察和从古今中外大帅的作品中学到的精湛的艺术技巧,形成了他忠于生活真实、追求和歌颂美、为人生也就是为人民的艺术观,并逐步发展完善为至今仍有许多人在学习的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 1949年1月15日,孙犁随军进人天津,在《天津日报》社工作。他发现并培育了一批很有才华的工人作者。1956年后的十年间,孙犁一直在病中,加上文革十年,前后约二十年一直搁笔。从1977年7月开始,又重新开始创作,“老作家焕发青春”,写出了许多优美的作品。 孙犁从1930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作品,到1949年创作了三十多篇小说,结集出版过《荷花淀》(1947,小说散文合集)、《芦花荡》(1949)、《嘱咐》(1949)和《采蒲台》(1950)等,还写过辅导文学青年的小册子《文艺学习》。解放后写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和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1981年孙《犁文集》出版,后又陆续发表了许多散文、杂文、小说、文艺随笔等,结集的有《晚华集》、《秀露集》、《无为集》、《远道集》、《如云集》、《曲终集》、《陋巷集》、《尺泽集》、《澹定集》、《老荒集》及《耕堂杂录》、《芸斋小说》等。孙犁一生的创作不算很多,但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却有重要的影响。 其早年的主要作品,首先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对这些作品,作者认为:“我最喜欢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 这个故事发生在农业合作化初,作者没有像柳青《创业史》那样,通过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父子关系来揭示这种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十人们思想的影响,而是从经济状况变化之后铁木二人的友谊悲剧这样一个侧面来写,这是因为作者觉得“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作者侧重写人情变化,写人生,写内心感受,即从人情与道德角度切入生活,别具一格。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说中的一个性格复杂的独特人物——小满儿。她美丽、热、大胆、伶俐,却又狡黠、尖刻,乃至有点放荡;她聪明能于却又常常逃避开会、学习,野性难驯;她被人称为“落后的女人”,但内心非常自尊,充满着对幸福的渴求,生命力充盈。这是在那个年代徘徊在人生交叉路口的“圆形人物”。这样丰满复杂形象的成功塑造,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技巧与风格。 茅盾先生曾称赞过孙犁的风格:“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多风趣而不落人轻怫。” 孙犁晚年的(斋小说)风格大变,古朴凝重,篇幅极短,且后附“芸斋主人”的议论,蕴含了作者一生的思索和睿智。这位精神田园的执著守望者,在晚年形成了自己崇尚自然之道的美学思想。 下面就来专门谈谈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它写于延安,发表于1945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副刊。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河北省中部白洋淀地区的一个农村里,有七个青年要去参军,在县里报了名。他们怕家里人拖后腿,就公推厂一个叫水生的游击组长回去跟他们的家里人说明白。水生连夜赶回家,到别人家里做了些说服工作,又与妻子话别,第二天便匆匆走了。过了两天,这些青年妇女想去看看参了军的丈夫,给他们捎点衣裳。她们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的马庄去。可部队刚好在前一晚开走了。于是她们回家,路上碰到了一只日本鬼子的大船。她们拼命地逃,鬼子在后面穷追不舍。在她们把小船划进荷花淀里的同时,埋伏在淀里的一支部队给了鬼子迎头痛击,打沉敌船,全歼鬼子。她们这时才发现,原来伏击鬼子,在危急关头救了她们性命的,正是她们想见的新参军的丈夫。战士们完成了任务,又见到了爱人,高高兴兴地带着战利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年秋天,这群妇女也学会了射击,在冬天配合子弟兵作战。 作品肯定了人民战争,热情歌颂了根据地人民英勇、乐观和自觉的精神。但艺术表现上却别开生面、情趣盎然,可以说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标志着孙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熟,体现了孙犁小说的鲜明特色。第一,善于运用日常生活画面来展示时代风貌。作者在五千多字的篇幅中,用来写伏击战的只有十分之一的文字,重要笔墨都用来写夫妻话别、探亲遇敌、见到丈夫等场面,但这些平凡的场面却别有深意。如夫妻话别,写的是水生他们报名参军抗日,可作者没将笔墨放到水生他们如何报名的场面上,而是通过水生嫂识大体、顾大局,勇挑家庭重担,支持丈夫参军的举动,写出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人民尤其是年轻妇女的崇高品德和革命觉悟。丈夫走了几天后,水生嫂和女伴们想念丈夫,借日去看他们,足见爱之深。而爱得那么深切又能毫无怨言地送自己的丈夫参军,更见民族大义。亲眼见到丈夫的伏击战后,她们说“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这样的“儿女情”,正是对新时代英雄儿女的一曲赞歌。《荷花淀》的续篇《嘱咐》(1946),写的是离家八年的水生回家,只呆了一晚又匆匆与妻子离别的故事。水生嫂的临别嘱托看似夫妻告别的日常画面,写出的却是广大人民的嘱托、历史的嘱托,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持和殷切希望。孙犁的小说致力于挖掘日常生活画面中解放区劳动人民尤其是妇女的新风貌和高贵品质,“至于那些年轻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时代精神最闪亮之处被孙犁捕捉到了,显示出他小说的敏锐和深刻。 第二,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这、点是和孙犁的艺术追求分不开的。孙犁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很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的作品,“我喜欢他们作品里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勤学苦练》),要“表现真善美的极致”。《荷花淀》一开篇,寥寥几笔.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饱含着诗情画意的风景画,同时也是风俗画。“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女主人公在这美丽的画中,愈见其心灵手巧、勤劳能干。劳动生活也不似往常那般枯燥,而以一种诗意般的描写将劳动的愉快表现得含蓄、优美,作者对于乡下、对于人民的赞美和想念也全在这画里。这是一幅白描的画,但画中分明有诗,一首不露痕迹的“抒情诗”,显得那么浪漫。又如后面的文字:“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L生长去了。”描写于净利落,照实写出却处处弥漫着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展示出一幅解放区安闲宁静的美好生活画面,更激发人们对破坏这种生活的鬼子的痛恨。 第三,善于运用对话和细节描写人物。如写水生嫂和四个年轻妇女想念丈夫却又找借口的那一段:“我不想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我本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虽每人只一句,却活画出了处于战争环境中的一群活泼可爱的青年妇女形象。她们在见到丈夫后回来的路L的那些议论也是如此。孙犁不但善于通过外在的言谈举止塑造人物,而目,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的典型细节。例如,当水生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时,“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苇眉子划破了手”,内心瞬间剧烈的心理活动,借助手指的震动传达出来。听了丈夫的解释后,她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低着头说出这句话,与仰着头、歪着头、笑着说、撇着嘴说是不同的。它生动地表现了这时的妻子对丈夫那种爱中有怨,怨中有爱的复杂感情和矛盾心理。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对家乡人民话语、动作的熟悉,是作者生活、思想和艺术修养深厚的一种表现。 第四,语言简洁、优美,富于诗情画意。大家常喜欢用“诗的语言”来概括孙犁的作品的语言。孙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并善于运用饱含诗情的笔触来表现它。不论是对话,还是叙述、描写,用的哪怕是最通俗的口语,都能像诗句一样优雅。如几个女人没见到丈夫往回走时,有句这样的话:“可慌(高兴的意思)哩,比什么都慌,比过新年,娶新——也没见他这么慌过!”一个“慌”字生动地表现了青年妇女那种既兴高采烈又急不可待的心情,看到了青年们火热的心。而那位女人说到“娶新”时,心里一羞,脸上一红,灵机一动,舌头一卷,忙把吐到嘴边的“媳妇”两字咽下去了,诗境一般地显现了人物心灵深处的一闪念。 孙犁的小说有其独特的贡献。在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创作中,尽管题材风格上有差别,但主题与旋律却基本相同,即对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以及民族精神的弘扬,形成了一种“政治、功利”的叙述模式。而孙犁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一流行格局,并为现代文学民族化、现代化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与赵树理侧重探索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如何成长的“变”的过程不同,孙犁以充满诗意的笔致侧重于歌颂“变”之后的人民群众的“新”与“美”,不按流行格局去表现,而是将艺术的聚焦点对准他们内在的心灵世界,为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习惯于大风沙的“延安读者”带来了“带有荷花香味”的风。在孙犁的影响下,出现了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苑纪久等一批作家,形成了“荷花淀派”,可谓影响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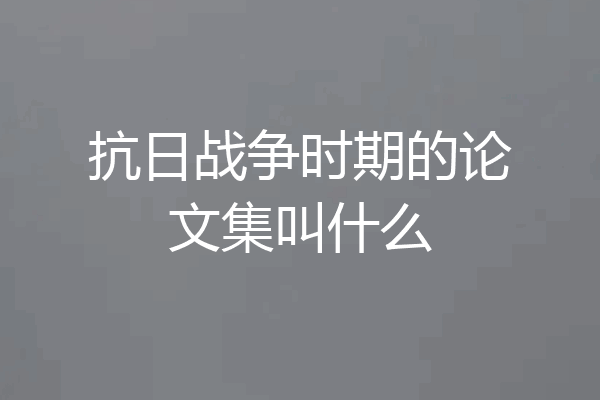
一、作品简介:《白洋淀纪事》是孙犁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小说、散文选集,曾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包括作者从1939年到1950年所写的绝大部分短篇小说、散文、特写、通讯等,其中共收录短篇作品近百篇,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荷花淀》与《芦花荡》这对“姊妹篇”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作品。二、作者简介:孙犁(1913—2002),河北省衡水市安平人,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孙犁”是他参加抗日战争后开始使用的笔名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十二岁岁开始接受新文学,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45年发表短篇小说代表作《荷花淀》。“七七”事变前夕,在白洋淀地方小学教书,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步人文坛。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孙犁的作品极具特色,清新自然、朴素洗练,茅盾称之为“多风趣而不落轻佻”。三、主要内容:小说主要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生活情景。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烽火燃遍冀中平原,燃遍白洋淀,根据地的人民是那么顽强。房子是烧了,但还有炊烟;草是枯萎了,但花还开着;淀是围了,但人们还在打渔;冷月虽然是凄清的,但还照着人们前行的道路。作家没写酷烈的战斗,没写血火拼杀,他就写根据地人民的坚韧执着,写苦难中的人民生生不息的斗争。吴召儿带领八路军转到山里打游击,她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八路军有她当向导如鱼得水,游韧有余。秀梅在白色恐怖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成功配合男友从伪军手中夺下枪枝,以后又帮助男友的父母渡过重重困难,表现了一个抗日军属的高风亮节。刘兰作为一个八路军护士对革命军人用情之深也很见光彩,她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对病人尽职尽责,嘘寒问暖,有空就给病人唱歌讲故事,用自己的热情和善良疗救着每一个伤病员。作品共刻画了六十多个性格鲜明的妇女形象,每个短篇虽然只刻划了一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但总起来看,就勾画出了根据地妇女的生活,和她们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的过程。四、重要篇章:(一)《荷花淀》内容:在抗日战争期间,河北省中部白洋淀地区一个农村里有7个青年要去参军,在县委报了名。他们怕家里人拖后腿,就公推了一个名叫水生的游击组长回去跟他们的家里说明白。水生连夜赶回家,辞别了自己的妻子,又到别人的家里做了些说服工作,第二天就忽忽走了。过了两天,这些青年妇女就想去看看参了军的丈夫了。她们偷偷地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的马庄去。谁知道赶到那里,部队刚巧在前一天晚上开走了。她们只好回家去。可是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只日本鬼子的运输船。她们拼命逃命,把小船划进荷花淀里,鬼子却穷追不舍。幸亏我们有一支部队埋伏在荷花淀里伏击鬼子,在危险关头救了她们性命的,正是新参军的丈夫。战士们完成了伏击任务,又和亲人见了面,就兴高采烈地带着战利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青年妇女们在荷花淀伏击战中受到锻2炼,后来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很快就学会射击,参加了反“围剿”战斗。人物形象:在《荷花淀》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农村妇女的群像。这些妇女勤劳、朴实、善良,识大体、顾大局,是在特定的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水生嫂是作品着墨最多的妇女典型。她勤劳、能干,编苇席,一会儿“就编成了一大片”;她贤慧、温柔,敬重老人,疼爱孩子,体贴丈夫,在她身上有着我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水生嫂虽然爱丈夫、爱家庭,眼光却不狭隘,她能识大体、顾大局,懂得如何处理爱国与爱家的关系。当她知道丈夫报名参了军,虽然也心疼丈夫,依恋不舍,但她还是很快欣然同意,并为丈夫准备好了行装。白洋淀的妇女不仅是勤劳、能干、识大体的,也是乐观的、坚强的。水生嫂等妇女们的成长,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冀中人民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巨大变化。作者通过塑造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妇女群像,歌颂了冀中地区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革命斗志以及爱国主义精神。(二)《芦花荡》内容:《芦花荡》主要写了一个老英雄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一个老头子撑着一只小船,在白洋淀里无数次地穿过了敌人的夜间封锁,为游击队运输粮草、护送干部。他不带一支枪,只靠那只灵巧的篙和水鸭子似的游水本领,在万亩苇塘里穿梭,从未发生一次意外,靠了他,游击队才维系了淀里淀外的交通联络,部队的战斗力也得到大大增强。不过芦花荡中的这个老英雄有时又有点过于自尊、自信,有一回,他带着两个和队伍走失的女孩进入苇塘时,因为自信自己是万无一失的,最后在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一个女孩不幸被射伤,他于是觉得“丢人现眼”、“没脸见人”,充满了满满的自责。第二天,还去找鬼子报仇雪恨。芦花荡中的这个老英雄非常的智勇双全,十几个鬼子因为中了他的计谋,被钩子咬住、动弹不得,只好等着被痛打一顿。 人物形象:老头子的英雄性格,首先表现在他爱国抗日的热情,老当益壮的气概上。老头子将近六十岁了,“浑身没有多少肉,干瘦得像老了的鱼鹰”。他像青壮年一样,充满活力,无所畏惧,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出没苇塘,成为一名贡献卓著的英勇的交通员。这不仅因为他熟悉白洋淀的地理环境,有高超的“水上的能耐”,更是因为他具有英雄气概,藐视敌人,无所畏惧。老头子能够冲破敌人的封锁,对于苇塘里面的队伍坚持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老头子的英雄性格,还表现在他具有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上。对乡土,对同胞,对抗日队伍,他是如此深情,对日寇则满怀仇恨。老头子那么喜爱两个孩子,这是他对同胞的感情。在老头子的意识中,咱中国人是白洋淀的主人,他对乡土充满感情,对侵略者充满仇恨。老头子的英雄性格,还表现在他的过于自信自尊上。他自信万无一失,这一次女孩子受了伤,他就觉得“丢人现眼”“没脸见人”。这样的要脸面,正包含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心,他对自己要求之严,近于苛刻,偶有过失,他就痛苦得万箭穿心,愧疚得无地自容。老头子的英雄性格,还表现在智勇双全的英雄行为。老头子用竹篙痛砸十几个鬼子的脑袋,是用了计谋的。他早在枯木桩子上系上了一只只锋利的钩子,船头上放了一大捆新鲜的莲蓬,引诱鬼子进入枯木桩子的水区,让钩子把鬼子咬住,叫鬼子动弹不得,束手挨打,张牙舞爪的鬼子在他面前一个个成了被绑的困兽。《芦花荡》中的这个老英雄不畏艰险、老当益壮。对革命,他真的是尽心竭力,勇敢得出奇。他强烈的责任感、他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的斗志昂扬让我们看到了当年革命胜利的原因,让我们看到了英雄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三)《采蒲台的苇》内容:《采蒲台的苇》以抗战时期的白洋淀地区为背景,以质朴的笔触叙述了一个真实的军民抗日的故事。到处是苇,最好的苇在采蒲台。一次,敌人来搜查这个村,妇女们想了一个办法,把抢插在孩子的裤裆里,枪掩护过去了,敌人抓住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最后这个男人被杀死了。作者采用了象征手法,用坚韧不拔的“苇”来表现那些英勇抗战的白洋淀人民,更是用白描手法来表现勤劳勇敢的白洋淀妇女在面对敌人时那种冷静与无畏的精神,同时也是对当地老百姓智慧的赞美和歌颂。五、艺术特色(一)、从平凡的生活事件中开掘主题,反映时代精神。在孙犁的作品里,虽然描写的是抗日战争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直接写战争的激烈、残酷,也没有“凄凄、惨惨、戚戚”的描绘,就连那个女孩子受伤后的几声呻吟,也被轻轻一笔带过去了。作者把笔墨集中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力图通过在我国革命进程中那些最普通、最常见的生活事件,表现出作家所经历的那个时代,表现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精神风貌。作品要高昂浓重地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念和乐观情绪。我们透过他的小说,可以遥看到历史车轮辗过的痕迹。《山地回忆》写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她用自家仅有的一点“白布”给“我”做袜子的事。当“我”穿上那双坚实的袜子时,妞儿自豪地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一个普通的山村女孩,一双普通的白布袜子,却折射出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山地回忆》可谓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曲军民鱼水深情的颂歌。这双凝集着军民鱼水深情的袜子,穿在“我”脚上整整三年,伴随着“我”到了抗战胜利,袜子虽然被奔腾的黄河水冲走了,但我对妞儿一家的怀念之情,永存心中。袜子虽小,却凝结着军民深情。(二)、着力于内心世界的刻画,塑造人物的心灵美。孙犁是善于刻画人物的,尤其善于刻画农村妇女的形象。青年妇女和少女的形象,更是被他描写的绘形绘声和生动活泼,体现出中国劳动妇女的聪明美丽勇敢的特点。他的小说在塑造人物时,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荷花淀》写了以水生嫂为代表的一群劳动妇女,小说将那些淳朴的、近乎稚嫩的年轻妇女们置于革命战争和个人生活的矛盾中,细致地展示在她们纯洁的内心世界里掀起的情感波澜。她们时而陷入离别亲人的痛苦,时而为探寻丈夫编织着种种荒唐而又可笑的理由,时而对丈夫的转移发出埋怨的谑语,时而撞见敌人的火船时表现出惊恐和镇静,时而意外地遇见亲人又感到兴奋和羞愧……总之,作家以多情的笔墨描写了她们被无情的战争打乱了的内心世界,显示了她们丰富美丽的精神情操。(三)、简洁传神,朴实自然的富有个性化的艺术语言。《“藏”》中那个叫浅花的媳妇,人还未出场就给读者惟妙惟肖的印象:这个女人,好说好笑,说起话来象小车轴上新抹了油,转的快叫的又好听,这个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活赛过一个好长工。她纺线,纺车象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挺拍乱响,梭飞的象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象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这样的语言,似乎人人都会说,但却人人未必都能付诸笔端。没有扎实的生活基础,没有对群众生活的真实体验,没有精湛的艺术修养,是不会把蕴藏在沙砾中的璞玉变成闪光的艺术瑰宝的。(四)、富有特色环境描写:即使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作者仍然以沉静从容的姿态抒写白洋淀的美丽风光。环境描写富有诗情画意,充满水乡的气息。《芦花荡》、《荷花淀》两篇都讲了一个很小的故事,而对于歼灭敌人都不作正面描写,反之着墨更多的是芦花荡与荷花淀的景物,写芦花芦苇,写荷花荷叶,写小渔船,写船上的妇女儿童,写水天一色,烟波浩渺,写抗日军民的机智勇敢,乐观豪迈。比起那些酷烈血腥的故事,孙犁的散文没有大喊大叫,没有哭哭啼啼,而是轻灵飘逸,婉约唯美,抗日故事写成这样的风格应该说是孙犁的首创和独创。六、深度解读之人物人物: 《投宿》通过“我”的眼睛,描写那位腼腆而又庄重的农村少妇,熟悉北方一带农村生活的读者会深切地感到,这正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受着时代激流冲击的那些年轻妇女的面影。一方面,这个年轻妇女受着革命战争的熏陶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她的丈夫就是一个八路军战士,后来当了连长),对于我们的抗日干部无疑是信赖和尊敬的;另一方面,应当估计到传统的思想意识在她身上的影响,因此,她的信赖和尊敬,是用一种无言的,略带伍泥和腼腆的仪态表现出来的。作者这几笔简单的勾勒,含蓄而蕴藉,所画的正是那个时代我国北方农村某些青年妇女的神态和气质。《走出以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是多么善于观察和捕捉时代在这个女孩子精神上和外形上所留下的印记, 她和婆家脱离关系、进入抗属中学之后的几个月,她变了,封建婚约,这是旧时代产物,反映着旧的生产关系,它在王振中身上造成的那种“神气一萎”,实质上是恨时代在这个女孩子身上的阴暗投影。但王振中毕竟生活在充满阳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所以她萌发了冲出那个顽固家庭的革命要求,并在很短时间内变成了另一个人。她那洗去了愁闷的红润面颊、举手敬礼的大方姿态以及用“德文”做的回答,都是新时代战胜旧时代的胜利标帜里王振中,这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农村教育出来的第一批新的女性中的一个。3、《刑兰》主人公邢兰“他身长不到五尺,脸上没有胡须,手脚举动活象一个孩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对抗日工作表现了非凡的热倩和精力,作者写他如何在白夭劳动,夜间主动做侦察工作,如何从坡下硬是将一条大树干扛上来。他的矮小的外表是旧时代造成的,而他的特别旺盛的革命精力,却是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抗日战争诱发出来的。可以说,邢兰是以旧时代的控诉者和新时代的开拓者的双重身份活跃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的一个人物。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个人的遭遇》、《解放》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描写中国革命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 冯德英的《苦菜花》、 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 吴强的《红日》、 冯志的《敌后武工队》 吴承恩的《三国演义》全文19分享1踩上海七猫文化传媒有2020-10-10关于军事的小说全本,免费在线看小说,不用花一分钱,立即下载APP!广告199******112019-11-08关注
写作背景:从1939年到1950年,作者在抗日时期同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日、并与当地地主等恶势力进行斗争,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犁毅然投身抗战,在平汉路西的山里工作,听到从冀中平原的同志向他讲过两个战斗故事,其中一个是关于白洋淀青年组成雁翎队,这个素材触发了孙犁的创作灵感。文中景物描写清新自如,情景交融,意境优美,富有诗情画意。故事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年代,作者没有描写残垣断壁、生灵涂炭的场景,也没有描写金戈铁马的厮杀,而是着意于荷花淀的旖旎风光,以妇女们的从容谈笑显示出风云的变幻。抒情的笔调,乐观的画面,使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小说中的景物描写,既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又为人物的活动提动了典型环境。扩展资料《白洋淀纪事》主要内容简介: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地区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展现了纯美的人性,也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绝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他那种寂寞冷清的状态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他所期盼的,他是现代社会的一位“大隐”。他后半生恪守文人的清高和清贫。这是文坛上的一声绝响,让我们后来人高山仰止。孙犁,1913-2002, 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县人。 孙犁一生笔耕不辍,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作品特点熔写景、抒情于一炉,充满诗情画意被称作“诗体小说”。产生极大影响,形成数量可观的“河北作家群——白洋淀派(菏花淀派)”。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短篇小说《荷花淀》、散文集《津门小记》、论文集《文学短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