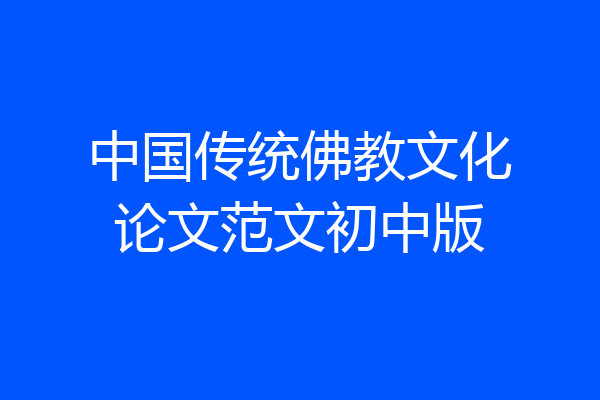kepler123
kepler123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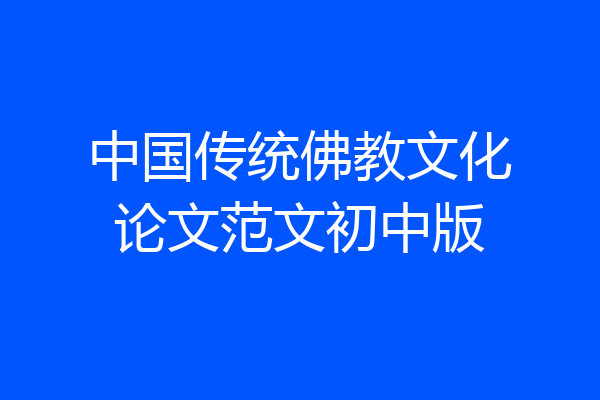
论文一:把佛教精神融入企业文化 佛教精神不是简单的佛教教义,而是佛教信仰者身上所具有的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在具有深厚东方文化传统的中国,这种处世态度对于建立和完善企业文化有着许多积极意义。以下即是就佛教精神对于企业文化的积极意义所作的阐述: 1、经世济众 为自己和别人解脱痛苦,是佛教蕴含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佛教的自力拯救不能理解为只追求自我个人的解脱,佛经说:“惟行菩萨行者得成佛,其修独觉禅者永不得成佛。”佛理说佛与众生同出一源,本为一体,怎能一独悟而众生迷?所以佛教根本上兼济天下而非独善其身,要求把自我拯救建立在每个人的努力并引导众生共同努力的基础上。自度度他、自济济人,或说通过超度他人以求得自己的超度,通过救济别人以求得自己的救济,这是佛教中经世济众的基本精神。 作为社会组织之一的企业,应该吸纳经世济众的精神,把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作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虽然企业的组织目的就是赢利,但并不表明企业以赢利为唯一目的和准则。其一,企业可以通过其用以获利的产品来给别人带来思想、身体上的解脱,对于企业的经营方式、所经营的产品,都要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香港李嘉诚先生就曾经力排众议,否决开设赌场的董事会提案。企业经营的产品只有是利他的才会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才会给企业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带来更稳健的经营风格,才能使企业获得更长期的利润。其二,企业通过赢利来帮助企业员工以及社会解脱痛苦、寻求快乐。而企业员工和社会得到企业的帮助后,会自然而然地信奉企业本身所倡导的一些思想和理念。企业树立了经世济众的精神后,通过一定的途径,让企业员工和社会知晓、认同这些精神,会为企业本身的经营带来极大帮助。无论是金蝶“发展软件产业、振兴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还是商务通“科技让人更轻松”的温情关怀,都会激发企业员工的使命感,使员工工作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同时也会使社会对企业本身给予更多的信赖,以利于企业自身发展。 2、众生平等 佛教教义不要求人绝对服从于某种意志或力量,在佛教中,没有创世者与被创造者,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佛教中佛与佛弟子的关系,不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而是先觉与后觉、师与徒的关系。释迦佛创立了僧团组织后,没有以领袖自居,而是把自己当成僧团中的一员,与普通僧众一道,持钵乞食,赤足云游。(引自《阿含经》)佛陀之所以提倡众生平等,按佛经佛理所言,在于众生皆有佛性,与佛本来平等一体。依据现代组织论的原则是,每个人在这个组织中都是平等的,只是在组织中的分工不同。佛只存有大慈大悲之心,而绝无主宰支配众生的意图。而在佛教徒心目中,佛虽福慧双圆、神通广大、自在逍遥、至尊无上、功德无量,却毫无领导者、主宰者的威慑性,而是可亲可敬、可学可效的。在佛教中,佛与人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人人可以成佛。众生平等是佛教的又一特质和基本精神。 对于企业文化而言,众生平等应该作为其基本精神之一,应倡导企业内部员工平等相侍。企业的创立者并非绝对神圣,他可以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作为企业里最早为该企业寻找到生存和发展途径,并引导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角色。企业的各级领导者是各级团队中具有不同分工,承担不同任务的普通一员,领导者不是带领团队去执行他所决策和定义的工作目标,而是与团队的其他人员一道去共同实现大家所认可的工作目标。每位员工都有权利和义务去定义所属团队的目标,也有权利去否决他所在团队的工作目标。在企业里扁平化管理模式应取代A型管理模式,互助观应取代领导观。除平等相待外,企业应尊重每位员工在企业的发展权利,在企业文化里要突出每位员工,无论资历深浅、能力大小,只要自己不断努力,都有可能成为领导的观念。每位领导都是帮助员工成功的兄长和朋友,每位员工都希望成为领导,以帮助更多的员工成功,这样的企业没有理由不发展壮大。海尔提出了著名的“赛马场”策略,使海尔的每位员工都有公平感、成就感,也使海尔的诸多才俊脱颖而出,他们为海尔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3.弃恶从善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佛教的基本主张,虽然许多宗教都有弃恶从善的主张,但佛教的弃恶从善有独特内容。佛教的善恶观是绝对的善恶观,并附有因果报应说。佛教中的弃恶从善主要包括以下几层意思:一、善恶是从心里滋生出来的,人心的本性无善无恶,因一时的念头所引起的真妄及其衍生的善恶均没有实性,“真赅妄本,妄彻真源”,由此善恶不过是真妄分别而导致的后果。二、善恶是可以转化的,去妄存真、弃恶从善是有内在根据的。三、善恶是绝对客观的,没有任何理由或借某种名义,可以行恶而以之为荣。在佛教那里,不可能以佛的名义去征服所谓蛮族,也不可能以佛的名义去屠杀异教徒。善恶是自明的,永远不可能由人自己去做论释。四、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在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这六道轮回中,是上升还是堕落,取决于人自身。总之,以绝对善恶观为核心的劝善止恶是佛教的又一特质和基本精神。 对于企业文化而言,对应于佛教精神,弃恶从善有以下意义:一、员工本质没有好坏之分,本性没有善恶之分,当他行善时便是行善了,当他行恶时便是行恶了。因此著名的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 Gregor)的人性假设理论应受到挑战,如果持X理论(即人性本恶),就忽略了人从善的根基,如果持Y理论(人性本善),就会缺乏弃恶的主动性。在建设和宣导企业文化时应充分考虑员工从善的根基,并引导员工主动弃恶。二、善恶是可以转化的,对于曾经违反过企业法规的员工不是简单摒弃,而是努力帮助教化;对于曾经为企业带来过利益的员工不能盲目信赖,松懈对其管理和教化。同时,要根据企业员工的善恶行为现象,从企业文化自身去寻找根源,对于能够带来好现象的文化精神要发扬,对于会带来不好现象的文化精神要抛弃。并且注意在企业文化里应包含更多的宽容精神和引导观念。三、员工出现违反企业规章,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不要轻信其辩解,错了就是错了,即便是好心办了坏事也得受到处罚或谴责。同时注意在企业文化里不要掺杂攻击和蔑视其他企业即便是竞争对手的成分,企业员工和企业本身应树立起自觉与所在的社区和所处行业友善相处的精神。四、企业应渗透奖罚的道德和制度体系,让因果报应说在企业文化里具有全新内容,并得以提升到新的高度。 4.重智尚真 佛教作为宗教,希望寻求的是人的终极归宿,但是佛教却不是一种盲目信仰的宗教。佛教强调发挥人本身具有的智慧,通过现象来看本质,洞彻声色,证悟真如。佛教之所以重智尚真,在于佛教自认为其所认知或了悟的是客观的真理。佛祖不是真理的创造者,只不过是真理的发现者。“如来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引自《阿含经》),所以佛教更强调“以法为师”。佛教所崇拜的是“真如”,而不是佛祖,由此禅宗才敢于唾佛骂祖。佛教如此重智尚真,因而也很重视理性和实证。虽然佛教之所谓客观仍逃脱不了“万法唯心”的范畴,但佛教徒常会不自觉地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圭臬。这与其他宗教的神秘主义截然不同。 重智尚真对于企业文化的价值,显然不在于其“万法唯心”的主张,而在于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不为事物表象所迷惑,崇尚真理、质问权威的精神。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是企业永葆青春的法宝,3M公司为了激励员工的主观创造能力,设立了自己的诺贝尔奖——金步奖。在IBM一些富有成果的工程师拿着和总裁一样高的薪水,这些都是企业为了鼓励主观能动性而采取的措施。在企业文化里应明确一点,企业在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管理制度方面永远没有完全了悟其所有真谛、到达终级目标,还有许多本来就存在的资源和潜力没有被我们利用和挖掘,以此来激励企业员工借助自己的智慧不断探求和接近各自工作领域的真理。对于企业内部乃至行业内的权威,虽不赞成去唾骂,但也要敢于去质问和挑战。在企业文化中应该鼓励员工去发现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错误和缺陷,并及时去修补。对于企业已有的文化,要不断地在企业经营中去加以检验,以便适当扬弃。敢于对企业已经形成的企业文化挑战,是企业文化中重智尚真的重要体现。 纵览古今,很多佛教信仰者以特有的佛教精神为人处事,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同样有很多人借助佛教精神建立起特有的企业文化,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自身的独特魅力,为打造百年老店奠定深厚的企业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