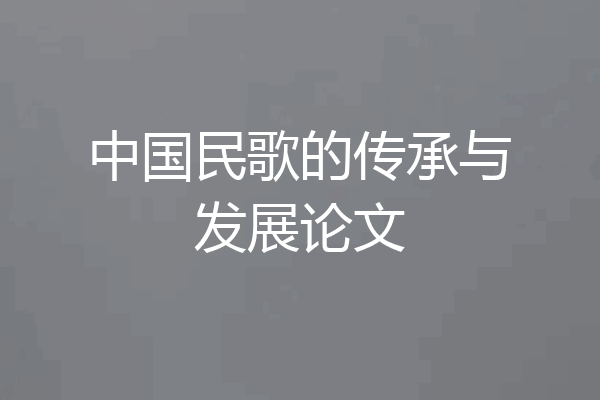tlsshh
tlsshh
音乐永远是民族文化中的那唯美的一面,在乐器的缓缓鸣奏中,表达的是作者的情感,无形之中乐曲的深处流淌着的是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精髓。。。每每听着古典音乐的响起,那种悠扬,那种独特的中国风,心灵深处的有着不一样的触动,虽然听不出《高山流水》的知音难觅,品不到《春江花月夜》的清丽奇幻;但是依旧为凄凉忧伤的《二泉映月》而伤怀,被《霸王别姬》的悲凉豪迈而震撼。。。。他们再现了古代的情感生活,过往的抑郁悲愤,那时的英雄儿女,跨时代的哲理思考,都是那么地多情,那么的发人深省。 中国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到殷周奴隶主统治的时代,音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不断得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 中国民族音乐基本上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四部分构成。 宫廷音乐:一部分是典制性音乐,如各类祭祀乐、凯歌乐、朝会乐等;另一部分是娱乐性音乐,如各种筵宴乐、行幸乐。这两大部分音乐体现了宫廷贵族文化的两个侧面,一是皇权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贵族阶层的精神享乐。 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与词调音乐,它与书、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琴、棋、书、画,琴居首位。古琴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远”的浪漫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和”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 宗教音乐:一、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点,佛教、道教、基督教、萨满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宗教音乐各有特征; 二、外来的宗教带来的外来音乐和乐器不断与本土音乐的融和; 三、较浓的民间风格,大量的宗教音乐以民间歌曲为基础加以改动使之仪式 化、教仪化。 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以综合艺术为主。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体裁、形式、风格、内容,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 如今古典民族音乐的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历来重视音乐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普通教育中将音乐作为正规课程列入期间,则是清末才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以“请开学校折”上书光绪帝,提出了废八股遍设学校的主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此后几年间,新式学堂陆续开设了唱歌课,从而在普通学校中形成了以教授新式歌曲和欧洲音乐常识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教育,至此,学堂乐歌成为我国一个新文化即将实行切换的关键时期。1927年采用德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建立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均依照德国音乐院校的课程内容上课,学生们演奏我国传统乐器也是用现代方法演奏。 当时以西方音乐为主体的中国学校音乐教育虽然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中国音乐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未能把传承中国音乐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因而对多数教育者来说,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阻隔和影响。虽然在各个方面做了一些有利措施,但从学校音乐教育的整体来看,民族音乐尚未能取得其应有的主体地位。这不仅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今后的民族音乐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体制和观念及外来文化的侵入,使得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教育传承之间存在割裂、脱节现象,这就造成了国民对民族音乐的不重视,而使民族音乐文化处于不断滑坡状态。因此,学校教育应该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大历史使命。 民族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种文化形式的综和,同时又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音乐文化里包括了多种文化,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各种类型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现象,其中也体现了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文化、民俗、语言、美学观点,同时也寄托了一种文化的情思,其所涵盖的情感和精神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与思想,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载体。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这样说过:“民族传统有机的继承,唯有从我们的民间音乐中才能找到。”意思是说,作为文化的民族民间音乐具有继承的价值,民族音乐教育同时也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意义。 音乐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民族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教育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的教育是不可行的,没有教育的文化就失去了它的实际存在价值,教育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的音乐教育是分不开的。 毋庸置疑,民族音乐文化在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几千年来的中国音乐史及现代的音乐教育现状看,我国音乐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提高,必须以中华民族本土音乐为主,如果把西方或者其他流行音乐当成主流,而将民族音乐作为附庸的话,必然会带来民族音乐衰退乃至消亡。学校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要使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得以很好地传承,就要强调民族音乐教育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所以要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改善教育措施是关键。 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传统民间音乐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就像我们的母亲河每年断流一样,民间音乐中的许多品种也出现了断流,濒临绝灭。流行音乐充斥着中小学音乐课堂,民族音乐教育被忽视。专业艺术院校招生和业余器乐考级中,报考西洋乐器和报考民族乐器的人数惊人的悬殊。更令人痛心的是多数学生都不会欣赏民族音乐的美,甚至对教材中的民族音乐持排斥态度。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用历史追朔法分析这些现象不难发现: (一)近二十年来受外来文化、市场经济的影响,各种媒体播放民族音乐的比例较少,流行音乐所占比例较大,加上港台流行音乐的推波助澜,使得很大一部分学生趋之若鹜。致使我们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追星族与歌迷越来越多,而民族音乐的爱好者却越来越少。青年学生只知道四大天王、超级女生,对民族音乐知识可以说了解甚少,说不出几种民族乐器的名称、叫不出几位中国民族音乐家的姓名; (二)应试教育长期不重视音乐教育,音乐课的情况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指导音乐教学。致使音乐教育无法执行教学大纲,更无法完成规定的内容。音乐教学科研不足,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模式没有改变,致使学生对音乐课丧失兴趣。 二、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具体措施 长此以往,没有青少年对民族音乐的喜爱和发扬光大,民族音乐将会失去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发展民族音乐教育,提高民族音乐素养”显得尤为重要。学校责无旁贷地成了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振兴民族音乐的主要阵地。在教学中发挥民族音乐教育的优势,陶冶学生情操,增强民族意识,让绚丽璀璨的民族音乐自立于世界之林,乃是当前音乐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怎样落实呢我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点抓起: (一)以情感教育为主线,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深厚感情。通过学习一些带有典型民族风味的歌曲,在掌握和灌输民族音乐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明白音乐离不开民歌,民歌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的道理,使学生从心理上崇拜民族音乐,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感情。我国民歌浩若烟海,内蒙民歌的豪放、辽阔,江南民歌的婉转、秀丽,陕北民歌的高亢、奔放,云南民歌的明丽、清新,新疆民歌的活泼、欢快,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从中得到丰富的体验,体味到各民族的风俗民情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学生对这些民歌创作根源的追溯,会对民族音乐产生由衷的热爱之情。有了这样美好的感情,就会对学习民族音乐产生浓郁的兴趣,为学校进一步实施民族音乐教育打下浓厚的情感基础。 (二)以民族音乐的欣赏为契机,增强学生的体验能力,体验民族音乐所塑造的意境,开拓学生的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以学生自我感受为基础,启发学生展开形象的翅膀,令学生将民乐与自我的情感认识不断协调起来,使民乐的欣赏成为学生情感体验的活动,在此活动中令学生自我振奋、自我感动。教师有意识地选择欣赏曲目,做到有浅到深、由表及里地对学生实施教育。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怀着由衷的喜悦去吸收民族音乐的营养,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 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很有市场前景,关键是要有好的作品和市场运作。我认为,当前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存在着创作和市场两个问题,需要下大功夫解决。“中国民族音乐的作品不够丰富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由于民族管弦乐的乐器和编制的特性,你不能用西洋的配器方式来写中国民乐作品,而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有许多却还是从西洋乐团的配器移植过来的,这样的作品并不适合民族乐团演奏。民族音乐的市场开发问题也十分明显,从我们在欧洲和美国的演出看,实际上民族音乐有市场,但国内缺少推广民族音乐的机制,没有专门的人才和经纪公司向世界各地推广中国民族音乐。” 古典民族音乐的传承也许还要走很远,但是我们必须不停的寻找契机,为民族的文化作出应有的保护,更要作出应有的创新,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去认识我们的音乐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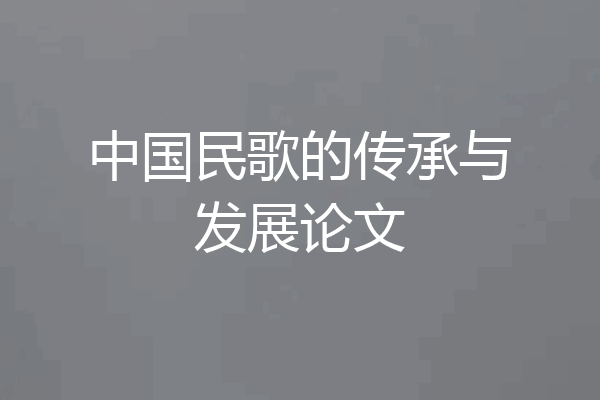
中国古代民歌的传承与发展,可以分为民间歌谣、骚体诗、乐府民歌和杂言诗四种基本体裁。 诗歌是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体裁,产生在有文字记载的文学产生之前,和音乐、舞蹈一体。由於没有文字媒体辅助记载记忆,这种文学体裁要求语言既精练又形象,音调要和谐,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韵律。 诗歌的原始形态是民间歌谣。在今天看来,最早的民间歌谣的艺术特徵是朴实无华,它只具备诗歌形式的基本内涵,而在音调的模式、节奏的类型、韵律的规则等方面都没有定式,这就决定了它是最彻底的自由诗。民间歌谣的自由属性还表现在具体作品的不定状态。一首民间歌谣被创作出来以后,是通过口耳相传得以保留的。在传播当中,人们会对其中的句子、用词、节奏、韵律等作一些修正,使之在艺术和思想上更具感染力,所以它具有集体创作的性质。后世的民间歌谣,一方面继承著传统的某些要素,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拘泥於传统所有要素,只要表达需要,它们就往往突破传统,产生新的形式,这些新的形式,当然有优秀的,也有低劣的,低劣的很快就被淘汰了,而优秀的则被广泛的模仿定型为新的典型模式。 民间歌谣是孕育诗人和正统诗歌的摇篮。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诗人及名著,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民间歌谣汲取营养后,经过对生活实践的感受、认识、理解与思考,运用传统与创新相结合艺术手法加以表现而产生的。 上古时代,民间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被记录在先秦的经史子集中保留下来的很少。这些记录,不排除有所加工润色,但是其基本风貌应该说还是得到了保留。清代大学者沈德潜编辑的《古诗源》中,选录了《古逸》103首,其中一部分是上古民谣,如《击壤歌》、《康衢谣》等,还有一部分是《诗经》以外的周代民歌。上古民间歌谣,与后世的诗歌相比,句子不受字数限制,篇幅不受行数限制,用韵位置不固定,韵律也很自由,这是其共性。但上古民间歌谣也有一些个性: 1、与音乐保持著密切的联系,是唱的,而不是诵的,是歌词,而不是狭义的诗; 2、四言句最多,占主导地位; 3、每篇行数以双数的居多; 4、出现了三言句、五言句、六言句和七言句,有杂言倾向; 5、出现了骚体诗的雏形。 上述这些特徵,可以说明四言诗为什麽会成为中国诗歌最早的正统体裁,也可以说明汉乐府民歌为什麽会有明显的杂言倾向;又可以说明为什麽在《诗经》之后会有骚体诗兴起。 由於四言句式是上古民间歌谣的基本形式,所以自《诗经》起,四言诗首先登上了正统诗歌的宝座。四言诗只有两个双音步,没有单音步,在节奏上死板,在表达的空间上局促,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些缺点便越来越明显。为了表达的需要,也为了节奏富於变化,屈原第一个学习南方民歌和上古歌谣中的一唱三叹的句式,创作了篇幅宏大、数量可观的骚体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自觉的诗体革命,他与四言正体分庭抗礼,其作品的基本艺术形式在汉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项羽、刘邦、刘彻,都有过骚体诗作,汉代一些有影响的文人,在创作四言诗的同时,也大量尝试骚体诗,使屈原的骚体革命得到了继承和推广。汉代这些骚体诗,表达方式多平铺直敍,修辞手法也不如屈原那样丰富多彩。最有成就的还是汉末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关於这组诗歌是否蔡作,学术界颇多不同见解,但从这个作品大致产生於那个时代和它对后世的影响的角度看,无论是否蔡作,并不损伤它的历史地位。骚体诗的另一条支脉在两汉变成了散文化的“赋”,到六朝时代进一步演变成既区别於诗歌又区别於散文的骈体文,已经同诗歌分道扬镳了。所以此后保留原有风格的骚体诗越来越少,到唐代李白等人之后,就寥若晨星了。 骚体诗有以下两个特点: 1、用叹词“兮”连接两小句构成一个较长的句子,或者放在句子末尾,连接下一句,使诗句更有节奏感和音乐性。 2、句式突破了四言正体,向三言小句方向(如《国殇》)和五言句型(如《东君》)、七言长句(如《橘颂》)方向变革。 骚体形式的出现,无论其所表现的创造性、突破性,还是其句式有意识有规律的增损,都为汉代乐府民歌及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的产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乐府民歌与民间歌谣的不同,在於它是被官方加工和认可过的。其实,就其本质意义而言,《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也是乐府民歌,只是那时还没有出现“乐府”这个概念和名词,所以十五国风不叫做乐府民歌。汉武帝创建乐府,作为宫廷礼仪的音乐机构和从民间采风的专门机构,后来渐把这个机构创作的歌曲和采集加工的民歌称为乐府,才有了乐府民歌这个新的诗歌体裁称谓。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经过多次加工的民歌,其民间性已经被淡化,因而表现为四言诗句的压倒多数;汉代乐府民歌则不同,它只经过了一次性的加工,因而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本色。 南朝时期沿用了汉代的体制,官方依然注重从民间采风,所以这一时代也有许多民歌得以保留传世。隋唐以后,正统诗歌完全居於统治地位,采风也不再是官方统一组织的社会活动了,但民间的与音乐密切相连的歌词却在不断产生并广泛流传。由於乐曲的存在,按照曲调所提供的乐句填词成为风气,后人把曲子词叫做近体乐府,是有道理的。 乐府民歌的出现有两大意义: 1、被官方采集加工过的民歌,经过了文人的加工润色,其艺术价值超过了民歌的原始状态; 2、被官方采集加工过的民歌的广泛传播,使民歌中的最新艺术成就,能够被众多的文人借鉴,使个别的艺术进步变为全社会的历史性的艺术进步。 乐府民歌由於保留了民间创作的基本艺术成就,对於正统诗体来说是一场变革。这种变革对於正统诗歌形式的突破,使之成为自由性质的诗体。汉代的乐府民歌,五言体和杂言体交相辉映,是继承上古歌谣中杂言倾向的传统,是对四言正体句式的平行扩张和参差损益两种倾向的结果,前者带有改良意味,后者代表变革趋势。 乐府民歌的出现,是新的正统诗体形成的基础。周代民歌,更远一点说上古民谣,他们的基本句式决定了四言诗的形成;汉代乐府民歌中所产生的基本句式,决定了五言诗的形成;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基本句式的扩张,则决定了七言诗的形成。 杂言诗是真正的自由诗,这种自由是由自发到自觉发展起来的。杂言诗在自发阶段朴实自然,还没有割断与散文之间的联系,而到了自觉阶段则生动活泼,在变化中表现音韵、节奏和句式和谐统一的规律性。自觉的杂言诗,实际上比半自由诗难作。杂言诗句式的转换,要能够於变化中存统一,於错杂中见和谐,所以它不能藏拙。中国传统诗歌中,文人的杂言诗很少,成功之作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可见高度自由的诗要作得好,甚至比严格的律诗还难。 杂言诗的发展主要是在民间进行的,它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上古歌谣,而汉代乐府民歌则是它的第一次繁荣。到了唐代,在近体诗鼎盛发展的正统诗歌黄金时代,在民间则悄悄地兴起了杂言的曲子词,这是杂言诗第二次繁荣的序幕。杂言诗的自由性,是对正统诗体的挑战,而杂言诗一旦被文人所普遍模仿,它就失去了自由的属性,成了新格律诗,按谱填词填曲,就不再是自由的杂言诗了,而是严格的格律诗了。 亢 民间歌谣 民间歌谣是诗歌发展的源泉。这不仅仅是从诗歌的发端意义上讲,而且在诗歌的流变中依然起著积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一切传统诗体的产生,无不得益於民间歌谣中的最新艺术成就。民间歌谣的基本特徵是:它既保持著以往艺术形式的基本传统,又不以这些形式为桎梏,为了表现上的需要,它总是积极地、顺乎自然地对其有所突破。 上古时代的民间歌谣,保持了四言句式占主导地位的原有基本传统,但在需要的情况下往往突破。如《击壤歌》,其前四句完全是整齐的四言,而在结尾,则突然出现了七言句,增加了表现力,使全首诗在艺术上升华。如果用两句四言句结尾,变成“帝力於我,有何益哉”,艺术上就大为逊色了。再如《南风歌》,如果用四言正体也是可以作出的:“南风之熏,解吾民愠;南风之时,阜吾民财”但在艺术感染力上,就远不如原诗一唱三叹的骚体句式那麽强烈了。 两汉乐府民歌是在骚体诗产生之后出现的,它的自由和突破,是相对於四言诗和骚体诗而言的。如《有所思》,也可以用四言诗体:“我有所思,在大海南。何用遗君,玳瑁珠簪。……”但风格上就显得很陈腐了,没有新鲜感,意境也远不如原诗。再如《战城南》,也可以用骚体来写:“战城南兮死郭北,野死不葬兮乌可食;为我谓乌兮且为客号。……”但在风格上则显得凄婉有余而悲愤不足。可见,所谓自由,并不是为了自由而自由,而是为了艺术表现力的增强而自由。民歌对传统形式的突破,莫不以此为原则。这两首乐府民歌,是最能保持民歌风貌的,文人加工的痕迹绝少,可以作为民间歌谣来认识。 东周时的歌谣《饭牛歌》是从《淮南子》上摘录下来的,未必是甯戚的原作,但是至少代表了西汉时的诗歌水平,应当早於张衡的《四愁诗》,代表了最早的七言歌行。它是对骚体诗的突破,基本去掉了叹词“兮”。此后的歌谣中,出现的七言形式越来越多,如《临河歌》、《楚聘歌》、《巴谣歌》等,也出现了《匈奴歌》这样的五七言相交的杂言诗,为文人的七言、杂言歌行的出现提供了营养。 在民间歌谣和文人歌行的相互借鉴、相互推动中,七言四句的“乐府”诗得到了发展。说它是“乐府”诗,不仅是因为它有浓厚的民歌特色,还因为它们是合乐的歌词,也是为了和唐代出现的律体七绝相区别。因为这种“乐府”不太讲究粘对,其对偶性和音乐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风格。到了隋代的《送别歌》,已经发展成与七言律绝完全相同的艺术形式了: 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 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其平仄结构完全是一首仄起式首句入韵的七言律绝,而且首联用了对仗,其句法、章法与唐代七言律绝佳作相比了无逊色。可以认为,这种“乐府”是唐人七绝之母。 《送别诗》这种体裁,后来向著三个方面发展:一是七言律绝,二是通俗活泼的《竹枝词》、《折杨柳》等民歌,三是增损变化个别句式,向《渔歌子》、《捣练子》之类的曲子词小令方向演变。而第二种则作为民歌的正宗形式一直流传到现代略无衰减。 盛唐时代李白、王维、王昌龄等诗人的七言绝句,有些是律体,有些则是“乐府”体。这种七言“乐府”,对於此前500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五言诗而言,是自由的、非正统的,而其艺术表现力则往往超过五言诗,其节奏、韵律、平仄变化,也逐步向规律化方向发展。 唐代的民间歌谣,一部分突破了其既往500余年五言、七言整齐句式为主流的传统,发扬了从上古民谣到《诗经》楚辞和汉魏六朝乐府的杂言倾向,从而产生了曲子词。不过这时的曲子词不是后来的格律化的歌词,而是完全自由或基本自由的,在依据现成音乐曲调的基本前提下,句子中的字数是不完全确定的,也不受平仄的限制。在“词”和“曲”被格律化以后,民间的“挂枝”、“寄生草”之类的歌谣仍然保持著这种既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品格。 氐 骚体诗 骚体诗得名於屈原的《离骚》,而且在这种诗体创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者也是屈原。但骚体诗毕竟不是屈原独创的,他只是这种诗体的集大成者。 骚体诗萌芽於上古。最早的一唱三叹式的诗歌,有文字可考的是《尚书》所载的《卿云歌》: 卿云灿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早期文献中记载的这种形式的诗歌还有《南风歌》、《采薇歌》、《孺子歌》等等: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南风歌》(载於《家语》,舜帝弹五弦琴所歌) 登彼西山,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孺子歌》(载於《史记》。春秋末年楚国民歌) 其定型时代已经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形式的诗歌代表著上古诗歌的一个体裁流派。《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差不多都有这种形式的作品:如《周南》中的《麟之趾》;《邶风》中的《绿衣》、《旄丘》、《简兮》;《卫风》中的《淇奥》;《郑风》中的《缁衣》、《将仲子》、《遵大路》、《狡童》、《丰》;《齐风》中的《还》、《东方之日》、《猗嗟》;《魏风》中的《十亩之间》、《伐檀》;《陈风》中的《宛丘》、《月出》;等等,都是骚体诗的渊源,可见这种体裁的雏形出现,远远早於屈原。 但是,屈原以前的“骚体诗”,除了一唱三叹的“兮”之外,还是与四言诗有著密切的联系,因为其基本句型还是四言的。屈原的楚辞则不同,它打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创建了五言、七言句的基本雏形。《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少司命》、《东君》、《河泊》,开创了五言体的基本模式。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及,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恻。 桂棹兮兰枻,斲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石濑兮浅浅,龙飞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鼂骋骛兮江臯,夕弭节兮北渚。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屈原《九歌•湘君》 这些诗都基本具备了七言歌行的体制,而到了张衡的《四愁诗》,已经基本上从骚体脱胎而出,成了七言歌行了。 以贾谊为代表的汉赋,把骚体诗引向了骈体散文。他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是四言体与骚体的结合,与屈原的楚辞有明显的区别,尽管它们保留了诗歌的一些要素,但已经有了较强的散文化倾向。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以六言句式为主,句法更接近於《离骚》,也还保留著诗歌的特点,但已经是近似於散文的句式。司马相如的这种风格,在蔡邕的《述行赋》、弥衡的《鹦鹉赋》、王粲的《登楼赋》中得到了继承。再往后,就很少有人作这种风格的“赋”了。唐代李白的《惜余春赋》、《悲清秋赋》,可称这种风格的余响。而自扬雄的《酒箴》、张衡的《归田赋》起,已经完全从楚辞中脱胎出来,变成了四六句的讲平仄、压韵的骈体文。从此后,骈体文开始流行,与诗歌参商分野。值得一提的是,在骈体文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使平仄、对仗得到发展,反过来又对诗歌的艺术形式探索产生了新的影响:六朝的诗歌逐渐讲究对偶和声律,到了唐代,这些艺术成就又回报了律诗的形成;在两宋,也对许多散文化长调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 作为诗歌的一种体裁,骚体诗本身在后世发展不明显。但是,在历代诗人中,还是有人运用。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就是一例。学术界一般认为《胡笳十八拍》不是蔡琰所作,但又无法考证出自何人之手。而《胡笳十八拍》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则是较大的,不妨暂寄蔡琰名下。 唐代是历史上诗歌最繁荣的时代,在大量涌现新体诗歌的同时,也有不少人沿用骚体创作:如卢照邻的《狱中学骚体》,王维的《双鸿鹄歌送别》,李白的《代寄情楚辞体》,韦应物《萼绿华歌》,元结的《怀潜君》,韩愈的《拘幽操》,元稹的《有酒十章》,等等。甚至有人专工骚体,如卢鸿一,《全唐诗》所收其作品全部都是骚体。 骚体诗不仅对汉民族文学有深刻的影响,甚至对少数民族文学也产生过影响。辽道宗耶律洪基的皇后萧观音曾经写过一首骚体《绝命词》: ……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共西耀兮将坠,忽吾去乎椒房。呼天地兮惨悴,恨古今兮安极;知吾生兮必死,又何爱兮旦夕。 在中唐以后近体诗占统治地位的1000多年间,作骚体诗的传统,象一股涓涓溪流,一直没有断绝,我们看《红楼梦》,贾宝玉在祭奠晴雯时所作的一首诗歌《芙蓉女儿诔》,就是骚体。 房 乐府民歌 乐府民歌得名於西汉。汉武帝刘彻设置中央音乐诗歌官署,名叫乐府,任用宦官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一方面采集、加工、整理、编辑民间诗歌,一方面管理宫廷音乐,组织文人创作诗赋。后来,又把这个官署刊定的民歌称为乐府民歌。就其本质而言,《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也属於“乐府民歌”。 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冲破了占据霸主地位1000多年的四言正体,产生了以五言为主流的新体裁,奠定了“选体” 五言诗在魏晋至盛唐统治的基础,同时也开创了七言诗、杂言诗的先河。 《江南》、《长歌行》、《君子行》、《枯鱼过河泣》等五言抒情小诗的出现,开了《古诗十九首》的先声。 《艳歌行》、《十五从军征》、《饮马长城窟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五言敍事诗的出现,则代表了上下近1500百年的最高艺术成就。特别是《孔雀东南飞》,下及唐宋元明清,鲜有可与相敌的文人作品。 《战城南》、《有所思》、《上邪》等杂言抒情小诗,和北朝民歌《木兰诗》这样的杂言敍事诗,则堪称500年独步。它们体现了成熟的五、七言完善结合的自由奔放、和谐流畅的境界,盛唐以前,文人绝少登堂入室者。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主要成就,是大量创作了五言、七言绝句,为唐代绝句的繁荣充当了基石。自晋《白紵辞》起,七言诗复兴,至唐代达到鼎盛。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诗经》中的杂言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四言为基调,点缀少数三言、五言、六言句式。如《王风•扬之水》: 扬之水,不流束薪。 彼其君子,不与我戍申。 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这首诗分三章,句式组合结构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国风是配乐而歌的,所以节奏型各段间相同。 另一种是完全突破四言模式的,在句数上也出现了奇数句为段的情况。如《秦风•权舆》: 于我乎夏屋渠渠, 今也每食无余。 于嗟乎不承权舆。 这首诗是两章,句式组合结构前后段相同,它没有四言句,也不是完全的七言句。 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徵是因循守旧,特别是正统派的上层文人。一种艺术形式一旦定型,固守其制便为正统潮流。汉代的正统诗体是四言诗,而传世的汉代四言诗,几乎无可褒奖,因为这种体裁过於陈旧,加上思想性的不足,所以佳作罕见。民歌则不同,它反映的生活是有血有肉的,具有时代的典型性;它所采用的艺术形式是自由的,具有启发性。所以在汉代的乐府民歌中,出现了《战城南》、《有所思》、《上邪》这样的千古佳作。而这种形式的出现,则开辟了比四言、五言、七言诗更加久远的艺术创作天地。虽然在唐代以前,杂言诗从数量上看成就不高,但在现代及未来中国诗歌的发展中,必将会超越其他任何传统体裁。曲子词、北曲的繁荣,就是最好的实例。 屈原之后第一个专门向民歌学习艺术成就的士大夫是李延年。李延年作为汉武帝的协律都尉,接触和了解民歌之多之深,是当时其他文人士大夫所不可比的,所以他能最先冲破传统,接受和模仿之。他的《北方有佳人》六句中只有一句是突破五言句式的变例,却使全诗变得异常生动活泼。 李延年之后,杂言诗在文人中杳无声息。此后二百余年,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和曹植的《当墙欲高行》,才使李延年的首开先例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以五言句式为基调,中间大量穿插七言句式,变化生动而自然,比李延年大大地进了一步。 曹植的《当墙欲高行》,则是以七言为基调的,中间六言、四言、五言句式与七言句式相互转换,又比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显得活泼,但由於四言句过多,散文味道略觉明显。 六朝最有成就的杂言诗作者是鲍照。鲍照极为注重学习汉以来的乐府民歌,把文人五言诗的艺术成就同七言民歌的艺术手法结合起来,作了大量的拟乐府民歌旧题的杂言诗。《拟行路难》18首中,有5首是杂言。第四首以上五下七为基本格调,生动活泼(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中,间有此种结构,但未成主旋,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开头四句就用了这种格调)。第四首以上五下七起,接下来忽七七,忽五五,变化流畅。第六首五言起,双句意尤未尽时,突出三句组,跳跃跌宕。收尾联又出九言句,出乎意料而顺乎自然。 鲍照之后,陆厥颇有成就。他的《临江王节士歌》,三五七言交替,使一首短诗变得特别生动活泼,而又完全没有散文意味,是成熟的杂言体制。 杂言诗最难作。难在要求作者对传统的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乐府民歌、骚体诗的变化规律,必须达到融会贯通,使诗的句式、章法、音韵,变化得既自由奔放,又要自然流畅,不能有拼凑的痕迹。杂言诗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要求诗人的创作,不拘原有模式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要的是天才之力。有人说:“第一个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才”,临摹比创意要容易得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循守旧,使人往往缺少创新的胆量,加上能力的不足,就使自由体的杂言诗发展受到了局限。人们作诗,不但在题材、意境上类比古人,而且在体裁上也一味地类比古人,这正是中国诗歌形式变化缓慢的原因。 幸而有天才。倘使没有天才的创造,中国诗歌至今依然停留在《诗经》的四言正体上,那会是多麽可悲的结果呢?
起源和发展 民歌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民歌,即民间歌谣,属于民间文学中的一种形式,能够歌唱或吟诵,多为韵文。 民歌是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语言艺术之一。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音乐,唱出了最早的民间歌曲——劳动号子。原始的民歌,同人们的生存斗争密切相关,或表达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猎获野兽的欢快,或祈祷万物神灵的保佑,它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和社会制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广,其社会作用也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诗经》中的《国风》,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民歌选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约500多年间,流传于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国风》中的民歌,大部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实质,表达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思想和斗争精神,如《伐檀》,它以辛辣的语言讽刺和诅咒了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在《硕鼠》中,更把剥削阶级比作贪得无厌的老鼠,刻画出劳动人民对奴隶主的切齿痛恨和对于“乐土”、“乐园”的向往。 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民歌已经十分繁荣。战国后期,诗人屈原等人,对楚国民歌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根据楚国民歌曲调创作新词,称为《楚辞》。《楚辞》中的不少作品,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感情,热烈面富于幻想,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乐府,从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入乐的歌谣,被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这些乐府民歌,多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直接道出了人民的爱憎,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这一时期的民歌在形式上已发展成为长短句和五言、七言体,并开始加进了乐器伴奏,《孔雀东南飞》等长篇叙事歌曲的产生,同时标志着这一时期的民歌在不断发展和日臻成熟。 唐代民歌的创作也相当繁盛。李隆基登位,杨玉环得宠,建立了杨家的裙带关系,她的姊妹都被封为夫人,气焰之盛竟至“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的地步,谣曰:“从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却为门上楣”。这未必代表老百姓心里的向往,只是一种对皇家的讽刺而已。 到了南宋,民间产生的讽刺性歌谣就更多了。南宋的统治阶级,贪污腐化,玩弄政权,有民歌讽刺道:“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皇帝卖酒醋。”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元明时代,人民的痛苦越来越深了。人民作歌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由于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激起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其中,以颖州的刘福通声势最大,他率领了10万农民,头包红中,号“红军”,所向无敌,所以歌谣道:“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进入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面临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具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民歌。如明代民歌:“吃闯王、穿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 清朝统治中国后,人民清醒地看到,统治阶级昏聩贪婪,这是招致外侮、陷国家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那悲惨的年代,老百姓连温饱都不可得,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 “天子坐金銮,朝政乱一团,黎民苦中昔,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1900年,袁世凯奉他的主子——清皇帝之命,到山东执行血腥屠杀政策,杀害无数义和团将士。人民恨透了袁世凯,便唱出了“杀了袁龟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人们在袁世凯巡抚衙门的墙壁上,画上一个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爬在一个洋人的屁股后。这幅漫画和歌谣,发泄了老百姓对袁世凯的痛恨心情。 随着清朝的垮台,民国以来,帝国主义为了扶植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军阀,残害中国人民,支持袁世凯称帝,当时袁世凯听见北京街上有许多卖元宵的,认为大犯忌讳,把元宵当成“袁消”,于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叫卖元宵,硬把元宵改为“汤圆”,于是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圆’。”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仇恨,日益增长,他们讥讽卖日货的商人:“绿坎肩,真是阔,绿帽子,也不错,叫你再贩日本货!” 作为历史的见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壮丽史诗,在民歌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如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农民这样唱道: “边区本是根据地,赶走了鬼子杀汉奸。”“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主,赋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正像一个人在经过艰苦跋涉的沙漠旅行后,突然看到了碧波万顷的大海,人们的情绪激动了,歌不断从激动的心头流出来。人们用歌声唱出了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人民创作了如《东方红》、《咱们的领抽毛译东》、《浏阳河》、《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传世之作。 民歌在新中国的土壤上得到培育,像春天田野里的野花,连片密布,摇曳生姿。社会主义民歌创作的沃野展现在眼前,劳动人民的歌声冲天而起,响彻云霄。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派出工作组对全国的传统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风进行大范围的抢救挖掘工作。自1984年起,又开展了编辑《中国歌谣集成》工作。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活动,使得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得以典藏保存,为丰富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民间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国民歌有着悠久的传统,远在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搬运、祭祀、娱神、仪式、求偶等活动中开始了他们的歌唱。由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歌,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歌也就遭受到同样的命运。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帝令禁唱。有关它的历史很少有文字记载。从出土文物考察,有关古代乐器的较多,而歌唱活动的较少。青海大通县出土的那个有歌舞图像的陶盆实在非常宝贵,它显示的是六千年前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歌舞活动。在原始时期歌与舞是结合在一起的。直至今天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持歌舞不分的古老传统。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淮南子》这本书上,曾提到古人抬木头时唱着劳动号子,可见早期民歌与劳动紧密相连。从兄弟民族来看,如阴山岩画上的歌舞图像、瑶族的《盘王歌》、苗族的《古歌》、满族的《萨满调》等,又可看出原始民歌与巫等原始宗教活动有关。有关古代的民歌,实际音响已不可能再现,只有它的歌词,从古代文学著作中可见到一些。至于曲谱是没有的,因为民歌一直是口头传唱,就是有了记谱法以后,劳动人民也不用它。宜到19世纪末才有民俗学家用工尺谱记录几首民歌。全面、有计划的搜集、整理、记录、出版民歌只有在新中国才成为现实。从历史上看民歌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小曲、俚曲、小令、俗曲、时词以及明、清时代常以山歌泛指各种民歌。《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民歌词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五百年间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它的鲜明特点是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阶级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多方面的生活。在形式与语言的整齐划一上,不难看出这是经过选择、加工整理过的。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出现了另一部长江流域的民歌集《楚辞》,这是一部在长江中游古代巫歌的基础上经过伟大诗人屈原整理加工的歌词集。它的突出特点是充满了古代的神话、传说,富于想象,它开始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并且把《诗经》的四言体民歌发展成一种句式自由,韵脚多变的“骚”体歌,而且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到了汉魏六朝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420年)的民歌,大部分保存在乐府里,汉《乐府》民歌实际是淮河流域、长江下游、黄河中下游各地民歌的汇合。这时已经有了故事歌,如《孔雀东南飞》、《木兰从军》等故事歌,其内容大多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以及封建礼教下的家庭悲剧。这样的故事从公元初流传至今,几乎家喻户晓。不但有民歌形式演唱,而且成为戏曲的著名剧目,可见其影响之深。乐府民歌的突出特点是不仅文字部分经过整理,而且在音乐方面得到当时汉代著名音乐家李延年的加工,配上丝竹乐器伴奏,称之为相和歌。从《诗经》民歌到汉乐府民歌,可以说是中国民歌的古代早期,其内容之丰富,表现力之强烈,已相当完美,可以想象到在此之前,民歌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原始时代。在原始时代音乐文化无专业可言,到奴隶社会,奴隶主有了专为他们享乐的乐奴,才开始有了分化。真正划分为专业音乐与民间音乐两个范畴还是到了封建社会,有了专为帝王、贵族的祭祀、仪礼、宴会、娱乐等演奏、演唱的人员,尤其是有了记谱法与专业作曲人员,才逐渐形成了明显的文野界限。在我国从汉代逐渐有了专业与民间音乐之分,汉代以后,也就很少再有由官方组织编纂的民歌集了。早期民歌的音调是否今天仍然存在很难确认,但是如今流传在湖北秭归县纪念屈原的划龙船歌(包括《起桨》、《游江》、《竞渡》)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古老船歌(包括《摇橹号》、《拉纤号》等)的音调恐怕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吧!也许就是千古遗音。从汉代到隋、唐当中有一个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在历史上这是我国各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歌明显的分为南朝民歌(南方民歌)与北朝民歌(北方民歌)两大部分。这一时期民歌的显著特点是多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不论北方民歌的粗犷、豪放;还是南方民歌的清新、活泼,都不是单一民族风格色彩。这种南北民歌的不同风格,在今天现存的南北民歌中仍然能分辨出其深远的影响。唐代(公元615——967),宋代(公元960——1279)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兴盛时期,尤其是盛唐时期,边疆民族的歌舞艺术大量传入中原,对于中原的音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显然内外文化交流对音乐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唐代的专业音乐有了很高的成就。唐、宋以宋民间音乐中的说唱与戏曲逐渐形成。有关唐代的民歌,我们从敦煌所藏曲子中可以找到一些,如《五更啭》之类。另从当时流传的《竹枝歌》也可了解一、二,竹枝歌是兴起于长江中上游巴渝一带的一种自由吟唱抒情山歌,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白居易都吸收过这种民歌因素,写过一些文人创作的《竹枝歌》。直至今天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的田歌中还能找到《竹枝歌》的曲式结构痕迹。宋代的“曲词”很盛行,当时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新型演唱形式。元代(公元1221——1368)以“小令”闻名,“小令”是民歌的一种,现今西北地区的民歌仍有以“令”命名的山歌。元代的小令流传后世的很少,元代统治者对民间带有不满与讽刺时事为内容的民歌,视如洪水猛兽,严禁传唱。明代(公元1368——1684),清代(公元1641——1911)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中、小城镇市民阶层兴起,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民思想异常活跃,民歌特别兴盛,其数量之多,人民性之强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时已有半职业艺人演唱民歌小曲。到清代晚年(184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封建,反抗外来侵略为主题成了近代民歌的时代特点。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文学家搜集编辑的民歌歌词集,如黄遵宪的《客家山歌》、冯梦龙的《吴歌》、李调元的《粤讴》以及华广生的《白雪遗音》等。由于个人的偏爱,这些民歌集在品种上大都偏重于民间抒情民歌。其中不少民歌今天仍在民间传唱。更值得提出的是清代著名民间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俚曲》,选用了明末清初民间流行的五十几种民歌曲牌。其中有一些一直为民间艺人传唱至今,使我们能够听到三、四百年之久的民歌曲调,甚为珍贵。20世纪以来,经历了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歌达到了高潮。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广大农、牧民的觉醒,民歌得到了振兴。这个时期民歌的显著标志是,大量的内地新民歌向东部沿海地区传播,部分边疆兄弟民族的民歌也向中原地区传播,反映人民革命和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题材的新民歌,空前繁荣。此外,如争取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反对烟毒的民歌也为数不少。五四前后,李家瑞编《北平俗曲集》问世,已经有了民歌的曲谱记录。更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以后在延安兴起的向民间音乐学习的运动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揭开了现代音乐史新的一页。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人民才真正得到尊重,中国民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反映人民新生活的民歌如春笋般的大量涌现出来,不但题材新颖,而旦音乐格调更加活发、热烈、开朗、明快,充满了向上的激情合乐观主义精神,由于各个民族以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有不少民族甚至尚无文字,民歌仍然是他们的主要艺术形式,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大都保留着“诗、歌、舞”相结合的形式。相比之下,汉族由于戏曲、说唱的迅猛发展,民歌演唱活动不如兄弟民族活跃,沿海不如内陆地区传唱的民歌多。这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民歌的一个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