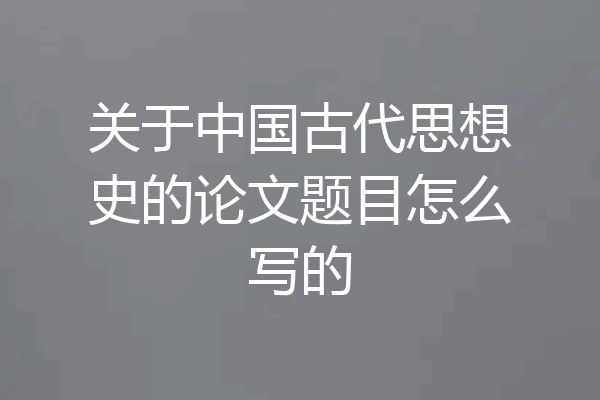借我一生1314
借我一生1314
传统文化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所积淀下来的文化~感觉有很多很多点可以写~你可以看看(心理学进展)、(社会科学前沿)等等这样的期刊论文吧~找下这类的论文好好学习参考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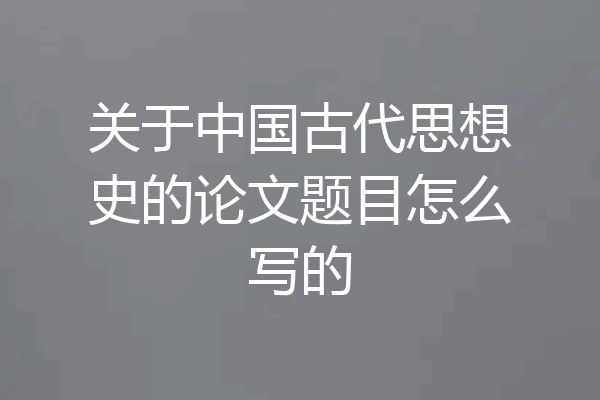
2000字2016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论文语文论文频道小编搜集的范文“2016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论文”,供大家阅读参考,查看更多相关论文 ,请访问语文论文频道。从勾勒出了人物品评转向的大致理路,由“德”向“才”转向。本文从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出发,来透视人物品评发生转向的原因,以下就是由精品学习网为您提供的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魏晋人物品评相比于汉代及以前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向,这一转向是在魏晋这一鲜明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一、 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人物品评古已有之,如孔子将门人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孟子将人格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等等。到了魏晋六朝时期,人物品评最初是和相书联系在一起,对人物的贵贱、贫富、祸福等进行评论、预测。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包含的将人物的内在精神同外在形体相联系的合理内核为后世所彰显。真正使人物品评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风尚,则起始于东汉的清议。这与当时政治上提拔、任免官吏要求士人必须在言行举止上有比较好的声望,必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地方宗族乡村集体对名士的品评和鉴定,普遍是被作为品评人物的核心依据,直接关系到士人的升迁、提拔及其政治前途,由此,品评人物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人物品评在曹魏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曹操的“唯才是举”与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是对东汉以来统治阶级所极端重视的却业已经成为空虚的道德标准的人才标尺的一个极为大胆而有力的冲击。这种重才轻德的“叛逆”对冲破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具有极其重要的解放性意义,导致了当时的人物品评由重“德”向尚“才”的历史性转变,即从强调人的道德伦理的本位性,转向强调个体的智慧才能的重要性。“这就使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打开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的一个领域,开始集中地对个体的智慧才能,包括对个体的气质、心理、个性及其外在表现进行研究。”汉末魏初的政治动乱使人对自身的生命短促、欢乐少有、悲伤凄凄等发出了一连串的怀疑和追问,而当时经学的衰落又使人对儒家礼教离心离德,从而给议论、争辩的风气打开了一条门缝,使这一时期的道德、哲学、文艺等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士人对此前传统的功业、信仰、经学发生了极大的怀疑,同时,伴随着这种思考,一种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这标志着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的传统标准和价值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种觉醒除受玄学思潮影响外,亦在人物品评中鲜明而具体地体现出来。分析考察一下人物品评的发展演变历程即可明白,魏晋前由政府主导下的官员人选决定着人物品评的基本内容,所评论的对象必须做到仁义、孝廉,言行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而才智则远远置于仁义礼智之后。具有规范性、广泛性的道德标准讲究唯德是评、唯贤是论,从根本上遏止和压抑了潜藏在不同士人身上的才智的充分发挥,使人物的个性不得不长期牵制于所谓一般共同性。自曹魏氏政权唯才是举推行后,便赋予了“才”以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它成为人物品评由政治伦理性向审美性转变的桥梁,促进了人的独立觉醒、人的自我认识意识的萌发,无疑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先声。及至《世说新语》问世,这部把人物品评作为主要内容的志人着作, 从重才情、尚思理、标放达、赏容貌等方面,对人物作了全方面的审美性考察。它排除了在人物品评上事关伦理、道德、学问等德性方面的诸多内涵,其所侧重的重才,是对人的本质的多重体现,虽仍然包含政治之才,但更多的是指绘画、书法、音乐、思辨等方面的创造欣赏、玄学思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人的种种智慧和才能,亦即是对此前几百年来才屈于德、人服于礼的一个重大反驳。正是这种转变使魏晋六朝的审美理想更具艺术趣味,更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也为这一时期文艺美学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先秦诸哲以争鸣的方式说,是道德实践的美,是智慧思考的美,而魏晋六朝在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兴起后,却赋予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人所追求的作为人的本质在于审美和自由! 如果说,在两汉时,人是善恶伦理的化身;那么,在魏晋六朝时期,人便是心灵和精神的化身,是诗意般的人生体验。经学的崩溃和儒学的经离给了魏晋这一特定时代的人们充分欣赏自己的绝好机会,它促使人们去感受人的存在、人生在世的意义及价值。这是一个讲求个性,欣赏自己,追求主体内在精神自由的时代,更是一个发现人本身、弘扬人格美的时代。魏晋六朝文学因为有肥沃的艺术土壤,便在此背景下显示出文学的自觉。也正随着文学的自觉,在创作上结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二、魏晋人物品评特色形成的基本原因人物品评最终脱离了“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选拔舆论准备的既定轨道, 成为广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间进行审美性的评价、认识和了解的主要渠道, 成为门阀士族彰扬和宣泄本阶层意志、观念乃至审美趣味的主要途径”。这一阶段许多文学上宝贵的收获都留下了人物品评的痕迹,都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当时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分不开。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水浒传》的主题是什么?自其产生以来就有争议。近几十年来以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为多。仔细剖析《水浒传》内容,它很少涉及到宗法社会的农民生活,更没有表现出宗法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诉求。即使偶尔写到一些农民也大多是沉默的、没有追求的、随人俯仰的一群。《水浒传》中写的社会底层的精英,他们绝大部分是游民或社会边缘人物。所谓游民就是脱离宗法网络、宗法秩序沉沦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小说中描写了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的挣扎和奋斗。他们的“经济诉求”是优裕的物质生活(成瓮吃酒,大块吃肉),为了实现这种物质生活就要迅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发迹变泰”就成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水浒传》中写出了游民奋斗过程中成功的一面(梁山聚义),但由于黑暗势力的阴谋陷害,最终失败了。《水浒传》所写的是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 《水浒传》作为第一部用口语写作的长篇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而且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考察,它也提供前所未有思想。一是它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人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人们受到社会不公正的待遇时,造反也是他们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水浒传》通过林冲、解珍解宝等人的故事指出官逼民反,造反有理;《水浒传》还为造反者建立了一套属于他们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不仅为后世造反者所认同,也为其他阶层的人们所理解。 近几十年来,《水浒传》中的招安是最为人们所诟病,特别是持“农民起义说”的人们认为“招安”是背叛。摆脱一些教条,对招安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招安既是当时(北宋南宋之交)不可避免的结局,其意义也不完全是负面的。 【关键词】 水浒传,游民,造反有理,招安。 一《水浒传》主题辩 尽管《水浒传》产生的时代和作者的生平状况,在学术界都有不同的见解,但它是中国出现最早的长篇通俗小说之一,这是没有争议的。从它一产生便拥有了大量的读者,上自皇帝,下至贩夫走卒都不乏“《水浒》迷”。尽管许多人抨击它,禁止它、焚毁它,但还是明清两代最畅销的通俗读物之一。明代批评家把它列为“四大奇书”中的一种。著名的评点家金圣叹说:“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它的“奇”不仅在于用当时的“引车卖浆者”的语言撰写了一百余万字小说,使读者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也是主流社会的人们非常少见的,与以前的文学作品相比,《水浒传》更是空谷足音。它的出现给读者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1,争议 《水浒传》是写什么的?它的主题是什么?这在不同的时期则有不同的说法,对于文学名著的研究与评价往往是与社会思潮同步的,社会思潮常常通过文学批评来表达自己。 《水浒传》写成于明代中叶,当它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刊刻出来的时候,正处于思想解放、个性觉醒时期,此时许多学者对《水浒传》是肯定的,说它所表现的梁山好汉“诵义负气,[1]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⑴。这是把梁山的英雄看作是实现正义公正的社会良心。托名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叙》也明确指出《水浒传》是“发愤之作”,其内容表现的是“水浒忠义”,把罗贯中、施耐庵看成是宋遗民,他们借写伏身草莽的英雄豪杰用以表达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到了清代,封建专制加强、统治者实行全面的社会控制。此时主流舆论对《水浒传》多持否定态度,说它“诲淫诲盗”,为不逞之徒立传,把《水浒传》视为最败坏人心的作品。最高统治者多次下诏禁止刊刻和出售《水浒传》。 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有许多研究者借《水浒》以比附当时社会斗争,二十世纪初,定一的《小说丛话》说《水浒传》“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并指出作者“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借宋江之事,而演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王钟麟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指出《水浒传》是讲平等、均财产的“社会主义小说”。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书信中称赞施耐庵有社会党人的思想,《水浒传》一书的主脑在于表现“官逼民反”。有的甚至用以借喻“实行宪政”或当代革命。鲁迅对此加以嘲讽“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⑵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阐释《水浒传》中则定“农民起义说”为一尊,五六十年代,对于这点的背离往往会招致批判;文革中要整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水浒》这部书”,又成为“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工具,这时谁要再赞美《水浒传》又会给他带来无妄之灾。由此可见,对于《水浒传》主题与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与当时的思想运动和政治倾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世更是把评论“水浒”当作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开古今未有之先例。 近二十年来,思想解放,对于一般的学术研究很少干预,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文史界的研究者逐渐突破对于“农民起义”的迷信,对《水浒》的阐释有所突破。从而打破“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先后提出了“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以及“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争说”,“综合主题说”,最近又有“反腐败说”等等。应该说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水浒传》思想内容的一面,但我以为都没有抓住《水浒传》的本质。这些论点大多还是没有从作品的总的创作倾向出发,而是从某种理念出发,甚至是为了适应某种思潮而产生的。自然,这些议论也就缺少说服的力量。 2,《水浒传》主题 我认为《水浒传》是游民说给游民听的故事,其内容是讲述游民的奋斗成功与失败的,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由于《水浒传》的最后写定者是沉沦社会下层的文士,其中就不免有些文人意识),反映了游民的好恶。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谈《水浒传》的主题: ①,水泊梁山好汉的个人成分的构成是以游民和边缘人物为主。 ②,梁山主人公的经济与政治诉求是带有游民性质的。 ③,从《水浒传》的形成过程以及书中所体现的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意识。所谓主题也就是该作品写的是什么和表达什么思想意识?弄清了这两个问题,主题自然也就显现出来了。 ④,从《水浒传》主要英雄人物形象的故事,也可以看出它是描写游民的成功与失败的。 3,《水浒传》述说的是什么人的故事? 《水浒传》是写什么的?说的是什么人的故事?这是理解《水浒传》的起点。小说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作者的思想倾向的,也就是说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的历史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演绎出的故事是该作品主题的载体,因此,只要我们对《水浒》主要描写对象及其故事做一些分析就可以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主要是写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位头领的遭遇与追求的。那些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之下,跟着头领们摇旗呐喊的喽啰们,虽然没有完全在作者视野之外,但也是被作者忽略不计的。 《水浒传》在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给读者提供了一百零八位好汉的名单。这些人按照出身或职业大体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将、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庄园主、其他等类。人数最多的是游民,近五十人;其次是武将,约二十人;第三是吏人,十人;勉强算农民的只有五人(阮氏三雄,解珍、解宝),而且这五人也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勤苦耕作的宗法农民。 甲,游民的故事 什么是游民呢?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脱离了宗法网络、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处的的人们都可称之为游民。游民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以获取生活资料。毛泽东在他早年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⑶谈到“游民无产阶级”时,把农村的游民分为五种:兵、匪、盗、丐、娼妓。“他们的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谋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 《水浒》中的游民以“盗”为多,而且还往往是占山为王的大盗。《水浒》的一百零八人,最后都上了梁山,都可以说是“盗”,当然不能这样算。这里只以梁山好汉上山以前赖以谋生的手段进行分析。梁山除了自己底班人马和初次聚义就选择了梁山的人物以外,许多头领还是其它小山头的山大王。如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桃花山的李忠、周通;清风山的燕顺、王英、郑天寿;黄门山的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对影山的吕方、郭盛;登云山的邹渊、邹润……这是有组织的游民。还有个体的抢劫者,如活跃在道路上、江河之中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夫妻黑店的张青、孙二娘等。其他如盗马贼段景住,小偷小摸的时迁。这些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以杀人抢劫为业的人们,在任何社会里都是非法之徒,为绝大多数人所否定。 游民并不是完全从事非法活动的,也有许多并无祸害民众行为的。但由于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脱离了农村、又没有正当职业的,生活没有保障,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卷入反社会活动。这样的游民在一百零八人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如在家乡“打杀了人”逃亡在外做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四处“躲灾避难”的武松;“自幼漂荡江湖,多走途路,专好结识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流浪蓟州、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式卖艺闯荡江湖的病大虫薛永;“权在江边卖酒度日”的王定六;“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着”的焦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个人”,奔逃在江湖上的石勇,这些都是无家无业的流浪汉。他们的共同点除了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沉沦于社会底层之外,就是:爱好拳棒,好勇斗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干犯法纪;讲义气,专好结识好汉等等。这是他们在江湖上生存和发展的本钱。有了这些他们才能够与主流社会对抗,杀人放火,攻击官府,用暴力向社会索取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他们在江湖上游荡期间,有的直接投奔绿林,不以当“盗贼”为讳;有的寻找一切机会以改善自己境遇,哪怕为此触犯国法。 乙,游民知识分子 宋代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文化要求的日益迫切,科举考试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更增强了这种迫切性,而造纸技术和雕版印刷的发展和发明,使得书籍易得,又为一般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宋代文化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使得读书人大量增多。然而官府对于知识分子的吸纳能力毕竟有限,有些掌握了一定文化。做官不行,又弄得无家无业,就成了我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这些人可能成为江湖艺人,可能成为各种各样江湖骗子,可能成为豪门贵府的帮闲,也可能参与造反活动。梁山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军师吴用,副军师、宗教代表公孙胜都是这类人士。无论什么朝代。游民骚乱、农民抗争没有这类人士的参加,民众的造反活动闹不大,有了这些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会提出斗争策略、会神道设教,从而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反抗的队伍。因此,要使造反队伍壮大,必须有此类人物参与决策。例如为北宋真宗时益州起事的王均出谋划策的“宰相”张锴,就是“粗习阴阳,以荧惑同恶”的道士之流⑷。南宋初杨幺起义最初领袖锺相也是巫师、道士一流。史书上说他“以左道惑众”⑸。梁山上的吴用、公孙胜是宋江等武装抗争活动的重要决策人。由此可见,水泊梁山的政治军师活动是受到游民支配的。
 借我一生1314
借我一生1314
 借我一生1314
借我一生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