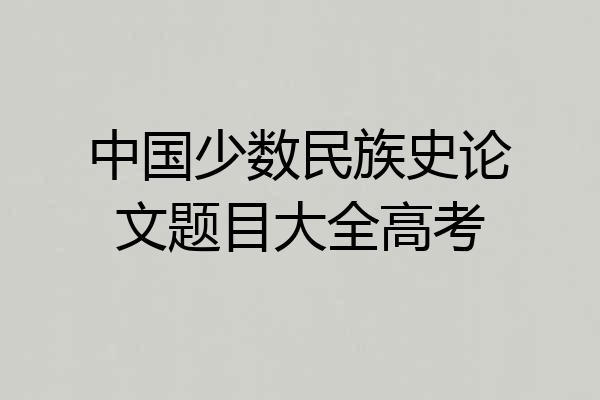guyue911
guyue911
先秦时代尤其是战国时期楚、秦就被认为是蛮夷,到汉朝时期中原人民逐渐形成汉族。但是后来唐、元、清都是身上都有游牧民族的血统和基因,这些游牧民族逐渐吸收中原农耕文化的精髓,完成封建化,然后入主中原。还有些民族虽然没有统治过整个国家,但是也为民族的融合做出过贡献,如渤海国、吐蕃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回、满、畲用汉语外,其他都有自己的语言,蒙、藏、维吾尔等十几个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为创造祖国灿烂的文化,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自己宝贵的贡献。中国各民族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互相融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为全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过分强调汉族的作用,忽视少数民族的贡献,是片面的。比如入主中原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在保留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延袭和发展的前朝的制度,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就是那些完成了局部统一的少数民族同样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匈奴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吐蕃统一青藏高原等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光荣传统。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反对压迫剥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族人民为了反抗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曾多次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例如,东汉杜琦、杜季贡领导的汉、羌族人民联合起义,岭南各族人民联合起义,西晋巴氐人李特领导的关西六郡人民起义和蛮族张昌领导的荆州蛮汉各族人民起义,北魏匈奴人破六韩拔陵领导的“六镇”起义,鲜于修礼、杜洛周、葛荣领导的河北各族人民起义等,都是几个民族起义军互相联合,互相声援。唐末的黄巢起义,宋代汉、壮、苗、瑶、侗等族人民的多次起义,也都是各族互相响应,配合作战。元代,各族人民共同反抗的斗争,更是史不绝书。明代,大藤峡瑶、壮等族人民的起义,老回回马守应领导的回民义军积极配合李自成农民军一起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清初,作为张献忠农民军的继续,李定国、李来亨领导的西南苗、瑶、彝、壮各族义军前后败敌数十万,此后的苗民起义、回民起义,也都是有许多民族共同参加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边疆地区和中原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相互了解和依存关系的加深,进一步导致政治上的接近和结合,从而逐步为组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奠定基础。全国统一集中的发展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局面,统一了战乱频仍的中国,第一次建立起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给中华各民族进一步加强联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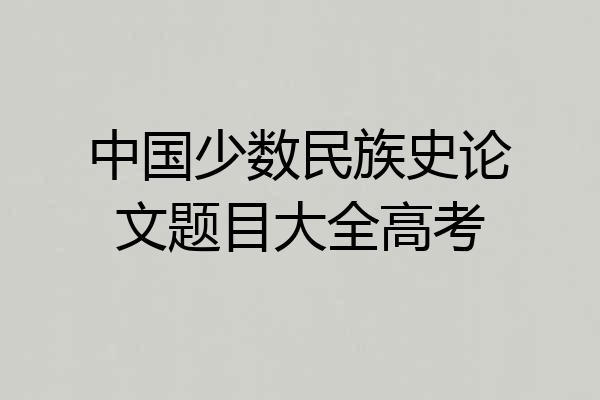
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齐民要术》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中国的传统经济文化是一个“多元交汇”的体系,少数民族对中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有的尚保存在现存少数民族之中,如藏医、蒙族的天文学等,比较容易看得见、摸得着;有的已融化到华夏族或汉族科技文化的历史成果中,这就不那么容易能看得见、摸得着了。我们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不但要注意前者,而且要把后者从历史的尘封中剔发出来,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估量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后者是更为困难、也更有意义的任务。 《齐民要术》是人们所熟知的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经典,它产生汉族传统的活动中心——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它的作者贾思勰是汉族人。但它的内容不但包含了汉族人民的科技文化成果,也包含了汉族以外许多民族的科技文化成果。通过这个典型实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文化是如何融汇在一起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 少数民族育种和引种的成就 《齐民要术》卷十为“五谷、果蓏、菜茹中非中国物产者”,所谓“中国”是指黄河流域中下游汉族传统活动中心。因此,该卷所列将近二百种植物,除部分重复的以外,都应视为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栽培作物或野生植物。我曾以此为线索,研究我国少数民族首先驯化或引种的作物[1] 。其实《齐民要术》前四卷论述种植业的有关篇章中,也包含不少这方面的材料,有些作物仅根据其名称或记述即能确知产于少数民族地区。例如,我国古代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泛称为“胡”。而《齐民要术》中产于“胡”地、冠以“胡”名的作物或品种就有十几个。 一是原产少数民族地区的作物和由这些少数民族育成的作物品种。例如,“戎菽”就是东北民族驯化和培育的大豆的品系。《要术》引《尔雅》曰:“戎叔之谓荏菽。” 今本《尔雅》作“戎菽”,“菽”是大豆的古称。郭璞注《尔雅》谓“戎菽”即胡豆。孙炎、樊光、犍为舍人、李巡也认为是胡豆。按《逸周书王会解》说周成王时北方民族的贡品中有“山戎戎菽”。《管子戒》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山戎是东胡族系的一支,春秋初年活动在燕国之北。可见,“戎菽”是山戎族驯化和培育的一个大豆品系,人们着眼于山戎的族属,把“戎菽”称为“胡豆”。类似的还有产于西南民族地区的“矩豆”和、从高丽引进的“高丽豆”。《要术》又记载了也泛称为“胡豆”的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杂豆[2] 。又如,水稻是南方百越族系先民首先驯化的,《要术》记载了不少水稻品种就是出在南方,如《要术》引《广志》:“南方有蝉鸣稻,七月熟。”这里的“南方”指岭南,“蝉鸣稻”就是岭南越人选育的早熟水稻品种。“盖下白稻”是我国迄今首见的再生稻,从其“正月种,五月获”看,也应是南方民族首先育成的。原产少数民族地区的蔬菜,有被称为“楚葵”的芹菜,被称为“越瓜”的甜瓜,以及“西域之蒜”(亦称“胡蒜”)“南夷之姜”等。此外,还有产于西部地区的“胡椒”、苜蓿等。“胡芹”则是胡人种植的用作调料的蔬菜,中原人况以芹菜而名之,恰如芹菜之名“楚葵”。 二是原产中原,传至少数民族地区并育成新的品种的。如粟黍是中原华夏族先民所驯化的,传到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育成适应各地风土条件的品种,《要术》中有“胡谷”、“胡秫”、“辽东赤粱”、“白蛮黍”等记载。葵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主要蔬菜,桃、李和枣是原产我国华北地区的水果,《要术》中所记“胡葵”、“胡桃”[3] 、“羌李”、“氐枣”、“西王母枣”[4] 等,当系这些蔬菜和果树传到胡地后育成的新品种。又有在少数民族地区辗转传播形成新品种的。如“柰”(绵苹果)原产我国新疆地区,东传首先到达河西走廊,魏晋南北朝时河西走廊已成为柰的中心产区,并育成“冬成柰”——一种体大味美的绵苹果新品种。 三是原产外国的作物或品种,首先传到少数民族地区后再引进中原,或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新的品系。例如原产南部非洲热带草原的芝麻,首先传入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5] ,再由西北地区传入中原,故有“胡麻”之称。西汉以来已在中原地区种植,我国从此才有了大田油料作物。《要术》:“《汉书》,张骞使外国得胡麻。” 沈括《梦溪笔谈》说:“胡麻直是今油麻。……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种,亦谓之麻,故以胡麻别之,谓汉麻为大麻也。”与此相类的还有起源印度北部、锡金等地的胡瓜(黄瓜)[6] ,起源地中海、里海地区的葡萄,从安息(今伊朗)传来的安石榴等。原产地中海沿岸和中亚的胡荽(芫荽),是西北部游牧人喜爱的调料[7] ,胡荽与游牧人的这种饮食习惯一同传入中原,《要术》中有种胡荽专篇,是一种获利颇丰商品性生产。小麦是原产西亚冬雨区的越年生作物,通过中国西部新疆河湟一线传到中原。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传播中,产生了春播秋收的“旋麦”和类似大麦的“ 麦”,见于《要术》所引《广志》。又,《要术》引《西京杂记》曰:“瀚海梨,出瀚海地,耐寒不枯。” 瀚海梨可能就是新疆梨,据俞徳浚研究,新疆梨是“中国梨和西洋梨自然杂交的产物”[8] 。这样说来,它是中西文化交流在新疆地区的结晶。 从以上情况看,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文化,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交流中向前发展的:一种是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另一种是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前一种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后一种文化交流也往往以少数民族为中介。总之,在两种文化交流中,少数民族都为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应该指出,上述材料只是在《齐民要术》中一个特定范围(1—4卷)内抽取出来的,它没有包括卷十中的大量材料,即使在卷1—4中,有些材料由于没有在名字或直接记述中反映它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暂时把它们舍弃了[9] 。因此,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是极不全面的。事实上《齐民要术》所记述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多半或出产于少数民族地区,或与少数民族有这样那样的瓜葛。但是,即使这样不完全的材料,也已经说明了不少问题,那么,少数民族对中华农业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和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二、少数民族畜牧文化和畜牧技术对中原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许多发源于北方草原的原游牧民族相继进入中原,他们带来了北方牧区的畜牧文化和畜牧技术,对中国科技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齐民要术》中有明显的反映。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