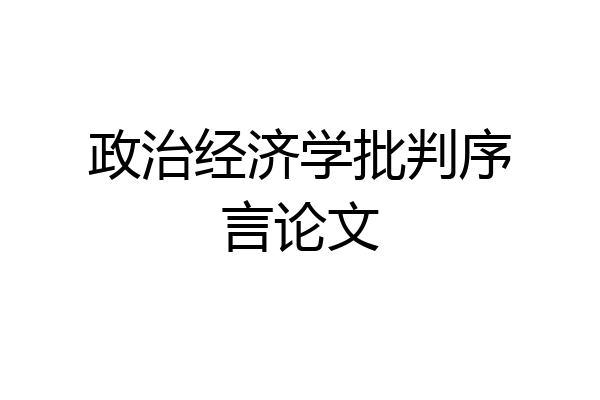wlhws2007
wlhws2007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读后感 金融实验 张帆 1857年,爆发了席卷欧洲各国和美国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促使马克思加快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进程。马克思利用过去积累的材料,在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间写出了总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导言》是这部未完成手稿的一部分。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马克思没有利用这篇《导言》,另写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说:“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导言》在马克思生前未发表,1903年3月,K考茨基首次把它刊登在《新时代》杂志上。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篇就指明了物质生产的重要性。然而,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很清晰地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总体中活动着的物质生产。没有认识到生产是历史的、具体的生产。人们紧紧把生产局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去进行研究和分析。马克思针对当时存在这样一种不够客观实际的观点就指出了在研究一个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时应该客观地去加以分析。应该把生产的发展看成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他在这里批判了那种孤立个人观点的肤浅性。马克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的“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这种三段论法的肤浅性。随后就具体的、分别地分析了生产和消费、生产和分配、交换和流通之间的复杂关系。 《导言》认为,社会生产是一个整体,它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这一节中,马克思主要阐明了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的观点。即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在阐述生产直接是消费时,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消耗这种能力。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在阐述消费直接是生产时,他也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生产者通过劳动将其劳动行为主要是指其在劳动过程中消耗掉的体力和脑力物化为劳动成果,即产品。第二,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产品,然后这些产品又为人们消费掉来维持消费者最基本的生活和再生产的需要。 除此之外,他还进一步深刻的解释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概括起来有下面几种具体的解释: ①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什么才能消费什么; ②消费同时也反作用于生产,如果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对象,那么也就不会有生产这种消费对象的生产了。 ③只有用于主体消费的产品才能发挥其固有的价值,才能在真正意义上称其为商品。 ④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同时生产又为消费提供了对象,没有生产就无所谓消费。 ⑤生产决定消费,同时决定消费的性质、方式。生产对消费产生了限制。人必须在生产的范围之内进行消费,脱离生产的消费就是一种空想。 ⑥生产创造出了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同时生产创造出来的产品也选择了消费该产品的消费者。 在生产和分配这一节中,马克思也是首先批判了那种把分配作为独立领域,从而把二者并列起来的错误观点。他在这一节中着重阐明了生产是先于分配而出现的,分配不能独立于生产而孤立的存在。他指出生产的前提不是分配,而是生产要素本身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不能把分配当做是和生产并列的两个孤立的领域。分配应该是生产的附属物才对。分配存在于生产的过程之中,存在于生产过程的始终。过程中的分配表现为生产工具的分配和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 在交换和流通这一节中,马克思开篇就阐述了交换和生产的关系。他在第二段中这样写道:“既然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从中可以很容易的看出,马克思认为交换作为生产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在这里我就把它理解成交换也是生产的附属物,它是依赖生产而存在的,生产决定交换。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我们在认识世界、认识客观规律的时候先是从丰富生动的感性具体出发,因为这是我们认识事物的起点,通过我们的感觉器官很容易被我们感知到。可以说这个阶段我们获得的认识是我们的感性认识。接着我们就会把我们所获得的感性具体经过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这样一系列的思维的加工之后我们就会对这些感性具体上升为比较深刻的抽象规定。到达了这一阶段后,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从表面现象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可以把握住若干个表面现象之后的规律性的东西。然而,到达这个阶段之后,我们的认识过程还没有彻底的完成。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规律的目的就是运用规律去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会把我们通过思维活动发现的规律性的东西运用到现实的具体中。而这个具体和先前的感性具体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个具体具有理性的性质,是更高层次的具体。是我们经过思维、思考以后合规律性的具体,这个具体在整体上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我认为只有达到了这个层次之后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刻的去把握事物,去认识世界。除此之外,马克思在论文中还点出了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思维进程与现实的历史过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读了这篇导言,我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关系更加明了了。更重要的是,我有了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一种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总结方法。这是比单纯的只是更加重要的。感谢马克思,感谢他的导言交给了我们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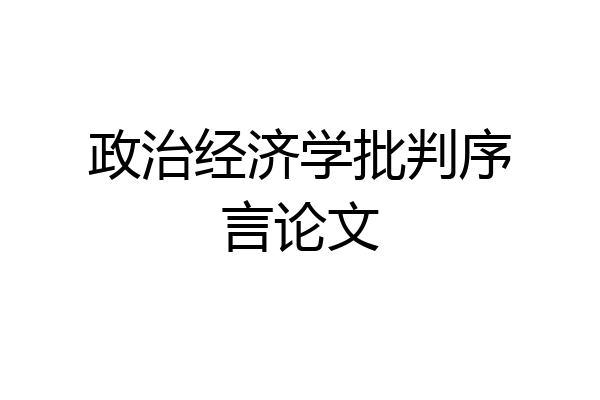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在我国流行并被不少人视为不能有半点怀疑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如此,在我的论文《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在《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发表以后,我国两位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奚兆永和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赵家祥不久就作出了回应。奚兆永教授在《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兼评〈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一文,批评我的论文想“从源头上来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我“不仅对有关文献缺乏整体的准确的把握,而且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理解也存在明显的错误”,并宣称“‘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一个建立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并经受了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1] 赵家祥教授则在《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对质疑‘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质疑——与段忠桥教授商榷》的论文,批评我的论文对《手稿》① 中的许多观点的具体理解是与马克思的原意相悖的,并坚持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一切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中。”[2] (P61)对于奚兆永教授的批评,我已在《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6期发表了一篇回应的文章。本篇论文,将主要回应赵家祥教授的批评。 在回应赵家祥教授的批评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谈谈我为什么要写那篇论文。实际上,那篇论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最近才提出来的,而是我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明确提出并在90年代详细论证过的。1987年,我在一篇题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形成、发展的再考察》的论文中对在我国流行多年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质疑,并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而不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3] 199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发展“五形态论”质疑——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文,对坚持“五形态论”观点的同志的一个论据,即“这一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来的”[4],进行了辨析,并进而表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没有提出过‘五形态论’的思想,而只是隐约地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论’的思想”。1995年,我在《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的论文,再次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提出质疑,并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的相关论述为主要依据,论证了“马克思本人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而只提出过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自那以后,由于我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别的领域,因而就再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来。2004年11月,我在武汉参加一个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南京大学学报》的同志约我给他们写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文。写什么呢?考虑到近些年来我国很多学者虽然都非常关注“回到马克思”的问题但在如何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上却存在种种不同看法,而我对国内学者了解较少的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又在一定程度上持欣赏态度,于是就想起了我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的那篇论文,因为那篇论文在方法上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颇为相似。基于这种考虑,我从如何解读马克思的文本的角度改写了那篇论文并将其给了《南京大学学报》的同志。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篇论文不仅在解读方法上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而且所提出的观点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后者尤其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这使我又有机会进一步阐述我近20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 一 我在那篇论文中提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著名论述,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是国内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学者的一个主要依据,然而,他们对这一论述的理解却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以这种错误理解为主要依据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就是不能成立的。对此,赵家祥教授提出,“《段文》认为,《序言》中的那段重要论述是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学者的重要依据,这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但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证明这个论据不能成立,‘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就不能成立了,则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因为,第一,‘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依据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第二,除重要依据之外,还有非重要依据。只有把所有依据都驳倒了,才算彻底驳倒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只要驳倒了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驳倒了这个理论,那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重要依据看成‘唯一’依据了。事实上,我们主张‘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决不只是《序言》中的一个依据,而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许多依据。”[2] (P61)为了证明其论点,赵家祥教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做了历史的梳理,并列举了八个他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文本依据。但这八个依据都能成立吗?让我们逐一分析。 在分析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明确两个问题:一是赵家祥教授所坚持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二是作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文本依据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按照国内包括赵家祥教授在内的学者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定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讲的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表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第一阶段)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6] 如果这就是赵家祥教授坚持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那么,作为这一理论的任何文本依据都应满足这样五个条件:它必须讲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不是其中某一时期的发展阶段;它必须讲的是社会形态,而不能是非社会形态的东西;它必须讲的是五种社会形态,而不能是三种或四种;它必须讲的是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而不能是并列;它必须是马克思(以及恩格斯)本人讲的,而不能是其他人讲的。 依据一:赵家祥教授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把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划分为三种所有制形式: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他们认为这三种所有制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所有制形式,如果再加上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和将来代替它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则正好是五种所有制形式。以这五种所有制形式为基础,形成五种社会形态,即部落所有制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依据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三种所有制形式的论述涉及的只是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因为从相关论述的上下文可以看出,他们是从“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7] (P68)这一论断出发论述这三种所有制形式的。其次,他们在这里讲的只是西欧历史上存在过的三种所有制形式,而不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讲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第三,他们在这里只提出了三种所有制形式,而不是五种。第四,他们并不认为在这三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依次更替的关系,因为他们强调,第一种所有制是与“分工还很不发达”[7] (P69)相联系的,第二种所有制是与“分工已经比较发达”[7] (P69)相联系的,第三种所有制是与“分工是很少的”[7] (P71)相联系的。这三种不同的“分工”之间显然不存在依次更替的关系,因而基于这三种不同分工的三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也不存在依次更替的关系。第五,“如果再加上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和将来代替它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正好是五种所有制形式”,但这只是赵家祥教授自己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没有这样讲过。 依据二:赵家祥教授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叙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并且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被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认为“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7] (P272)就是说,当时他们尚未发现阶级社会前的无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四种社会形态,再加上阶级社会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正好是五种社会形态。 这一依据也不能成立。第一,按照赵家祥教授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叙述的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这就是说,他们在这里谈的既不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也不是“社会形态”的问题;第二,按照赵家祥教授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尚未发现阶级社会前的无阶级社会”,即“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讲的第一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那就意味着他们此时持有的只是“四种社会形态理论”;第三,“如果再加上阶级社会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正好是五种社会形态”,这还是赵家祥教授自己的说法,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说的。 依据三:赵家祥教授说,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第一次以精确的语言表述了他的社会形态划分及其演进阶段的理论。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8]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再加上古典古代社会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历史也恰好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 这个依据能成立吗?也不能。第一,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并不是“他的社会形态划分及其演进阶段的理论”,而是“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7] (P345)这从上下文中看得很清楚。第二,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都不能说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讲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因为后者讲的是在人类社会不同地域普遍存在的社会形态,而前者指的只是在西欧存在过的两种特殊的社会形态。第三,马克思虽然讲了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每一个都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但由此既得不出他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的结论,也得不出在这三种社会形态之间存在依次更替关系的结论。第四,“再加上古典古代社会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历史也恰好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这仍是赵家祥教授自己的说法,因为马克思的这段话并没有这种意思。 依据四:赵家祥教授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序列,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将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正好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 这一依据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在我的那篇论文中已详细给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依据五:赵家祥教授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一个小注中说:“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