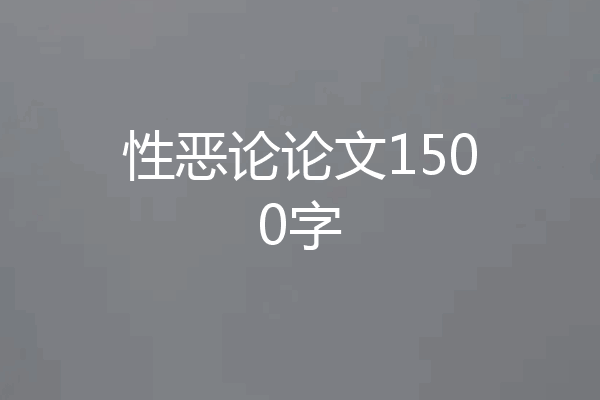菜鸟新
菜鸟新
孟子认为,“性善”是人的天赋道德;该说的根据是“四端”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就是说,人的四种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仁、义、礼、智,是从恻隐、羞耻、辞让、是非四种天赋的“心”发端的,也可以说就是这四种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所以孟子得出结论说:“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同上)意思是这四种心或品质,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人生来就固有的,只是人们没有通过思考而发现它。孟子认为这四种心普遍存在于一切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同上)其中“恻隐之心”——即仁之端,是核心。孟子举例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这个例子表明,善念的产生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而是恻隐之心的发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人性是善的。孟子的“性善论”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困境:既然人具有“善端”,具有善的本性,那么何以会有恶呢?如果没有恶的本性,不具恶端,恶又从何而来?孟子还说:“富岁之弟多赖,凶岁之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这简直就是用后天环境来谈论人性之善恶了,显然与他的“性善论”大相径庭。“性善论”在理论上的不彻底,创造了否定自身的条件;荀子的“性恶论”终于起而代之。荀子认为,一般所谓“善”,是一切行为都符合道德规范,服从礼仪制度;所谓“恶”,是用心险恶,行为不正,犯上作乱,破坏统治秩序。这种“善”,在人性中是没有的,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自然地符合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相反,人生来就好利、嫉妒、喜声色,如果不加以克制,发展下去就会产生争夺、犯上、**,而仁义礼智等道德也就没有了。所以,事实上人生来就是“恶”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圣人、君主对臣民的教化,需要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去引导人们。如果像孟子讲的那样——人性本善,那还要君主、圣人及礼义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什么用呢?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为)也”(《性恶》)。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有“善”,那是人为的结果。他批判孟子没有把本性与人为两者区别开来,因此不能正确了解两者的关系,不能了解圣人、君子的重要作用。从总体上说,荀子的“性恶论”比孟子的“性善论”要圆通一些,但 “性恶论”仍然存在自相矛盾的致命弱点:人性既然是“恶”的——在人性这个内因中不具备“善”的成分,而制度规范等又是后天的,是外部强加给人的,是外因,那么,在缺乏内在根据的情况下,外因何以能够发生作用?或者说,人何以会有道德行为?何以能成为善?荀子的解释是,这是由于反面的要求,亦即本身缺少什么就需要什么,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但是,从逻辑上说,所谓内在的反面要求,实际上就是善的要求,所以,荀子的“性恶论”无形中由性恶一元论发展为善恶二元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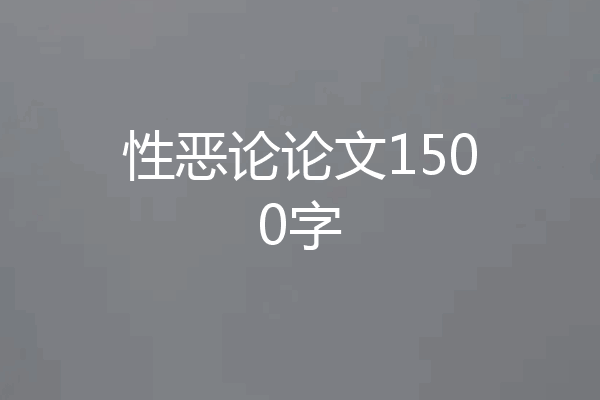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有的说人之初性本善,有的说人之初性本恶,已经争了至少有两千多年,至今未能有一致的结论。其实,人类自从有了文明以来,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此一直争论不休。究竟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我们之所以要旁及性善性恶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对伦理学关系重大。人称孟子(孟轲)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从性善论方面较系统论述人伦和施行仁政的哲学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人性善恶之争的引发者。有道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1]荀子(荀况)提出了与孟子对立的“性恶论”人性主张。凡人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2]康德说,“上帝的事业从善开始,人的事业从恶开始。”黑格尔和恩格斯说,恶是“推动历史发现的杠杆”。从善开始,是伦理绝对主义,即伦理主义;从恶开始,是伦理相对主义,即历史主义。东汉荀悦对性是善是性恶作了精辟论述:“孟子称性善,荀卿称性恶,公孔子曰性无善恶,扬雄曰人之性善恶浑,刘向曰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性善情恶是桀纣无性而尧舜无情也。性善恶皆浑,是上智怀惠而下愚挟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为然,韩子三品之说有类于此。”[3]我们便得知,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他们都说了人本性的一半。人的恶善时常被参半地表现出来。那么,荀悦提倡的“性善恶皆浑”,不得不引起我们关注的。西汉扬雄也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4]意思是说,人性内的善和恶是一体的,混在一起,难以分离。如果向善的方面培养,那善就出现,恶就消失。如果向恶的方向去培养,那善的因素就不存在,成为恶人。宋儒朱程等主张祛“人欲之私,存天理之正”,此儒家各宗,论心术之大要。但修行皆未得其法,而本性均未得其真也。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们曾经提出过另外一些精彩的理论,可惜由于后来出现独尊儒家的传统,这些理论没有得到重视,成为鲜为人知的非主流学派。现在,当我们看到了“性善”和“性恶”这两种理论都有缺陷后,有必要看看在这些非主流学派中是否存在更好的理论。除性善和性恶这两种理论外,第三种理论是荀子提出,他的学生战国告子发扬的“性不善不恶”说。荀子一直被人视为中国古代性恶论的代表,是因为荀子曾说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但是,有学者认为,荀子其实主张的是“性不善不恶,是中性的。”性是一团泥巴,塑造成怎样,就是怎样。(陈修武《人性的批判——荀子》)告子认为,性无善恶。“性无善,无不善。”善和不善,不是先天而生的,而是后天学习而能的。最后要讨论的是战国世硕的人性观。把他放在最后,因为从各方面考虑,他的学说应该是对人性的最正确的解释,符合历史和社会现实,而且正是我们要找的能够统一中西文化在人性观上分歧的新思维。世硕的理论是“性有善有恶”说(以下简称性善恶论)。他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以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王充:《论衡?本性》) 人自从有了智能、情感,有了语言与文字,便具有了善的能力,也有善报的诱惑,有乐善好施的满足的引诱,更因为有了自我实现的需要,当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得到满足,自我实现需要得到弘扬,善的本性就会更多地呈现,导人向善的动力是人类的本能。但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动物界里的弱肉强食、乱伦、生存竞争的基因还残留着,很多动物的本性还是保留着、潜伏着,只要生存条件重返险恶环境,恶的本性就会重新呈现,个体求生存的本能将导人向恶。由此可知,人性内有善有恶,培养善,善就会增长,培养恶,恶就会增长。郝懿行曰:“性恶篇末自‘繁弱、钜黍’以下,皆言身有美质,亦须师友渐靡而成,然则性质本恶,必资师友切靡而善,其意自明矣。然亦可知性善、性恶皆执一偏而言,若就浑全而论,自当善恶并存。所以孔子语性,惟言‘相近’,可知善恶存焉尔;又言‘相远’,可知善恶分焉尔。故曰‘群言淆乱衷诸圣’也。”[5]性善恶论基本上是对人性的最贴切的描述。因为人性论讨论的是有无的问题,所以只要能够简单地证明善恶的存在,问题就解决了。简单地说,人性本来就共生着善和恶的因素和观念。一个人初涉世事,他因具有了善的能力,在亲情的熏陶下,觉得这世界充满阳光、充满了爱,他会用善来回报这个世界,这就是日后变恶的人们在回忆当初时所谓的“太单纯”。到了三十岁左右,因直接参与了生存竞争,体验到了现实的残酷,他的善不但得不到善的回报,而且还会被人利用,在这时人性就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始终能坚持自己的信念,继续善的一面,这时,人类的本能占优势;另一部分人弃善变恶,参与了弱肉强食的混战,这时个体本能占主导。前者造就了一代伟人,后者使本已进化的人类返祖沦为凡人。你看那些贪官或绑匪,一生横行霸道,作恶多端,到了受法律制裁即将
《问说》《训俭示康》《马说》《师说》《为学》《薛谭学讴》《朱买臣传》《师旷论学》《卖柑者言》《孟子 梁惠王》《罴说》《苏武传》《颜回好学》